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觉悟了 '意义世界'
觉悟了 '意义世界'
文/梧闽
我有感覺,因为我活着。而这种感觉里,我又发现在了一个活着的意义,这就是人的生命理念一一意义世界。我刚懂事时,就盼着姥姥来了咱家…这姥姥住在九龙江边,而我的家,在云洞岩西麓…姥姥年迈七十几岁了,总是隔三差五来看我,有时侯背着2粒芋头、偶尔也有地瓜…或者一只鸭子,反正姥姥一到'天下都好'!我的欢呼雀跃…总与姥姥有关!而这一切,因为母亲,是姥姥生育6个子女的唯一幸存…旧社会太穷、兵荒马乱,又是水灾疫情,反正生育率与死亡率都高。姥姥迈騰蹒跚小步,从江边到山场十几华里。这一段弯弯曲曲的山野之路,写满了姥姥的爱,她的'意义世界'就是母亲,而母亲的'意义世界'就是我一一为么什活着,需要找到真正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意义',可以'舍身取义'。所以今晨醒來,我赶緊下笔,撰写一个哲学理念,人的'意义世界',高于人的'动物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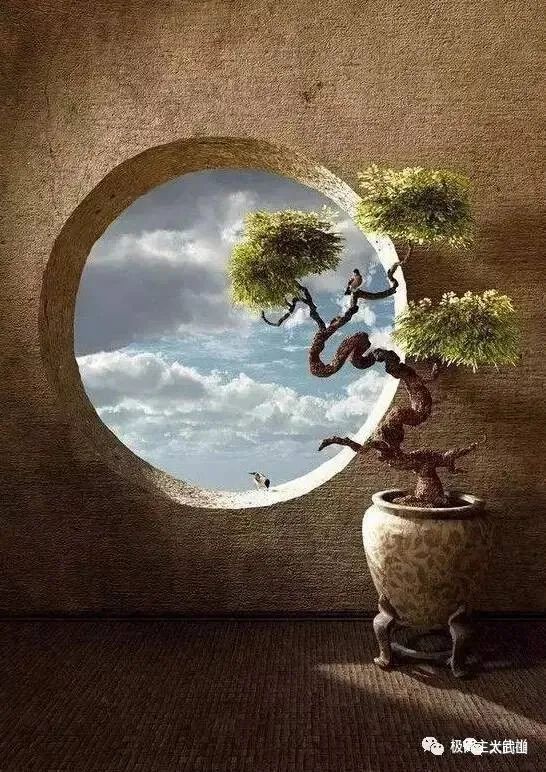

王阳明,字伯安,名守仁,自称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也就是当今著名作家余秋雨的家乡人。王阳明于1472年出生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时就读私塾,以“读书学圣贤”为“第一等事”。21岁举浙江乡试,后随父到京师,苦读朱熹遗书。26岁因北方边报甚急,遂留心武事,学习兵法。28岁中进士,赐观政工部。不久授云南清吏司主事,后改任兵部武选清吏司主事。因怒犯武宗,被谪为贵州龙场驿丞。以后曾先后担任过江西卢陵县知事、南京刑部、南京鸿胪寺卿、都察院左佥都御史等职。正德十六年(1521年)因平定赣南、粤东北及闽西南之乱有功(期间首倡设置漳州府平和县和广东梅州府和平县),后升任兵部尚书。嘉靖六年(1527年)总督两广军务,镇压广西少数民族起义,次年回师途中在福建南安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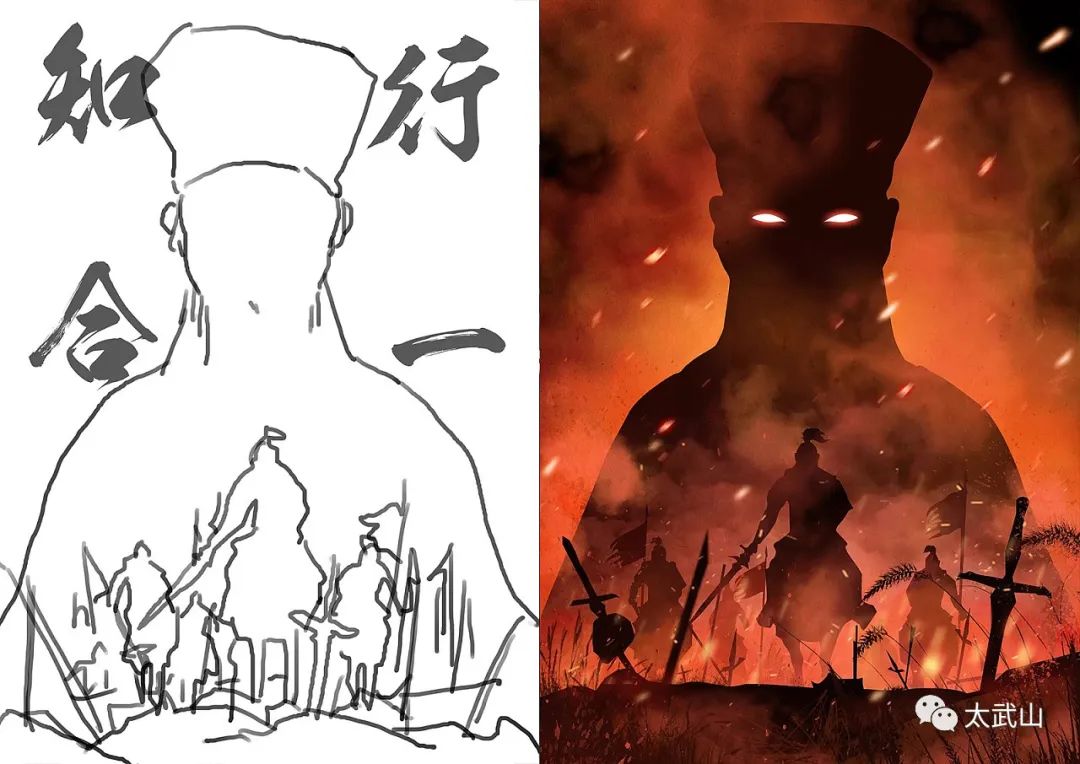
王阳明之名流传至今,倒不在于其丰功伟绩,甚至被美誉为明朝“军神”名声,而在于其摒弃业已僵化的朱熹理学体系,将佛学禅宗和老庄道学理论融入儒学体系,继承和发挥了南宋陆九渊的“宇宙便是我心,吾心便是宇宙”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把“心”看成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否认客观存在的真实性。这从本体上吸收了禅宗“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而变成“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的“心即理”理论。根据佛学《成唯识论》的观点:唯识者,一切万法不离心故。唯识学首先提出了“阿赖耶识”的命题,梵文译成汉文即“藏识”,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经验、过去、现在、未来、六根六尘十八界全部都在藏识里,也就是王阳明所说的那个“心”里。因此,王阳明强调做学问应在“明白自家本体”上用功夫,“不假外求”,即不必通过外界事物来获得知识,也不必盲目地尽信典籍。因而,他的心学属于主观唯心主义范畴,不同于客观唯心主义的朱熹理学。在知行关系上,他不同意朱熹理学的“先知后行”的方法,主张“知行合一”,以“致良知”取代朱熹的“尊德性”教育方法等等。但无论如何,他发展了儒学“以人为本”的辩证思维,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家思想的创新开辟了心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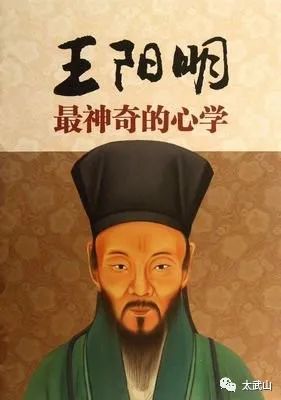
在王阳明的思想变化历程中,有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那便是“龙场顿悟”。养尊处优的礼部侍郎之子王阳明(在今天看来,是典型的“官二代”),出于忠诚和正直为忠臣辩护,却惹来牢狱之灾,出狱后又被太监刘瑾追杀,辗转数月才来到自己的谪居之地——远离京城的偏远之地贵州龙场。那么,在贵州龙场,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阳明幡然醒悟,不再向外求理,不再依附于人、追随于人,而笃信“心即理”?

王阳明在龙场生活是艰辛的,当时贵州的中心是贵阳,而龙场只不过是贵阳西北的一个小村寨,这里条件恶劣,道路艰险,而且王阳明和当地居民语言不通。《阳明先生年谱》曾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情形:“龙场在贵州西北万山丛棘中,蛇虺魍魉,蛊毒瘴疠,与居夷人舌难语,可通语者,皆中土亡命。”《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也提到:“居无宫室,惟累土为窟,寝息其中而已。夷俗尊事蛊神,有中土人至,往往杀之以祀神,谓之祈福。”王阳明初抵龙场,便披荆斩棘,搭建了一间茅草房。茅草房非常小,只有齐肩高,仅够宽慰旅途劳累。王阳明以原有的荆棘为篱笆,垫土为阶,台阶非常低矮,若有若无,以致让人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茅草房到处都是缝隙,早晨的凉风会呼呼地吹进来。屋顶铺着茅草,漏雨是在所难免的,但幸好便于修缮。在茅舍,可以听到清澈的潺潺流水声;傍晚,当郁郁葱葱的森林变得一片淡黑时,又可以体味那无尽的森林之趣。龙场的百姓依然过着“与鹿豕游”的野蛮生活,他们相当淳朴,经常聚到王阳明身边,用全然不知所云的语言向他打招呼。渐渐地,王阳明与当地人产生了骨肉般的亲情。当地人每天都会送食物给王阳明,王阳明也会和他们一起饮酒,有时会喝到酩酊大醉。关于这一时期的情况,《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是这样的:“先生初至,夷人欲谋杀先生,卜之于神不吉。夜梦神人告曰:‘此中土圣贤也,汝辈当小心敬事听其教训。’一夕而同梦者数人,明旦转相告语。于是有中土往年亡命之徒能通夷语者,夷人央之通语于先生,日贡食物,亲近欢爱如骨肉。

王阳明立足龙场之后,有一天他想起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之世,于是写了一首题为《初至龙场无所止结草庵居之》的诗,末尾有“缅怀黄唐化,略称茅茨迹”之句。太古时期,尧帝的宫殿非常简陋,台阶是泥土做的,且仅有三层,屋顶是用茅草铺的,连茅草的穗儿都没切除。虽然宫殿简陋,但尧帝的仁德却令天下百姓感服,他们遵守人伦道德,心平气和地生活。尧帝的仁德实在是太伟大了,就像太阳的光辉一样,人民日日沐浴其中,时间久了就会被同化,也就感受不到恩德的特殊存在了。正如《击壤歌》中所唱道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十八史略•帝尧陶唐》)尧帝的理想是“无为而治”,他是一位推行“无为而治”政治思想的伟大君主。王阳明到龙场之后,感觉这里就如同黄帝和尧帝所处的太古时代的“理想乡”,因此即使他身处逆境,也能够随遇而安。王阳明能够拥有这样的心境,全凭他日常不懈的修行。

在安居龙场茅舍不久,王阳明发现了一处钟乳洞,于是便将自己的住处搬到洞中。这个钟乳洞大约能够容纳百人,初名“东洞”,后来王阳明效仿家乡的阳明洞,把它更名为“阳明小洞天”。其实,王阳明家乡的阳明洞,并不是一处洞窟,而龙场的阳明小洞天却是一个真真切切的洞窟。钟乳洞所处的位置较偏僻,荒凉不已,而王阳明却觉得这是因为钟乳洞不容他人,专等自己到来。王阳明搬入此洞后,乐其幽静,悠然自得。他将洞内平整之地打扫干净,安放好床具,修好灶台,堵上老鼠洞,还作诗三首,题为《始得东洞遂改为阳明小洞天》(《王文成公全书》卷十九)。在第一首诗的末尾,王阳明写道:“夷居信何陋,恬淡意方在。岂不桑梓怀,素位聊无悔。”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已经达到了《中庸》中提到的“素位”境界,即君子要根据自己所处的地位来行事,而不要考虑其他不切实际的事情。《中庸》中关于“素位”境界的原文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根据《阳明先生行状》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当时跟随王阳明前往龙场的家仆共有三人,当王阳明决定搬进阳明小洞天时,他们都为能够找到这样的天然住处,无须再费力盖房子而欣喜。对此,王阳明在第二首诗中做了如下描述:“童仆自相语,洞居颇不恶。人力免结构,天巧谢雕凿。清泉傍厨下,翠雾还成幕。我辈日嬉偃,主人自愉乐。虽无棨戟荣,且远尘嚣聒。但恐霜雪凝,云深衣絮薄”。由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和家仆都夸赞这天然的住处,并为能够远离俗世而感到高兴。王阳明还为自己能够过上远古时代的生活而欣喜,他在第三首诗中写道:“上古处巢窟,杯饮皆污樽。冱极阳内伏,石穴多冬暄。”接下来,王阳明又写道:“豹隐文始泽,龙蛰身乃存。”喻指这样的隐居生活可以保全自己的名节,就像豹子隐藏起来,以防自己的毛皮花纹被雨雾损坏;龙蛰伏起来,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完好一样。也许有人会觉得住在宏伟的宫殿里,身着轻柔裘皮的生活才算快乐,但王阳明却期许颜回那样的生活。孔子曾大力夸赞弟子颜回,称其为:“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故王阳明又在第三首诗的末尾处写道:“邈矣箪瓢子,此心期与论。”

在王阳明理论书信简集的《传习录》里说一个故事,有一天,王阳明的一个学生问他,你老人家说万物都在心中,但山里的花开花落,如果没有看到,那花又怎么会在心里呢?王阳明是这样回答的,我没有见花时,那花与心同归于寂,当我看花时,花与心同时都明明白白了,可知花不在心外。又有个学生问,你老人家说天地万物都离不开自己,但是某人死了以后,天地万物仍然存在啊!王阳明回答说,你问得好,但我反问你,某人死了以后,他的那个天地万物还在不在呢?王阳明一生纵横于朝廷内外,足迹遍布明朝十多个省州,三十七岁在贵州龙场悟道后提出“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理论基础,并将朱熹理学那种尊重客观世界的“格物致知”,转变为将人的主观能动性发展到极致的“心”学理论。特别是他五十六岁在山阴县天泉桥上阐发的王学“四句宗旨”,即“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心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的格物。”王阳明的“心学”克服了中国传统儒学理学形而上学的偏差,为儒学注入了佛教禅学和老庄道学的思辨精华,从而整体提升了中国当时主导的东亚文化的领先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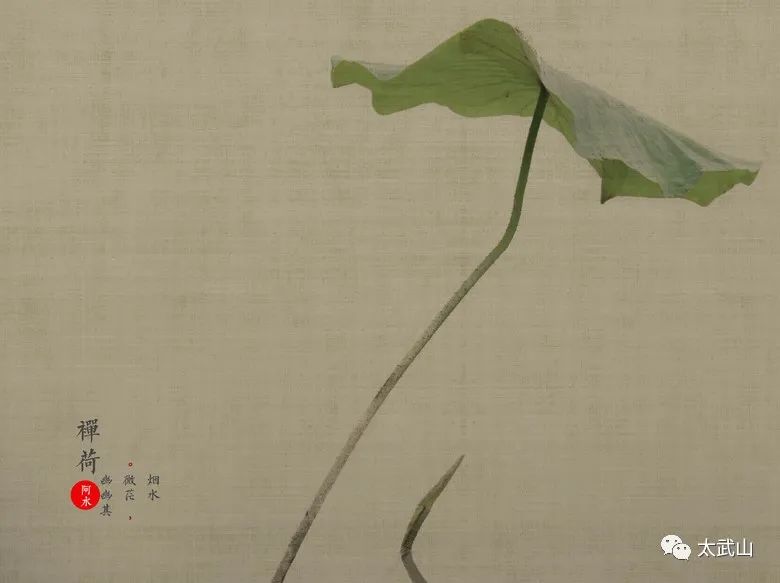
用辩证唯物主义比照“心学”,说明物质是否在意识之外独立存在,前者是肯定的,后者是否定的。王阳明关注的是“以人为本”的他的世界,这种世界,也就是属于人的意义世界。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客观世界的天地万物,其存在变化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然而,王阳明“心学”所关注是人的意义世界,天地万物与不同个体往往构成了不同意义关系,换言之,对于不同的主体,天地万物常常呈现不同的意义。从实际上看,每一个人都有其不同的、自己认可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而当他生命走向终结时,属于他的意义世界也即同时趋于终结,不属于他的客观存在也与其“心”永寂冥冥无期。如果他活着的时候,尽管尚有千山万水的风情美景,但也由于人的局限性,人的意义世界也具有相对性。更多的客观世界与人的心“同寂”而未醒,因而,“心”量的开发与客观世界的开发一样,同样具有十分开阔的内容和前景,也将赋予人的“意义世界”更加丰富多彩。人要与时俱进,完全不必受众人、别人或者古人种种前置的、死的、过时的、掺杂的框框和条条限制,而应努力去创新和突破,开辟其“心”中尚寂的新的意义世界。当然,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而言,不论你怎样“大胆地闯”或者非常“超人”的发挥,过程还必须受制于客观世界的科学规律,否则,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宋代大文豪苏东坡说过:“古之成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但换从“以人为本”角度而言,如果没有孜孜不倦、不怕失败的尝试,何来“致良知”而对“无相周天”的“了了便知一切”呢?从人的意义世界而言,失败的教训与成功的经验,其人生价值意义同样可取的。

“心学”并不是王阳明先生首创的,其远承的老师南宋陆九渊因不满意朱熹把理与心分一为二的哲学,认为它将造成士子只重诵读古人典籍而忽视经世致用、放弃主观能动的流弊,所以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说“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陆九渊集》)。王阳明把“心学”由命题发展体系,在学术上以空疏简易反对朱熹的精微广博,以怀疑主动反动朱熹的学究呆板。朱熹主张治学须“泛观博览”,书无所不读,遍注群经,著作等身,王阳明对此表示反感而评论道:“务外遗内,博而寡要”,其危害是“玩物丧志”(《传习录》下)。但话说回来,心学理论主张“明本心”,反对向外求知,看来仅适合于具备“良知良能”的少数人,并不适合于芸芸众生,它可能会导致忽视实践和书本知识,而流于空泛,许多心学未流不读书,不究理,只会打坐,空谈性命,混同禅宗“狂禅”,这样说来,程朱理学比之陆王心学尚有可取之处。朱熹提倡的理学读书之道,把人民引向本本主义,造成士子盲从书本,盲从圣贤的风气,陆王心学的“明本心”主张,提倡“凡事看其理如何,不要看其人是谁,”不能“随人脚跟,学人言语:(《陆九渊集》卷三五《语录》下),虽其言出之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同上)心学者不迷信典籍经书,亦不盲从圣贤行为,陆九渊认为“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集》卷三四《语录》上)。王阳明的“心外无理,心外无事”等观点,都有助于人们从教条主义的禁锢解放出来。因而,从稳定的需要而言,应多谈理学;从发展的取向而言,应力倡心学。中国与东亚每每需要变革之时,王学便往往卓见其功,明末的刘宗周、黄宗羲、王夫之等哲学思想无不打上“心”学王阳明的烙印,清末改良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都曾利用过王学的某些思想破除程朱理学教条,传入东亚之后的王阳明心学理论,更成为日本明治维新改革的精神动力……至于史载王阳明先生在广东韶关南华寺执意洞见禅宗六祖慧能的肉身佛,偈示六祖慧能转世王阳明之谜,其宿世因缘另当别论。

蒋介石先生说,王阳明的《传习录》乃其终生最爱的书,他曾自述:“当我早年留学日本的时候,不论是在火车上、电车上或轮渡上,凡是旅行的时候,总看到许多日本人都在阅读王阳明的《传习录》,且有许多人读了以后,就闭目静坐,似乎是在聚精会神,思索这个哲学的精义。”从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和经济腾飞后的现代韩国,凝聚王阳明心学哲理的《传习录》,都被他们称作为精神范本。日本的高濑武次郎著有《日本的阳明学》。他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王学所赐与。”看来,王阳明的“心学”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喷喷的,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也该好好用“心”来学一学了!

一言以蔽之,朱熹的理学可以坚定我们实事求是的世界观;王阳明的心学,又可能使我们得到积极进取的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从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中,可以略见一斑。

郑亚水,笔名梧闽,出生于漳州东郊梧桥村,毕业于漳州农机校和厦门大学政治学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先后由漳州市图书馆出版《秋水白云》《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深处》、海风出版社出版《月泊龙江》等书籍。2001年中国东欧经济研究会授其《企业文化一一现代企业的灵魂》''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改革发展论文集》(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9年11月,该论文被清华大学收录《n<1知网空间》智库咨文;《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中国文化出版社)副主编。
作品《<兰亭序>拾遗》一文于2010年9月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并荣获2010年度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奖”;2021年8月,作品《说好的父亲》荣获“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2月,作品《说好的父亲》入编《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并被评为“特等奖”;2022年4月,《过故人庄还有多少龙江颂》荣获第九届相约北京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7月,《紫云岩 无住与不迁》荣获2022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奖“二等奖”;《禅意 太武凡木》荣获全国第八届新年新作征文“一等奖”;《一字圣手江山常在掌中看》入选《高中语文》古诗词必读讲解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