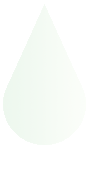也不知是从哪一天起,心里头就悄悄结了一层茧。总觉得这苍苍茫茫的人世,暗处里藏着些看不见的印记。那不是名山石壁上刻得工工整整的碑文,也不是经卷里正襟危坐的训诫——倒像夜深时,不知从谁家窗缝漏出来的一缕琴音,让夜风揉碎了,颤巍巍的,化进一团浓得化不开的墨黑里;又像是斜阳底下,荒草丛中那半截残碑,名姓都漫漶得看不清了,可石头缝里,偏偏挣着一股不肯伏地的骨气。
我要寻的,便是这样的痕迹——在时间的河里站成孤岛,拿骨头当笔,蘸着血作墨,在早已凉透的岁月里,硬生生烙下一道滚烫的魂。
这念头来得没头没尾。许是那个清早,推开窗,看见院里一夜风雨打落的花。残瓣软塌塌贴在泥地上,姿态却还撑着落下前最后那点倔,像咬着牙,不肯认输。看着它,没来由地想起南唐那位“梦里不知身是客”的旧王孙,想起汴京牢狱里,那支写着“天遥地远”、微微发抖的笔。他们的魂,是不是也像这落花,就算零落成泥了,还固执地守着生前的形状,存着最后一口气?我这是在寻他们呢,还是借着他们的影子,打捞自己心里那点不肯随波逐流、虽微弱却挺得笔直的东西?
昨夜里做梦,恍恍惚惚的,像是穿过鼎沸的街市,把车马人声一层一层甩在身后,独自往城西的废园走去。园子早就荒了,断墙边的野草窜得半人高,只剩一株老树,身子歪斜着,枝干像黑铁似的虬结着,默然对着天。一位须发长得邋遢的老者说,这是明末时候,一个不肯剃发的读书人种下的。没留下姓名,只留下这棵树。我靠着枯干的树干坐下,看夕阳一寸一寸从斑驳的墙头褪尽,寒气从脚底慢慢漫上来。闭上眼睛,风吹过倒塌的圆洞门,呜呜地响,恍惚间好像有人在空园里低低地哼着什么,调子苍凉极了,唱些什么却一个字也听不清。那份孤绝,那份在绝境里仍要守住一点什么的狠劲,隔着几百年的风烟,一丝一丝渗进血脉里。我要寻的,或许就是这样敢与无边孤独默然相对的胆气。
后来随着儿女去了江南,倒遇见另一种痕迹——清泠泠的,带着水汽的骨气。雇一叶乌篷小船,在欸乃的桨声里漫无目的地漂。水是沉静的绿,绿得幽深。两岸的白墙黑瓦、石桥台阶,都洇在蒙蒙的水汽里,轮廓软了,时光也好像慢了。船经过一处临水的旧楼,粉墙剥落了一片,露出一方青石匾额,“澹生堂”三个字清秀,却像用刀子刻进石头的背脊里。撑船的老艄公说:早先是个书痴的藏书楼,那人为了搜罗孤本,散尽了家财。后来书散了,楼空了,人也不知去了哪里。我望着那空荡荡的窗口,仿佛瞥见一个青衫影子,就着一盏黄豆大的灯火,在无边的雨夜里校勘、抄录。他的硬气,不在嗓门高低,而在那“润物细无声”的持守里,在静默中接续文明血脉的那股韧劲。雨丝落在河面,漾开无数细密的涟漪,方生即灭,就像那些没留下姓名的人生——史书上不见波纹,却真真切切,润湿过一方水土的魂魄。
可是,寻得愈深,那孤独的滋味反倒愈是咬人。那些魂终究是远的,隔着历史的云烟,隔着浩瀚的书海。我得找些近处的、活生生的回响,来证明这场寻觅,不是我一个人虚妄的梦。
于是把目光,投向眼前这熙熙攘攘的人间。没承想,真遇着了几位“文友”——这称呼是旧了些,却对我的脾胃。我们不常聚,多半散在各处过日子,像夜空中疏疏朗朗的几颗星,彼此知道方位,守着恰当的距离,与静默。
一位住在城北旧书市旁边,守着一个小小的书画摊。铺子里总飘着纸墨陈年的气味。他那双手枯瘦,却极稳,让人觉得生命是在纸上呼吸的。有一回去,见他静静坐在昏黄的灯下,低着眉,神情专注得近乎一种宗教的庄严。那一霎,我好像看见“澹生堂”主人的影子,跨过几百年,叠在这沉默的老人身上。我们偶尔也说几句,话极少,只论纸的成色、墨的浓淡。可就在这极简的话语里,流动着对“文”字本身的敬畏,那是我们相认的印记。
还有一位,在遥远的边地教书。我们靠微信联系。他的话总裹着风沙的粗粝,却贴着地皮,扎实得很。他不谈空阔的理想,只说怎样费尽周折,为山里的娃儿弄几本像样的书;又说寒夜里,批改那些语句稚嫩、情感滚烫的作文。有一次他写:“这儿风大,常把电线刮得呜呜响,像古时的埙。我不敢指望这些孩子个个成栋梁,但我信,他们心里若能因此多懂一点美丑,多分明一点是非,总不是坏事。就像风里的埙声,不成调,也是天地间的一点响动。”读罢,眼前倏地模糊了。这哪里只是一个教书人的独白,分明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那点星火,在最糙最砺的现实里,微弱而倔强地燃着。他的硬气,是根子扎在泥土里的,带着生存实实在在的重量与体温——里头自然也藏着无言的难处:教材缺,学生少,外面“读书无用”的私语像风沙一样磨人。他没有多说,我却从字缝里,听出那沉甸甸的摩擦声。
这么一来,我的寻觅,像有了着落,又好像永无尽头。历史的孤魂与现世的友声,像经线与纬线,在这匹叫“生命”的布上交织。他们让我渐渐明白,那“骨气”从来不是悬在半空的东西——它是孔夫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奔走,是太史公受刑后不肯停下的笔,是五柳先生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脊梁;它也是旧书店老人抚过纸页时一丝不苟的指尖,是边地风沙中,为孩子念书时那沙哑的嗓音。它是在绝顶孤独里的死守,也是在人间烟火中,将一点精神头儿传下去的那份近乎笨拙的认真。
前几日,又路过一处废园。那株老梅竟开了花,疏疏的几朵,颜色淡得近乎白,在寒峭的风里微微地颤,却吐着一股清冽的香。我立在那儿看了很久,直到暮色像墨一样晕开,浸透了天地。回去的路上,华灯初起,市声依旧嘈杂。心里头,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踏实,也空阔。踏实的是,我知道这世上,从前有,现在也还有那样的人,那样的魂;空阔的是,我明白自己永远寻不尽他们,而他们也从来不需要谁的寻访与惦记。
我不过是个在时间河边偶然驻足的人,俯身,掬起一捧水,看见里面漾着千年前的月光,也映着自己模糊的容颜。然后直起身,继续走我的路。或许有一天,我也会变成后来人眼中,一抹淡得看不见的痕迹,一缕散在风里、无声的叹息。
这样,也就圆满了。所谓来处与归途,不过是我们这些人间客,走在这条名叫“寻觅”的悠长古径上。如尘埃偶遇光,似微芒轻触夜——我们各自立在自己的时序里,不发惊雷之响,不作炫目之华,只是静默地、认真地,绽一朵属于自己的小花,或者干脆就是一株无名草。
作者简介:喻大发,笔名草根,1952年出生,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人,农民。早年深耕乡土文学创作,曾获县级“模范创作者”称号,后因生活压力搁置笔墨。近年重拾写作,寄情文字以修养心性、安放情怀。作品散见于《中国高新区》《武汉作家》《问津文艺》等地方刊物,亦在多家文学类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稿逾两百篇。

举报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