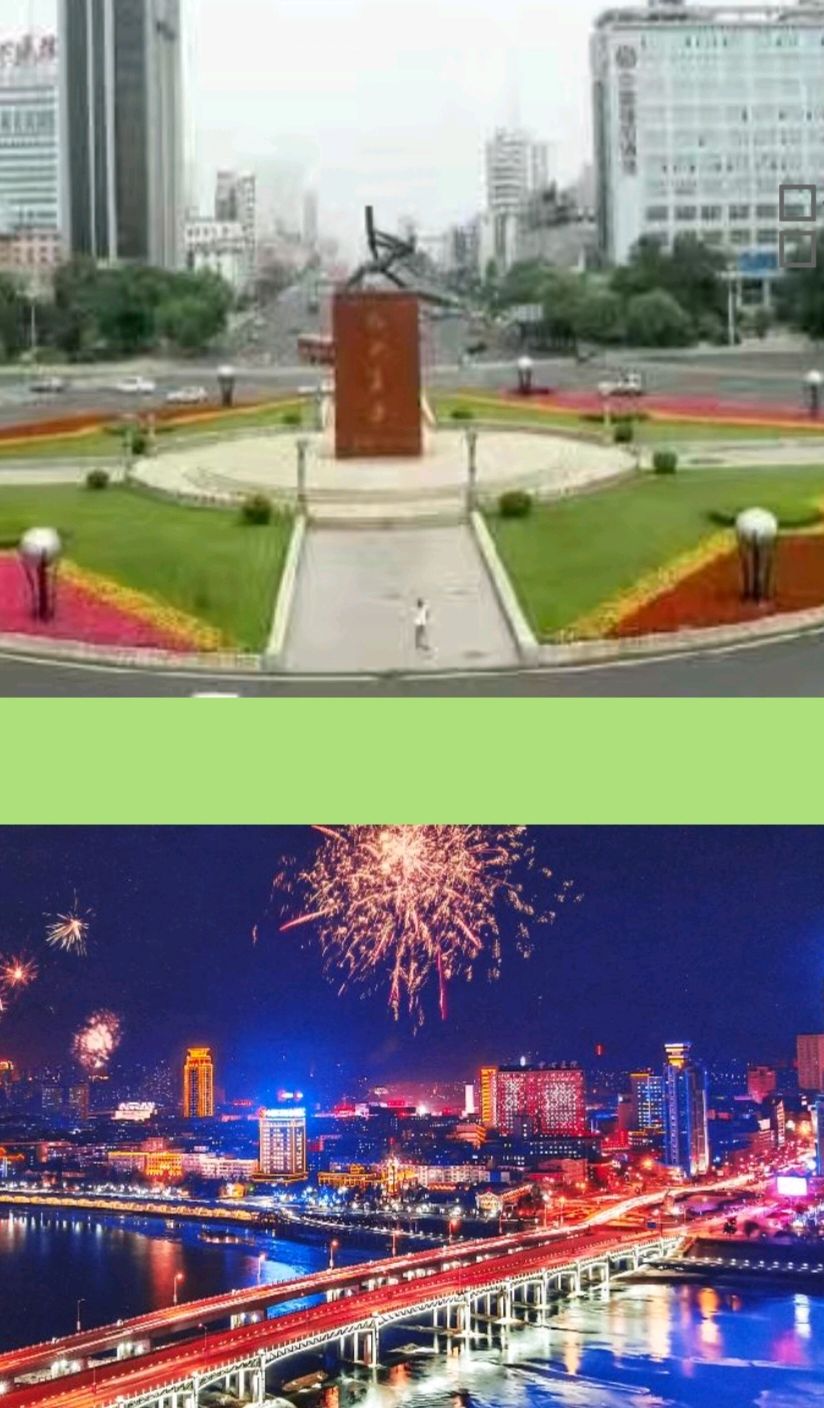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向往春天,从一朵木棉花出发(游记)

晨光微熹时,车轮已经碾过琼州大地二百余公里的风景。从三亚出发,一路向西,窗外的景致从椰风海韵渐渐过渡到丘陵山野。母亲坐在后座,额头贴着车窗,眼神里满是孩童般的好奇——这位在吉林冰天雪地里生活八十余年的耄耋老人,至今仍对海南岛这常年葱茏的模样感到不可思议。

“木棉花,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红吗?”母亲第三次问起这个问题。
“比您想象中还要红。”我透过后视镜看见妻子正握着母亲的手,两人相视一笑。这画面让我心头一暖。

一、赴约
昌江七叉镇的轮廓在上午十点逐渐清晰。还未进镇,那抹红色便撞进了视线——不是星星点点,而是成片成片的,像大地迸发的火焰,又像天空倾泻的霞光。母亲突然坐直了身体,发出一声轻叹:“天啊……”
车停在观景台时,我们都沉默了。不是无话可说,而是任何语言在这般景象面前都显得苍白。从高处俯瞰,昌化江如一条碧绿的绸带蜿蜒而去,两岸是层层叠叠的木棉树,每一株都高举着成千上万朵红花,没有一片绿叶的陪衬,就那么赤裸裸地、坦荡荡地燃烧着。
“这花真霸道。”妻子轻声说,“不给叶子留一点位置。”
母亲却摇头:“这不是霸道,这是赤诚。把所有的生命力都用在开花上了,多实在。”
我们沿着田塍小径走进那片红色海洋。木棉花开得那样浓烈,那样决绝,仿佛知道自己的花期短暂,便要在这有限的日子里燃尽所有的热情。春风过处,不时有花朵旋转着坠落,“啪”一声轻响,砸在地上,也砸在心上。
一朵完整的木棉花突然落在母亲脚边。她弯腰拾起,捧在手心细细端详。五片厚实的花瓣向外翻卷,花蕊密集挺立,橙红的花瓣基部渐渐过渡到金黄,像小小的火炬在掌心燃烧。
“真重。”母亲惊讶地说,“不像花,倒像是用红绸子做的。”

“所以叫英雄树啊。”我解释道,“你看它总是长得那么高大挺拔,花开时又这么热烈奔放。”
二、花语
我们在一株特别高大的木棉树下驻足。树干粗壮,树皮上布满圆锥形的刺。抬头仰望,满树红花在蓝天映衬下更显炽烈。阳光透过花瓣,几乎要让人产生幻觉——那究竟是花在发光,还是光本身变成了花的形状?
“妈妈,你看!”妻子突然指着远处。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几个黎族妇女正背着竹篓在田间劳作。她们鲜艳的筒裙在绿色田野中移动,与满山的木棉红遥相呼应。更远处,新建的民居白墙黛瓦,屋顶上太阳能板闪闪发光。
母亲眯起眼睛看了好一会儿,喃喃道:“这日子,真好。”
“妈,还记得咱吉林老家的丁香花吗?”我问。
“记得,紫色的花朵,一簇簇的,开得也旺,就是花期短,一场春风花香四溢。”母亲的目光变得悠远,“那花秀气,不像这木棉,大气。”
“北方的花开得含蓄,南方的花开得奔放。”妻子说,“就像北方人说话做事都留着几分,南方人热情直接。但都是咱们中国的花,中国的土地。”
一朵木棉花旋转着落在我肩头。我拾起它,想起传说中木棉是英雄的鲜血染红的。而此刻,在这和平年代,它红得如此坦然,如此喜悦,仿佛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丰饶与安宁。

三、漫步
我们沿着昌化江慢慢行走。江水碧绿清澈,倒映着岸边的木棉和远处的青山。偶尔有渔船划过,船头的渔人朝我们挥手。母亲也笑着挥手回应。
“这里的人真热情。”她说。
继续前行,路旁的田野里,早稻已经插下,嫩绿的秧苗整齐排列。田边立着牌子:“七叉镇优质稻米示范基地”。几个农民正在田间忙碌,看到我们,直起身子擦擦汗,露出淳朴的笑容。
“如果,遇‘稻’美好,会有木棉之恋吗?”妻子忽然念出我诗里的句子,然后自己笑了,“现在我知道答案了——木棉守护着稻田,稻田滋养着村庄,这就是最好的相遇。”
是啊,我想。木棉花开在春耕时节,那绚烂的红是献给大地、献给耕耘者的礼赞。而当稻谷金黄时,木棉已结出棉絮,准备为新的生命远行。这种生命的接力,在这片土地上已循环了千百年,只是在今天,才显得格外丰盈饱满。
四、高处
午后,我们登上附近的小山坡。从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七叉镇——红的是木棉,绿的是稻田,白的是民居,蓝的是天空,昌化江如一条玉带串联起所有色彩。远处,海南环岛高铁如银色丝线划过田野,偶尔有列车驶过,带来轻微震颤,旋即又归于宁静。
我们三人并排坐在山坡上,看风过处,木棉花瓣如雨飘落。有些落在我们身上,母亲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收集起来,说要带回去做成书签。
“在吉林时,冬天捡松塔做装饰。在海南,春天捡木棉花做书签。”妻子笑着说,“咱们的生活总是和自然分不开。”
“人本来就是自然的一部分。”母亲说,“只是现在很多人忘了。”
忽然想起我诗里的句子:“从冬天回来/约一朵木棉花/最好从很高的地方看/那一片片的红儿/随着风/满山坡的舞蹈”。此刻,我们正是在很高的地方,看这片红色的舞蹈。只是这舞蹈不再孤单——有绿水青山相伴,有阡陌田园相随,有安居乐业的人们在红云下劳作生息。
远处传来黎族山歌,嘹亮婉转,在山水间回荡。虽然听不懂歌词,但那欢快的旋律与眼前景象如此契合,仿佛木棉花开的声音被谱成了曲。
五、归途
夕阳西下时,我们踏上归程。母亲怀里抱着装满木棉花的布袋,妻子相机里存了些许照片,而我心中装着一整个春天的重量。
回望七叉镇,晚霞将天空染成橘红,与木棉的红交融在一起,分不清哪是天哪是地。炊烟从村落升起,袅袅婷婷,给这幅浓墨重彩的油画添上几笔水墨的写意。
“明年还来吗?”妻子问。
“来。”母亲抢着回答,“这么好看的花,看不够。”
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我忽然明白,我们奔赴的不只是一场花期,更是一个承诺——对美好生活的承诺,对亲情相守的承诺,对这个时代给予我们种种可能的承诺。
从冰天雪地的吉林到四季如春的三亚,从黑土地上的高粱红到海南岛上的木棉红,这不仅仅是地理的迁徙,更是时代的馈赠。若不是国家的繁荣发展,南北交通如此便捷,政策如此开放包容,我们怎能如此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怎能带着母亲跨越四千公里追寻永恒的春天?
木棉花又叫攀枝花,在海南话里与“盼归”谐音。可我觉得,它更像是在诉说“盼来”——盼来春风吹遍大地,盼来生活如花绽放,盼来每个平凡人都能在祖国的山河间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
回到三亚时,华灯初上。母亲醒来,看着窗外璀璨的灯火,轻声说:“咱们的家到了。”
窗外,二月的风暖暖地吹着,带着海洋的气息和隐约的花香。而我知道,在昌化江畔,那些木棉花依然在月光下静静开放,守护着村庄的安宁,等待着下一个黎明,下一次邂逅。
毕竟,所有的春天,都可以从一朵木棉花出发。所有的幸福,都始于脚下这片生机勃勃的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