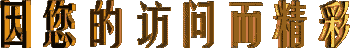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
连载十七
作者:尹玉峰(北京)
赵麻杆儿的唢呐 在榆树杈上炸开
野猫叫般的调子,撞碎“故人西辞”
的晨光。齐老师撞门而入的
大背头油光如盔,钢笔别在
胸前,像枚刺向秩序的针令人费解
云秀的教案飘落,粉笔灰簌簌成雪
1
云祥福死后,赵驼子对臭头、云秀和云娜兄妹仨人格外关心起来。他粗糙的大手总是不经意地搭在臭头肩上,眯着那双被烟熏黄的眼睛说:"臭头啊,你爸走了,有啥难处就跟叔说。"每到饭点,赵驼子就端着自家蒸的玉米面窝头,拎着一罐腌酸菜往云家跑,嘴里念叨着"孩子们正长身体"。
云秀知道赵驼子的心思。这天清晨,云秀正在领着学生们朗读课文。晨光在斑驳的黑板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孩子们清脆的读书声飘出教室,惊飞了屋檐下做窝的燕子。
"故人西辞黄鹤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突然,一阵刺耳的唢呐声打断了朗朗书声。赵麻杆儿不知何时爬上了教室外的老榆树,两条瘦腿悬在半空晃荡。他今天换了件崭新的白布衫,理剪个学生头,脖子上歪歪扭扭地挂个红领巾。
"云老师!俺还给你吹《纤夫的爱》!"赵麻杆儿腮帮子鼓得像塞了两个山核桃,吹出来的调子七扭八歪,活像被踩了尾巴的野猫叫。
教室里顿时炸开了锅。孩子们挤到窗前,几个调皮的男生已经开始学赵麻杆儿鼓腮帮子的滑稽模样。云秀手里的粉笔"啪"地折断,刚要开口训斥,教室后门突然"咣当"一声被撞开。
齐老师抱着一摞作业本冲了进来,今天他特意梳了个油光水亮的大背头,发胶抹得太多,活像顶了个黑漆漆的钢盔。眼镜后的眼睛瞪得溜圆,活像两条受了惊的泥鳅。
"赵麻杆儿!你这是扰乱教学秩序!"齐老师一个箭步冲到窗前,"啪"地合上窗户。
"俺就吹个小曲给云老师解闷!"赵麻杆儿在窗外跳脚,挂在树杈上的唢呐穗子一甩一甩。
齐老师不甘示弱,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诗集:"云老师,我昨晚为你写了首新诗!"他清了清嗓子,用夸张的朗诵腔调念道:"啊!你的眼睛像黑夜里最亮的星——"
"呕——"窗外传来赵麻杆儿做作的干呕声。
云秀气得浑身发抖,手里的教案"哗啦"掉在地上。教室里的孩子们早已笑成一团,有几个甚至爬上课桌看热闹。操场上的村民也三三两两聚拢过来,有人已经开始嗑起了瓜子。
"都给我安静!"云秀一教鞭抽在黑板上,裂缝处的粉笔灰簌簌落下。她突然注意到齐老师胸前别着的那支钢笔——那是去年教师节她获得的奖品,不知何时被齐老师"借"了去。此刻,那支钢笔在齐老师胸前泛着冷光,像一根刺,扎进了她的心里。
窗外,赵麻杆儿不知从哪摸出个破锣,"咣咣"敲了起来:"云老师!俺爸说了,你要是嫁到俺家,天天给你炖小鸡儿吃!"
齐老师闻言立刻冲赵麻杆儿吼道:"赖蛤蟆想吃天鹅肉,做梦去吧,你!"孩子们又是一阵哄笑。
云秀的太阳穴突突直跳,眼前一阵阵发黑,心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呼吸变得困难。
"云老师,俺爸让俺来问问,晚上去俺家吃酸菜白肉不?"赵麻杆儿扒着窗框,汗津津的脑门在阳光下泛着油光。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期待的光芒,那光芒让云秀想起野姜花在月光下摇曳的样子。
齐老师眼镜后的眼睛瞪得溜圆。"赵麻杆儿!现在是教学时间!"他故意把钢笔插进胸前口袋,金属笔夹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手指在口袋上轻轻摩挲,仿佛在抚摸一件珍贵的宝物。
"俺就问问吃饭的事..."窗外的赵麻杆儿趁机把半个身子探进来,变魔术似的摸出个草编蚱蜢。他的手指因为紧张而微微颤抖,草编蚱蜢在他手中显得笨拙而可爱。
齐老师一个箭步冲过去,两人卡在窗框里动弹不得。赵麻杆儿的唢呐硌着齐老师的肋骨,齐老师的钢笔尖扎进了赵麻杆儿的胳膊。操场上的学生呼啦啦围过来,有节奏地喊着:"打起来!打起来!"
"赵麻杆儿,你再胡闹下去,我就叫村支书带人把你抓起来!"云功德校长疾步走来喝斥道。他的声音像一把生锈的锯子,锯着在场每个人的神经。
2
此时,赵驼子盘腿坐在云家炕沿上卷烟,烟叶子碎屑掉在打着补丁的褥子上。"臭头啊,"他吐着烟圈说,"泼儿这些天咋没见着?那丫头野得很,你要见着她,可得帮叔说道说道。"他的手指在烟袋锅上轻轻敲打,发出沉闷的声响,像在敲打某种难以言说的心事。
臭头正蹲在门槛上磨镰刀,闻言手下一顿,刀刃在磨石上发出刺耳的声响。他的手指因为用力而泛白,刀刃上的铁屑像星星一样溅落。他想起泼儿那双野性的眼睛,想起她像野姜花一样在风中摇曳的身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叔,泼儿她..."臭头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他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完整的声音。
赵驼子吐出一个烟圈,看着它慢慢飘散:"臭头啊,你爸走了,咱们得互相照应着。泼儿那丫头,看着野,其实心里比谁都清楚。"
臭头低下头,继续磨镰刀。他的手指在刀刃上轻轻抚摸,仿佛在抚摸自己的未来。他想起父亲生前常说的"人活一口气",又想起自己这些年在乡村的挣扎。他突然觉得,生活就像这把镰刀,需要不断地磨砺,才能保持锋利。
"叔,俺知道。"臭头终于开口,声音低沉而坚定。他的手指紧紧握住镰刀,仿佛握住了自己的命运。
赵驼子满意地点点头,又吐出一个烟圈。烟圈在空气中慢慢扩散,像一朵盛开的野姜花。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那些日子,想起那些在田间地头挥洒的汗水,想起那些与乡亲们一起度过的艰难岁月。他突然觉得,生活虽然艰难,但只要心中有光,就能找到前进的方向。
"臭头啊,你爸走了,咱们得好好活着。"赵驼子站起身,拍了拍臭头的肩膀。他的手掌宽厚而温暖,像一片可以遮风挡雨的树叶。
臭头抬起头,看着赵驼子的背影。那背影虽然佝偻,但却充满了力量。他突然觉得,自己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男子汉。
"叔,俺会的。"臭头说,声音里带着一丝坚定和一丝期待。
赵驼子走出云家,回头看了一眼。云秀还在教室里教孩子们读书,她的身影在阳光下显得格外高大。他想起自己年轻时的梦想,想起那些没有实现的抱负,突然觉得,人生虽然短暂,但只要活得精彩,就没有什么遗憾。
他转身,朝着村口走去。他的脚步虽然缓慢,但却充满了力量。他像一棵老树,虽然枝干已经弯曲,但却依然挺立在风中。
而此时,在教室里,云秀已经平静下来。她看着窗外的野姜花,心里突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情绪。
她转身,看着教室里的孩子们。他们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像一朵朵盛开的野姜花。她突然觉得,自己不再是那个孤独的女子,而是一个可以传递温暖和希望的老师。
"同学们,"云秀说,声音温柔而坚定,"我们继续上课。"
孩子们立刻安静下来,坐得端端正正。云秀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野姜花,开在风里,活在心里。"
她转身,看着窗外的野姜花。那野姜花在风中摇曳,像在诉说着一个古老而美丽的故事。她突然觉得,自己就像那朵野姜花,虽然平凡,但却充满了生命力。
3
赵泼儿蜷在张寡妇家的柴房里,潮湿的稻草扎得她后颈发痒。她盯着墙角那堆发霉的玉米秆,想起前些天在河边洗衣服时,如何把张红说的“云秀在城里当裸模”添油加醋传给云祥福。现在云祥福死了,可能与她传话有关——那些闲话就像沾了血的麦芒,扎得她寝食难安。
“你倒是说话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赵泼儿猛地抬头,额前的碎发被汗水黏成绺。她盯着张红掀开的柴房帘子,手里半碗凉粥冒着馊味的热气。她的心跳得厉害,像被什么攥住了,呼吸也变得困难。她想起云祥福临终前看她的眼神,那眼神里有责备,有失望,还有一丝她看不懂的复杂。
张红忿忿地把粥往地上一墩:“云秀多念了几天书,就以为自己了不起了?我跟你哥处对象光明正大,她要是插一脚,你们老赵家的脸往哪搁?”她涂着劣质口红的嘴一撇,眼神却飘向墙角那堆杂物。她的心里,其实也在害怕,害怕这段婚事真的黄了,害怕自己成了村里的笑柄。
“我是问你,云秀脱光画画的事,你到底听谁说的?”赵泼儿的声音发抖,像风中簌簌作响的玉米叶。她突然站起来,撞翻了张红手里的粥碗。馊粥泼了一地,像摊开的伤口。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却强忍着不肯流下来。她恨自己,恨自己为什么这么轻易地就相信了张红的话,恨自己为什么这么冲动地就把这些话传给了云祥福。
张红冷笑:“无风不起浪呗!我恨死云秀了,搅着我和你哥哥的婚事一时半会儿定不下来。”她转身要走,赵泼儿却一把抓住她的胳膊。她的指甲在赵泼儿手背上划出三道红痕,像三条血色的蚯蚓。
“你撒手!”张红甩开她,指甲在赵泼儿手背上划出三道红痕,“别以为你还是那个跟在云秀身后跑的小丫头!你现在是赵家的‘大姑娘’,该操心的是你哥的婚事!”她说完,转身跑出了柴房,帘子在她身后剧烈地晃动。
柴房里的蜘蛛网在风中轻颤,赵泼儿突然觉得恶心。她撞开张红冲出门,差点踢翻那碗已经馊了的粥。张寡妇在院里晾衣服,晾衣绳上挂着的红裤衩像面羞辱的旗帜。她的心里,充满了委屈和愤怒,她觉得自己被利用了,被张红当成了枪使。
“原来我被你们当枪使了!”赵泼儿的声音惊飞了枣树上的麻雀。她跑过晒着辣椒的场院,红艳艳的辣椒碎末沾在布鞋上,像斑斑点点的血迹。她的心跳得更快了,像有一只小兔子在胸腔里乱撞。她想起云秀以前对她的好,想起她们一起在河边洗衣服,一起在教室里读书,一起在山路上奔跑。那些日子,像野姜花一样,开在风里,活在心里。
4
在村小学门口的老榆树下,赵泼儿撞进一个坚实的怀抱。青草和粉笔灰的味道扑面而来,云功德校长蓝布衬衫上还沾着教室里的白色粉笔灰。
“我正找你呢。”云功德的声音像他用了二十年的搪瓷缸子,磕碰得满是伤痕却依然温厚。他手掌上有开山凿石留下的老茧,轻轻握住赵泼儿颤抖的肩膀时,那些茧子刮擦着她化纤衬衫的线头。他的眼神里,有担忧,有心疼,还有一丝她熟悉的温暖。
赵泼儿想逃,却被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钉在原地。云功德眼角堆叠的皱纹里藏着粉笔灰,他托起赵泼儿的下巴,动作轻柔得像对待课堂上打瞌睡的学生。他的手指粗糙,却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
“你妈妈走的那年冬天,”他指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梁,“你抱着我的腿哭,说要把山凿通,让村里的梨子能卖到山外去,和妈妈坐大面包车到城里见世面!”他说这话时,眼里闪着泪光,像是在回忆一段珍贵的往事。
风掠过玉米地,掀起层层绿浪。赵泼儿突然看见十二岁的自己,举着铁钎跟在大人们身后,凿下的石屑在夕阳里像金色的雨。那时她扎着两条油亮的小辫子,裤脚卷到膝盖,露出被荆棘划伤的小腿。她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期待,对改变命运的渴望。
“老师...”赵泼儿的眼泪砸在云功德磨破的千层底布鞋上。校长从兜里掏出块洗得发白的手帕,上面还沾着红墨水。他的动作很轻柔,像是在擦拭一件珍贵的宝物。
“你记得吗?那年春天。”云功德指向远处云雾缭绕的山梁,那里的岩壁上还留着歪歪扭扭的红色标语——“愚公移山”。“你举着铁钎跑在最前头,辫梢上系着红头绳,像只小山雀。”他说这话时,脸上露出了笑容,像是在回忆一段快乐的时光。
记忆突然鲜活起来。赵泼儿看见十二岁的自己穿着打补丁的衣裳,胶鞋露出两个脚趾,却笑得比崖畔的野花还灿烂。那时她和云秀共用一把铁钎,跟在云功德校长身后,你凿一会儿我凿一会儿,手心磨出血泡也不肯休息。云秀总爱在休息时念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她的声音清脆,像山间的溪流。
深秋里的晨读课,赵泼儿总爱把冻红的手偷偷伸进云秀的秋衣袖筒。两个小姑娘挤在教室最后一排,合看一本被翻烂的《愚公移山》插图本。窗户缝里钻进来的秋风,把云秀朗诵的声音吹得发颤:“遂率子孙荷担者三夫...”
“啥叫荷担?”赵泼儿往手心哈着白气,在课桌上画了三个火柴人扛扁担。她的心里,充满了对知识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执着。
“就是扛着开山工具!”云功德校长突然出现在她们身后,粉笔灰簌簌落在两个小姑娘交握的手上。云校长从兜里掏出两块烤得焦黄的地瓜,掰开的瞬间甜香弥漫了整个教室,“下午劳动课,你俩负责给开路的叔叔们送热水。”
那天傍晚的夕阳特别红,像把云秀的红领巾染得更艳了。十二岁的赵泼儿扛着比自己还高的铁钎,鞋尖踢着碎石往山路上跑。新发的劳动布手套太大,她索性摘下来塞给云秀:“你手嫩,别磨出水泡!”她的心里,充满了对朋友的关心,对共同目标的追求。
“咱们比赛!”云秀突然指着崖壁上用石灰画的横线,“看谁先凿到标记处!”她辫梢上的红头绳在风里一跳一跳,像两簇小火苗。两个小姑娘的欢笑声惊飞了松枝上的麻雀,铁钎撞击岩石的叮当声,和远处大人们的号子声混在一起。她们的心里,充满了对胜利的渴望,对改变命运的期待。
赵泼儿记得特别清楚,那天她凿下来的第一块碎石有巴掌大,灰白色的石面上带着金色的细闪。云秀用红领巾包着石头跑去给校长看,云校长蹲下来用钢笔在石头上画了个小太阳:“等路修通了,你俩坐着大汽车去县里领三好学生奖状!”
“我要当女司机!”赵泼儿突然大喊,惊得树上残存的黄叶扑簌簌落下。她看见云秀眼睛亮晶晶地望着盘山公路的雏形,突然小声说:“我想当校长这样的老师。”她的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对改变命运的渴望。
放学的钟声在山谷里回荡时,两个小姑娘并排蹲在溪水边洗手。赵泼儿突然撩起水花,冰凉的溪水溅到云秀脸上:“拉钩!等路修好了,你教书我开车,咱们永远不分开!”
夕阳把她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两根翘起的小拇指影子,像山路尽头即将升起的月牙。她们的心里,充满了对友谊的珍视,对共同未来的期待。
5
赵泼儿突然剧烈颤抖起来。她想起长大后自己怎么学着城里女人往脸上抹劣质粉底。那些夜晚,KTV的霓虹灯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扭曲得像条蜕皮的蛇。她想起自己如何在酒桌上强颜欢笑,如何把云秀的诗集扔进垃圾桶,如何对张红说“云秀该嫁人了”。她的心里,充满了对过去的悔恨,对现在的迷茫。
“老师...”赵泼儿的声音沙哑得像生锈的铁,“我错了...”她的眼泪终于流了下来,像断了线的珠子。
云功德轻轻拍着她的背,像拍着一块被风化的石头。“错的不是你,”他说,“是这山,这路,这人心。”他指向远处开凿的山路,“你看,铁钎还在,石屑还在,野姜花还在。”他的话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对改变命运的坚定。
赵泼儿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在山路的裂缝里,几朵野姜花正顶着碎石绽放,白色的花瓣上沾着红色的铁锈,像被血染过的雪。她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力量,像野姜花一样,坚韧而顽强。
“老师...”赵泼儿突然跪下来,双手抠进泥土里,“我要把铁钎找回来,把路修通,把云秀的诗集捡回来...”她的心里,充满了对过去的救赎,对未来的承诺。
云功德扶起她,手掌上的老茧硌着她的皮肤。“铁钎在你心里,”他说,“路在你脚下,野姜花在你眼里。”他指向她额头,“这里,还留着十二岁那年的红头绳。”他的话里,充满了对她的鼓励,对未来的期待。
“老师...”赵泼儿的眼泪又砸下来,“我...我想和云秀和好...”她的心里,充满了对友谊的渴望,对过去的悔恨。
云功德笑了,眼角的皱纹里盛着午后的阳光::“我想,她也在等你,等你把铁钎磨亮,等你把路修通,等你把野姜花种满山梁。”
教室里忽然传来孩子们的读书声,是云秀在领诵《愚公移山》。当年她们一起在灯下抄写的课文,现在正从崭新的玻璃窗里飘出来。赵泼儿忽然发现校门口那棵老槐树上还刻着两道歪扭的划痕——那是她和云秀比身高时用柴刀刻下的。
云功德轻轻按住赵泼儿颤抖的肩膀,这个动作让赵泼儿想起母亲去世那天,校长也是这样按着她的肩膀说:"哭吧,哭完记得你妈妈最盼你成什么人。"现在他的手掌依然温暖,却比十几年前多了许多裂口,像老松树的树皮。
"泼儿啊,"校长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展开是张泛黄的奖状,"全县小学生劳动模范"的字迹已经褪色,"你妈妈要是看见你现在..."
一滴泪砸在奖状上,晕开了钢笔写的"赵"字。赵泼儿看见泪珠里倒映着小小的自己,扎着红头绳,举着铁钎,身后是漫山遍野怒放的野姜花。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