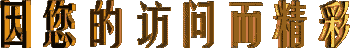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
连载十五
作者:尹玉峰(北京)
晨雾里,铜铃的叮当切开寂静
赵驼子的声音砂纸般磨过铁皮
"哭!都给我哭出声来”
灵幡下, 臭头的眼泪
混着债务,在孝衣上画下潮湿
的地图;野姜花从云秀的发髻
跌落飘散,白纸马驮着
金元宝,赵驼子的铃铛
摇响了如意算盘,林松岭的柳枝
抽打着空气,画下了扭曲的热浪
1
赵驼子对办丧事的确有一套,他佝偻着背,在院子里来回走动,沙哑的嗓音指挥着众人。他那佝偻的身躯里,藏着几十年操持丧事的经验与算计。每一次弯腰,都像是从岁月深处挖出的一把辛酸与狡黠。他穿着一件洗得发黄的白汗衫,后背洇出一大片汗渍,这汗渍在阳光下泛着微光,仿佛是他忙碌与焦虑的见证。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青筋凸起的小腿,那青筋如同蜿蜒的蛇,诉说着他身体的疲惫与岁月的侵蚀。他先是指挥几个年轻汉子搭灵棚,木桩子夯进松软的泥土里,白布幔子一抖开,立刻招来几只绿头苍蝇,嗡嗡地绕着布幔打转。赵驼子看着那苍蝇,心里暗想:“这丧事一开,各种污秽都来了,就像人生里的麻烦,躲都躲不掉。”他佝偻着身子,指挥着汉子们调整木桩的位置,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往左点,再往左点,这灵棚搭歪了,死者不安生,活人也不舒坦。”
临时组建的鼓乐队很快凑齐了人手——赵驼子自己打铜锣,铜锣边缘有个凹坑,敲起来声音发闷。那凹坑是他去年在赌桌上与人争执时,被对方用铜锣砸的。每次敲响这铜锣,他都会想起那场赌局,想起自己输掉的银子,心里一阵刺痛,可表面上却装出一副专注的模样。赵麻杆儿吹唢呐,他瘦得像根麻秆,腮帮子却鼓得老高,唢呐声又尖又利,刺得人耳膜生疼。赵麻杆儿吹唢呐时,心里盘算着:“吹完这场,又能赚几个钱,够不够买酒喝。”他的目光时不时瞟向赵驼子,想看看这位主事人是否满意自己的表演。打鼓的是村东头的王铁柱,光着膀子,一身横肉,鼓槌砸在鼓面上,震得地上的土渣直跳。王铁柱打鼓时,想着自己家里的婆娘和孩子,这丧事的钱能给他们改善一下生活。吹箫的是个外乡人,姓刘,总低着头,箫声呜呜咽咽,像是有谁在哭。刘姓外乡人吹箫时,思绪飘回了遥远的故乡,那里有他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可如今他漂泊在外,只能靠这吹箫的营生糊口,心里满是孤独与无奈。
灵堂两侧摆满了花圈,纸马、金元宝、童男童女一应俱全。纸马的眼睛画得极大,黑漆漆的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人,仿佛在诉说着死亡的冰冷与无情。赵驼子看着这些纸扎,心里琢磨着:“这些玩意儿,活人看着热闹,可死者能知道啥?不过是给自己赚点钱罢了。”童男童女的脸蛋涂得煞白,腮帮子上却抹了两团艳红的胭脂,嘴角诡异地向上翘着。那翘起的嘴角,像是在嘲笑活人的愚昧与对死亡的恐惧。灵幡上的墨迹还没干透,被风一吹,“奠”字的一撇晕开了,像一道黑色的泪痕。赵驼子看着那晕开的墨迹,心里泛起一丝不安,仿佛预示着这场丧事不会那么顺利。
院落后头,各家各户搬来了桌椅,木头板凳摞得老高。张寡妇系着围裙在临时搭的灶台前忙活,大铁锅里的油烧得噼啪作响,菜刀剁在案板上的声音又急又密。张寡妇一边忙活,一边想着:“这丧事办得越大,自己就越能多赚点钱,家里的日子也能好过些。”她的眼神里透着疲惫与对生活的无奈。张红和几个妇女蹲在井台边洗菜,手在冷水里泡得发白,指甲缝里塞满了泥垢。张红洗菜时,心里惦记着家里的孩子,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好好吃饭,有没有调皮捣蛋。她手上的泥垢,仿佛是生活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洗不掉,也抹不去。
傍晚时分,酒足饭饱的赵驼子抹了抹油光光的嘴,心里暗自得意:“这丧事办得还算顺利,钱也赚了不少。”他招呼赵麻杆儿和另外两个吹鼓手出了院子。过了一会儿,他们穿戴整齐地回来了——赵麻杆儿套了件皱巴巴的黑布褂子,袖口还沾着昨日的酒渍。赵麻杆儿心里想着:“这黑布褂子虽然旧了点,但好歹能遮遮身子,在丧事上不能太寒酸。”赵驼子换了双胶鞋,鞋帮上沾着新鲜的泥巴。他换鞋时,心里盘算着:“等下要做法事,得装得像个样子,不能让死者家属挑出毛病。”
2
他们先绕到屋子后院转了一圈。后院的老槐树下积着一洼雨水,几只蛤蟆蹲在水边,鼓着眼睛瞪着他们。赵麻杆儿的唢呐声惊起一群麻雀,扑棱棱地从树梢飞走,落下几片羽毛。赵驼子看着那飞走的麻雀,心里闪过一丝不祥的预感,仿佛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转到灵堂前,臭头、云秀、云娜跪在草席上,低着头抽噎。汗珠子顺着他们的鬓角往下淌,在草席上洇出深色的痕迹。臭头跪着时,心里满是悲伤与无助,父亲去世了,他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云秀和云娜则沉浸在失去父亲的痛苦中,泪水不停地流。
赵驼子他们并排站在棺材前,铜锣、唢呐、鼓、箫一齐响了起来,调子又高又急,惊得院墙外的野狗跟着嚎了两声。赵驼子听着那野狗的嚎叫,心里越发不安,但他强装镇定,继续指挥着乐队。赵驼子把一只手竖在嘴边,先是随着乐队的调子“啊啊”地唱,嗓子眼里像是卡了口痰。他唱的时候,心里却在想:“这唱词得糊弄过去,不能让死者家属看出破绽。”接着他含混不清地念叨:“房前房后,妖魔尽无,儿女已大,自有后福。”说这话时,他的眼睛瞟向棺材,嘴角抽了抽。那嘴角的抽动,泄露了他内心的紧张与算计。林松岭一直抱胸站在旁边。当赵驼子念叨“自有后福”时,他分明看见赵驼子的右手小拇指勾了勾——那是个赌钱时耍诈的手势。林松岭心里一阵冷笑:“这赵驼子,连丧事都不放过,还想从中捞好处。”灵堂里的灯泡突然闪了闪,投下的影子在棺材盖上扭动,像有什么东西要爬出来。林松岭看着那扭动的影子,心里琢磨着:“这丧事背后,肯定藏着不少见不得人的事。”
夜风卷着纸灰打着旋儿,一只蛾子扑向灯泡,“啪”地一声烧焦了翅膀,落在棺材前头的供桌上,腿还在不停地抽搐。赵驼子看着那烧焦的蛾子,心里一阵发毛,但他强作镇定,继续他的表演。赵驼子的声音突然拔高,沙哑的嗓门在灵堂里炸开:“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他一边念,一边从怀里摸出几张黄纸符,手指蘸了唾沫,“啪”地贴在棺材两侧。纸符上的朱砂字歪歪扭扭,像是几条盘曲的红蜈蚣。赵驼子贴符时,心里暗自祈祷:“这符可别出问题,不然这丧事就砸了。”他越念越快,唾沫星子飞溅,枯瘦的手在空中划着古怪的弧线,像是在驱赶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云秀跪在草席上,膝盖被碎石子硌得生疼。她抬头,怯生生地问:“赵叔,你在念叨啥呢?”赵驼子猛地转头,浑浊的眼珠子瞪得溜圆:“我在做法事!少插嘴!”他声音尖利,吓得云秀一哆嗦,赶紧低下头。云秀心里满是委屈:“我只是想知道父亲能不能安息,这赵叔怎么这么凶。”林松岭站在人群后头,冷笑一声:“荒唐!”他声音不大,但足够让赵驼子听见。赵驼子被林松岭的冷笑激得脖子一梗,浑浊的眼珠里闪过一丝慌乱,但很快被故作镇定的神色掩盖。他佝偻着背,故意将铜锣敲得更响,沙哑的嗓音在灵堂里回荡:“活人不懂死人事,莫要乱嚼舌根!这唢呐一响,阎王殿门开,童男童女引路,纸马驮魂过奈何桥——”他猛地转身,枯瘦的手指直戳林松岭,“你这城里的大教授,莫不是嫌丧事不够热闹?”
林松岭抱臂而立,目光如刀,扫过灵堂里那些纸扎的童男童女。那些煞白的脸蛋上,胭脂红得刺眼,嘴角的弧度像在嘲笑活人的愚昧。他压低声音,却字字清晰:“赵叔,这‘后福’是给谁的后福?赌钱的手势都使出来了,莫不是连死人的钱也要诈?”人群里一阵窃窃私语,几个抬棺的汉子手一抖,木桩子差点歪斜。赵驼子脸色骤变,后背的汗渍在昏黄的灯泡下泛着油光。他跺脚,卷起的裤腿下青筋暴起:“放肆!我赵驼子办丧事三十年,哪个村不敬我三分?云祥福的魂儿还在天上飘,你倒咒他不得安息!”他转向跪着的云秀,唾沫星子飞溅,“云秀丫头,你爹生前最信我,你倒听外人嚼舌?”云秀的肩膀猛地一颤,草席上的泪痕更深了。云秀心里委屈又无助:“父亲生前确实信任赵叔,可如今他走了,这丧事办得这么复杂,我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后院灶台边的张寡妇扯着嗓子喊:“驼子哥,油锅要炸了!豆腐下锅了没?”赵驼子趁机岔开话题,佯装呵斥:“急什么!丧事规矩大过天!”
灵堂里,唢呐声突然尖啸起来,赵麻杆儿的腮帮子鼓得像气球。他吹唢呐时,心里想着:“这赵驼子今天怎么这么紧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林松岭冷笑未落,一只野狗在院墙外狂吠,震得纸灰打着旋儿扑向供桌。烧焦的蛾子腿抽搐几下,终于不动了。赵驼子摸出黄纸符,朱砂字歪如蜈蚣,他贴符的手却抖了——林松岭的目光钉在他小拇指上,那里还残留着赌桌的狡黠。赵驼子心里一阵发虚:“这林松岭的眼神太锐利了,好像能看透我的一切。”夜色渐浓,纸马的眼珠子在风中眨动,童男童女的嘴角翘得更高。林松岭的冷笑化作一声长叹:“这‘后福’,怕是先要应验在活人身上了。”
3
赵驼子猛地扭头,眼神像刀子一样剜过去。他腮帮子上的肌肉抽动两下,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你懂个屁!"赵驼子的愤怒并非全因林松岭的嘲讽,更因为他敏锐地察觉到,这个外来的教授正在动摇他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的权威。作为村里唯一的"专业"丧葬师,赵驼子深知自己的地位建立在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传统仪式的迷信上。林松岭的质疑如同一把利刃,直指他赖以生存的根基。赵驼子下意识摸了摸腰间那枚祖传的铜铃,那是他父亲传给他的,铃身上刻着"驱邪避灾"四个字,如今在他看来,更像是讽刺。
灵堂里霎时安静下来,只剩下长明灯的灯芯"噼啪"爆了个灯花。云秀站在父亲遗像前,手指无意识地绞着孝衣的衣角。她想起父亲生前总爱在院子里种野姜花,说那淡紫色的花朵能驱散晦气。如今那些花被赵驼子说成"阴间路上的引魂香",插在父亲的遗像前。云秀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她不明白为什么父亲生前最爱的花,死后却要被赋予如此不祥的寓意。云娜紧挨着她站着,银镯子随着她的颤抖发出细微的声响,那声音让她想起父亲生前教她认星星时的夜晚。
出殡这天,天刚蒙蒙亮,雾气还没散尽。赵驼子走在最前面,手里拎着个铜铃,走三步摇一下。"叮——叮——"的铃声在晨雾里显得格外刺耳。赵驼子知道,这铃声不仅是召集村民的信号,更是他权威的象征。
"出殡最宜放悲声,后代儿孙运顺通!"他扯着嗓子喊,声音像是砂纸磨过铁皮,"哭!都给我哭出声来!"赵驼子的喊声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虑。他知道,如果这次丧事办得不体面,云祥福的家人可能会找其他村子的人来主持,那样他就失去了这笔收入,更重要的是,让臭头做自己女儿赵泼儿的接盘侠,让儿子赵麻杆儿娶到云秀。
臭头打着灵幡走在最前头,闻言立刻扯开嗓子嚎起来:"爸啊——你怎么就扔下我们走了啊——"臭头的哭声并非全为父亲,更多的是为自己。作为长子,他本应继承父亲的木匠手艺,却因沉迷赌博欠下巨额债务。父亲的去世让他失去了最后的依靠,也失去了村里人的尊重。他哭得情真意切,鼻涕眼泪糊了一脸,时不时还用孝袍袖子抹一把,袖口很快变得湿漉漉、亮晶晶的。
云秀和云娜跟在后面,两人搀扶着,嘤嘤地啜泣。云娜哭得肩膀一耸一耸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滴在胸前的孝布上,晕开一片深色。想起村里老人总爱讲《聊斋》里的故事,那些关于鬼魂和阴间的传说如今成了姐俩最大的恐惧。云秀则低着头,眼泪吧嗒吧嗒砸在土路上,溅起小小的灰尘。
再往后是抬棺材的八个壮汉。棺材是厚重的松木,刷了黑漆,在晨光中泛着冷森森的光。抬棺的杠子压在肩膀上,很快就把衣服磨出了血印子。他们咬着牙,额头上的青筋暴起,哪还有力气哭?只能从鼻子里发出"哼哧哼哧"的喘息声。
最后面是扛纸马、抬元宝的人。纸马足有一人高,两个小伙子一前一后扛着,马脖子上的铃铛"哗啦哗啦"响。抬元宝的筐子更沉,里面塞满了金灿灿的纸元宝,压得扁担"吱呀"作响。这些人早就汗流浃背,脸憋得通红,哪还顾得上哭丧?有个叫小栓的年轻人,是村里新来的小伙子。他第一次参加这样的仪式,既感到新奇又感到困惑。纸马和元宝在他看来不过是些纸糊的玩意儿,不明白为什么人们要如此郑重其事地对待它们。他的困惑里,既有对传统的不理解,也有对自己未来的迷茫。
4
赵驼子回头看了一眼,不满地皱起眉头。他快步走到队伍中间,抡起铜铃在几个抬棺材的汉子耳边猛地一摇——"叮铃铃!""哭啊!怎么不哭?"他厉声喝道,"云祥福在下面听着呢!你们这样,让他怎么安心上路?"赵驼子的呵斥并非全为仪式,更多的是维护自己的权威。他知道,如果抬棺的人不哭,整个仪式就会显得不完整,那样他的收入就会受到影响。几个汉子被他吓得一激灵,只好扯着嗓子干嚎起来:"云伯伯——您走好啊——"声音干巴巴的,像是老鸹叫。
赵驼子这才满意地点点头,继续摇着铃往前走。雾气渐渐散了,阳光照在送葬队伍上,把每个人的影子拉得老长。那些影子歪歪扭扭地爬过田埂,像一群蹒跚的鬼魂。林松岭和云功德并肩走在送葬队伍的中段。林松岭穿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衬衫,袖口卷到手肘,露出小臂上几道颜料留下的洗不净的色斑。他手里捏着根随手折的柳枝,无意识地抽打着路边的野草。露出野姜花,成了他在这片陌生土地上唯一的慰藉。
云功德则是一身板正的灰布中山装,胸前的钢笔在阳光下泛着金属光泽,走起路来腰杆笔直,像是随时准备上台讲课。云功德作为村小学校长,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却也不得不承认这些传统仪式在村民心中的分量。他的钢笔里藏着他对未来的希望——希望有一天,村里的孩子们能走出大山,不再被这些繁文缛节所束缚。然而,每次看到村民们虔诚地参与这些仪式,他又不得不承认,这些传统或许有其存在的价值。
"这赵驼子,倒是会挑时候停。"林松岭压低声音,用柳枝指了指前方。云功德说:"老规矩了,停一次赏一次,美其名曰'买路钱'。"云功德的话语里带着一丝无奈。作为校长,他本应倡导科学精神,却也不得不参与这些仪式。他的内心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摇摆,既想改变现状,又怕失去村民的信任。
果然,赵驼子又在田埂边站住了。他装模作样地整理了下孝帽,铜铃往腰间一别,干咳两声。臭头立刻会意,小跑着上前,从怀里掏出个红纸包塞进赵驼子手里。赵驼子捏了捏厚度,这才满意地一挥手,铜铃"叮当"一响,队伍继续前行。赵驼子的动作熟练而自然,仿佛这是他与生俱来的本能。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每次收取"买路钱"时,他都会想起儿子在城里的生活,那些现代化的丧葬方式让他感到自己的职业正在被时代淘汰。
林松岭看见云功德嘴角抽了抽。这位小学校长从兜里摸出块手帕,擦了擦头上的汗,低声说:"这已经是第五次了。"云功德的手帕上绣着一朵小小的野姜花,那是妻子小桃绣的。每次看到这朵花,他就会想起妻子小桃曾经说的话:"功德,你要坚持,村里的孩子们需要你。"这句话成了他坚持的动力,却也让他在这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感到无比孤独。
5
涧水河在正午的阳光下泛着碎银般的光。河水不深,刚没过脚踝,河底的鹅卵石被冲刷得圆润光滑。赵驼子喊停时,抬棺的汉子们如蒙大赦,赶紧把棺材架在事先准备好的条凳上。"就这儿了!"赵驼子把铜铃往地上一搁,三步并作两步奔向纸马。那纸马足有一人多高,马鬃是用黑麻绳粘的,马眼画得溜圆,在烈日下显得格外瘆人。赵驼子从后腰抽出一把柴刀,刀背在阳光下闪着寒光。
"咔嚓!"麻绳应声而断。纸马的左前腿突然松脱,整匹马向前倾斜,像是要活过来奔跑似的。几个妇女吓得往后缩了缩。赵驼子的动作熟练而果断,仿佛这是他与死神之间的某种契约。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每次进行这样的仪式,他都会想起自己年轻时第一次主持丧事的场景,那时的他充满敬畏,如今却只剩下熟练和麻木。
"都堆到一块儿!"赵驼子指挥着,额头上油亮的汗珠顺着皱纹往下淌,"花圈搁底下,元宝箱压上头,童男童女摆两边——对对,脸朝西!"云秀抱着童女,手指不小心戳破了纸人的脸颊。她"啊"了一声,赶紧用袖子去擦,结果越擦越花,童女的半边脸变成了模糊的红色。林松岭注意到,那个纸童男的笑容画得特别夸张,嘴角几乎咧到耳根,活像个索命的鬼差。林松岭的内心泛起一阵寒意,这些纸人在他看来不过是些纸糊的玩意儿,却承载着村民们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来世的期盼。
赵驼子摸出个塑料打火机,"咔嗒"一声,火苗蹿起老高。他蹲下身,火苗舔上花圈的纸花,"轰"地一下,整个火堆瞬间被点燃。热浪扑面而来,所有人都往后退了几步。赵驼子的脸上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满足,这火苗不仅烧掉了纸糊的祭品,也烧掉了村民们对死亡的恐惧。他的内心却并不轻松,每次看到这样的火焰,他都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对死亡的敬畏,如今却只剩下对利益的追求。
火势越来越猛。纸马的鬃毛最先卷曲、碳化,马眼在火焰中慢慢融化,像是流下了黑色的眼泪。元宝箱里的金箔纸遇火即燃,爆出无数细小的火星,在空中组成转瞬即逝的金色星河。童男童女的彩衣很快化为灰烬,露出里面竹篾扎的骨架,在火中扭曲变形,发出"噼啪"的爆响。林松岭摸出速写本,飞快地勾勒着眼前的景象。他的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捕捉着火堆上方扭曲的热浪,以及众人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的脸。林松岭的内心充满矛盾,他既想记录下这些真实的场景,又对这些仪式感到深深的厌恶。他的速写本里,不仅有眼前的景象,更有他对这片土地和这些人的复杂情感。
"差不多了。"赵驼子拎起个军用水壶,壶嘴对准灰堆一倾——"嗤!"滚烫的水蒸气腾空而起,灰烬中未燃尽的纸片顿时化作白烟。一股混合着焦糊味和香灰味的怪味弥漫开来。云秀突然打了个喷嚏,她揉着鼻子往后退时,不小心踩到了那朵野姜花。淡紫色的花瓣被踩得粉碎,林松岭的内心泛起一阵惋惜,这朵花本应是云秀最爱的,如今却成了这场仪式中的牺牲品。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