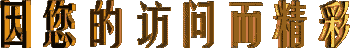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连载十
不寻常的清晨
作者:尹玉峰(北京)
山峦的呼吸凝成薄纱,轻轻
覆住沉睡的山村;苹果梨树
在晨风里颤动,野姜花
的香气,是昨夜未说尽
的梦。青果在齿间迸裂,酸涩
的汁液,或是少年莽撞的印记
露水在叶脉间游走,像
时光留下的指纹。树枝
轻叩地面,敲碎了涧水河的寂静
敲开了入伏头一天不寻常的清晨
1
涧水河村的清晨裹着一层薄雾,像给山峦披了件纱衣。薄雾在山谷间缓缓流动,时而聚拢成团,时而散开如烟,将远处的山峦勾勒得朦胧而神秘。入伏头一天,老天爷竟格外开恩,没按往年的惯例闷热难当,反倒送来阵阵凉风,吹得果园里的梨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在窃窃私语。这凉风带着山间特有的清新,夹杂着野姜花的淡淡香气,轻轻拂过人们的脸颊,让人顿觉神清气爽。
云祥福蹲在苹果梨树下检查叶片,粗糙的手指拂过叶背,沾了一手露水。他眯起被农药熏得发红的眼睛,眼神中透着一丝疲惫,但更多的是对果园的关切。这些年,他守着这片果园,就像守着自家的孩子,每一片叶子、每一颗果实都牵动着他的心。他朝正在搅拌药桶的儿子喊:"臭头,把喷头拧紧些,别又漏一身。"声音里带着几分父亲的威严,也夹杂着对儿子粗心毛病的无奈。
"知道啦爸!"臭头用袖子抹了把汗,古铜色的胳膊上青筋凸起。他生得虎背熊腰,活像棵移动的老梨树,那宽厚的肩膀和结实的肌肉,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只见他顺手揪下个青苹果梨,咔嚓就是一口,酸得整张脸都皱成了晒干的葫芦。他一边嚼着,一边在心里嘀咕:“这果子咋这么酸,还没熟透呢,不过倒挺开胃的。”嘴角还挂着几滴酸水,顺着下巴往下淌。
"作死啊你!"云祥福抄起根树枝作势要打,脸上的表情从关切瞬间转为愤怒。他心疼那些还没成熟的果子,那可是他辛苦培育的希望。“这果子现在吃跟啃树皮有啥两样?等它熟了,甜得能让你舌头打卷儿!”他一边说着,一边挥舞着树枝,仿佛真要给儿子一个教训。
臭头挤眉弄眼地嚼着,酸水顺着嘴角往下淌,他却不以为意,反而觉得父亲这反应挺有趣。“我尝尝熟到什么成色了,也好心里有个数,等果子熟了,咱就能卖个好价钱。”他想着,果园的收入可是家里重要的经济来源。话音未落,突然听见灌木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动静。那声音细微而急促,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快速移动,让臭头的心猛地一紧。
父子俩同时转头,只见赵泼儿从坡上慌慌张张冲下来,花布衫被荆棘勾开了线,露出小半截雪白的腰。她脸上满是惊恐,眼神慌乱地四处张望,嘴唇直哆嗦,仿佛遇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蛇……蛇……”她颤抖着吐出这两个字,声音微弱而带着哭腔。
臭头的瞳孔骤然收缩成两个黑点。他看见那条蝮蛇正盘成弹簧状,黑褐相间的圆斑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蛇信吞吐间露出粉红色的口腔。那蛇的三角脑袋高高昂起,眼神冰冷而充满杀机,仿佛在宣示着这片地盘的主权。臭头的心跳瞬间加快,一股强烈的恐惧和紧张涌上心头。他想起村里老人讲过的关于蝮蛇的故事,知道这种蛇毒性极强,被咬一口可能就会丧命。但他又不想在赵泼儿面前显得胆小,于是强装镇定。
"别动!"他低吼一声,声音像是从胸腔里挤出来的。那声音低沉而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赵泼儿僵在原地,连睫毛都不敢眨一下,只有鼻翼在急促地翕动。她紧紧盯着那条蛇,身体微微颤抖,仿佛随时都会瘫软在地。臭头在心里默默给自己打气:“不能慌,得想办法把蛇赶走或者抓住,不然赵泼儿会有危险。”
臭头的动作突然变得异常轻巧。这个平日走路都能震落梨花的莽汉,此刻竟像只捕食的狸猫,解放鞋碾着碎草悄无声息地向前移动。他的右手五指微微张开,左手则保持着随时出击的姿势。每一步都小心翼翼,生怕惊动了那条危险的蝮蛇。他的大脑飞速运转,思考着如何应对这突如其来的危机。
蝮蛇似乎察觉到了危险,三角形的脑袋昂得更高了,颈部扩张成扁平的威胁姿态。那蛇身上的鳞片在阳光下闪烁着诡异的光芒,仿佛在警告臭头不要靠近。就在蛇信再次探出的瞬间,臭头的右脚猛地跺地——
"啪!"
枯枝断裂的脆响让毒蛇明显一怔。臭头抓住这电光石火的时机,膝盖如同压紧的弹簧突然释放,整个人矮身扑出。他的右手化作一道残影,精准地钳住蛇颈七寸处,粗糙的拇指死死扣住蛇头下方的凹陷。那一刻,他感觉自己的手指被蛇身紧紧缠绕,那冰冷而滑腻的触感让他心里直发毛,但他还是紧紧抓住,不敢有丝毫松懈。
"嘶——"毒蛇扭动着露出尖牙,黄白色的毒液从牙尖渗出。臭头不慌不忙地抬起右脚,厚重的鞋底稳稳踩住乱甩的蛇尾。他手臂肌肉暴起,像拉弓弦一样将蛇身绷得笔直。他咬紧牙关,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住,不能让它挣脱,不然赵泼儿就危险了。”
"走你!"随着一声暴喝,他腰胯发力,整条蛇被抡圆了甩出去。蛇身在半空中划出一道黑褐色的弧线,鳞片反射着阳光,宛如一条飞舞的鞭子,最终消失在五十米开外的草丛里。臭头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他甩了甩手腕,那里还留着蛇鳞冰凉的触感。他转头看向赵泼儿,发现这泼辣娘们儿的脸白得跟新磨的豆腐似的,嘴唇不住地哆嗦。他露出一丝得意的笑容,觉得自己刚才的表现还挺英勇。
2
"没事儿了。"他咧嘴一笑,"这玩意儿看着唬人,其实..."话没说完,赵泼儿就软绵绵地倒了过来。
"哎呀妈呀!"赵泼儿惊魂未定,整个人像被抽了骨头似的软进臭头怀里。她丰腴的身子撞上来时,臭头只觉得胸口砸进一团温热的棉花,两颗饱满的果实隔着薄衫在他胸膛上压得变了形。这莽汉顿时僵成了根拴马桩,两只蒲扇似的大手悬在半空,指头无意识地开合着,活像被滚水烫着的螃蟹。他的大脑一片空白,心跳如鼓,从未有过如此近距离接触女性的身体,那柔软而温暖的触感让他不知所措。
"呜...吓死我了..."赵泼儿带着哭腔的喘息喷在臭头颈窝里,潮乎乎的热气顺着汗毛孔往他血管里钻。她下意识用指甲抠住臭头后背的腱子肉,月牙形的红痕立刻在古铜色皮肤上浮了出来。臭头浑身血液轰地冲到了天灵盖。他闻见赵泼儿发丝里野姜花的味道,那香气清新而独特,混合着她身上淡淡的汗味,形成一种奇异的诱惑。垂眼就能看见她衣领里漏出的半弧雪白,随着抽泣一颤一颤地晃着。这时臭头的身体比脑子动得快,那双晒得皴裂的大手突然铁箍似的勒紧,几乎要把赵泼儿的水蛇腰掐断。两人贴得严丝合缝,他清晰地感觉到对方小腹随着呼吸起伏的弧度,以及自己裤裆里不受控制抬头的变化。他的呼吸变得急促而粗重,脸上泛起不自然的红晕。
"你..."赵泼儿突然瞪圆了眼睛,挣扎着要往后退,却被臭头结实的臂膀困住。这憨货正沉浸在从未有过的柔软触感里,喉结上下滚动着,不自觉地用胯往前顶了顶——赵泼儿脚尖顿时离了地,整个人被托起来半寸。赵泼儿的脸瞬间变得通红,她既有些害羞,又有些恼怒,觉得臭头这举动太过分了。
"云、臭、头!"赵泼儿从牙缝里挤出三个字,脸颊红得能滴出血来。她用力挣扎着,想要摆脱臭头的束缚。
臭头喘着粗气说:“哎哟我的姑奶奶!你进城涮了几个月碗,回来这身段儿——扭得比电线杆上跳舞的母蛇还带劲!昨儿冲村口老爷们儿甩了个飞眼儿,几个年轻一点的,马上要跪地的样子,那些带假牙的糟老头子当场把假牙喷出三米远!“他一边说,一边还沉浸在刚才的冲动中,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言语的轻浮。
”哎哟我的姑奶奶!老黄牛见了你直接尥蹶子改跳舞;你再扭两下,咱村光棍们得集体去卫生院降血压!”赵泼儿一直咯咯笑着,突然曲起膝盖,作势要往男人要害处顶。臭头这才如梦初醒,慌忙松手后退,结果被农药桶绊了个趔趄。两人之间拉出半臂距离,空气中飘着暧昧的腥甜,像熟过头的南果梨裂开了皮。赵泼儿脸上带着狡黠的笑容,臭头则有些尴尬地挠了挠头。
云祥福别过脸去咳嗽两声,眼角余光却瞥见脚边金光一闪。定睛看去,竟是只通体金黄的黄鼠狼,毛色油亮得能照出人影。它正用前爪扒拉着农药桶边缘,琥珀色的眼睛滴溜溜转着,仿佛在评估这桶“神秘液体”的食用价值。云祥福的心里闪过一丝疑惑,这黄鼠狼怎么会对农药桶感兴趣呢?
云祥福的咳嗽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声短促的惊叫:“黄大仙!快别碰那毒水!”他抄起地上的树枝就要驱赶,却见那黄鼠狼后腿直立,前爪合十作揖,尾巴还欢快地摇了两下,活像在表演滑稽戏。这场景让云祥福又气又笑,他没想到这畜生还有这么有趣的一面。
臭头趁机抹了把额头的汗,咧嘴笑道:“爹,这畜生比赵泼儿还精,知道讨饶呢!”话音未落,黄鼠狼突然转身窜向赵泼儿,叼住她裤脚就往灌木丛拖。赵泼儿尖叫着跳脚,花布衫彻底被荆棘撕开,露出大片雪白的后背。她一边挣扎一边喊:“救命啊!色狼成精啦!”那惊慌的模样让臭头忍不住笑出声。
“救命啊!色狼成精啦!”赵泼儿挥舞着双臂,却见黄鼠狼从草丛里拖出个东西——正是她刚才慌乱中掉落的绣花手帕,上面还沾着几片野姜花瓣。臭头蹲下身,捡起手帕嗅了嗅,眼睛突然瞪得像铜铃:“这香……是城里美容院用的香水!”他惊讶地发现,这手帕上的香气竟然如此独特,与村里常见的味道截然不同。
云祥福眯起眼,从农药桶里舀出半瓢水泼在黄鼠狼身上:“滚!再敢偷东西,老子把你毛都染绿!”黄鼠狼抖了抖金黄的皮毛,水珠在阳光下折射出彩虹,它叼着绣花手帕蹿上梨树,转眼消失在枝桠间。云祥福看着黄鼠狼消失的方向,心里琢磨着这畜生是不是真的有什么灵性。
赵泼儿捂着胸口喘气,脸颊绯红未褪:“这畜生……它怎么知道手帕值钱?”她既觉得奇怪,又有些庆幸手帕被找了回来。臭头挠着头傻笑:“可能它闻见你身上的香水味,以为是什么仙丹妙药……”他话没说完,赵泼儿突然扬起手帕,狠狠抽在他脸上:“闭嘴!你尽胡说八道!”她一边说,一边整理着被撕破的花布衫,脸上带着一丝羞涩和恼怒。
远处山雾渐渐散开,露出涧水河村错落的屋舍。野姜花的香气混着农药的刺鼻,在晨风里织成一张无形的网,网住了梨树下的三个人,也网住了这个注定不平凡的清晨。
云祥福趁机把药桶推给儿子:“赶紧喷药!梨树都等着开饭呢!”臭头扛起药桶,却见赵泼儿正弯腰捡树枝,衣领滑落,露出颈间一抹银光——是条细链吊着的野姜花形银坠。他喉结滚动了一下,脚步突然变得沉重,仿佛药桶里装的不是农药,而是滚烫的岩浆。那银坠在阳光下闪烁着光芒,让他忍不住多看几眼,心里泛起一丝涟漪。
3
云祥福别过脸去咳嗽两声,眼角余光却瞥见脚边金光一闪。定睛看去,竟是方才那只通体金黄的黄鼠狼,毛色油亮得能照出人影。它人立而起,前爪作揖般搭在胸前,黑豆似的眼珠滴溜溜转着,竟泛着几分灵动的笑意。云祥福揉眼的功夫,那畜生突然就地打了个旋儿——
刹那间,枯叶纷飞处站着个穿杏黄衫子的姑娘。水蛇腰系着红绸带,裙摆翻飞间露出绣花鞋尖。她手腕脚踝都戴着银铃,转起圈来叮当作响,活像年画里走下来的仙女儿。最奇的是那张脸,明明生得柳叶眉樱桃口,眼梢却吊着几分黄鼠狼的狡黠,冲云祥福咧嘴一笑,露出两颗尖尖的虎牙。
"黄仙姑显灵啦!"云祥福心里咯噔一下。这光景他小时候听跳大神的王婆子讲过——说是修炼成精的黄鼠狼最爱扮俏姑娘,遇见心善的就送姻缘,碰上歹毒的便索命。眼瞅着那"姑娘"越转越快,铃铛声混着山风竟成了调子:"七月梨子八月瓜,九月里来抬花轿哟..."
云祥福正发愣,突然嗅到股骚臭味。低头见真正的黄鼠狼正用尾巴扫他裤腿,蓬松的尾尖沾着露水,在地上画出了个歪歪扭扭的喜字。再抬头时,幻影与实体倏然重合,那畜生冲他作了个揖,滋溜钻进了山杏林。
"爸?爸!"臭头的喊声把他拽回神。再定睛看时,哪有什么姑娘,只有只黄鼠狼正撅着屁股往山杏林里钻。云祥福搓搓老脸,心里却乐开了花:“这是吉兆啊,黄仙姑送姻缘来哩!”
“这么灵啊?” 臭头顺势拉了一下赵泼儿的手,赵泼儿脸颊红得像树上的山杏。她掏出手帕扔给臭头:"谢归谢,可没让你占便宜!"见臭头讪笑着擦汗,她忽然眨眨眼:"你媳妇呢?咋不见来送饭?"
"跟收山货的跑路了。"臭头梗着脖子,声音却矮了半截。
赵泼儿噗嗤笑了:"你们云家真是...啧啧..."她踮脚折了枝山杏,山杏青果衬得指尖更显白嫩,"不过三条腿的蛤蟆难找,两条腿的人多得是,是吧?"
臭头嘿嘿傻笑,突然掰断整根果枝塞给她。赵泼儿也不客气,咔嚓咔嚓啃着青果,酸得直眯眼却说好吃。临走时她抢回手帕,"走啦!改天给你带酸菜饺子!"
云祥福搓着下巴上硬扎扎的胡茬,眯眼望着赵泼儿跑的方向,却与黄鼠狼消失的方向一致。心里头跟揣了只活兔子似的扑腾起来,"老辈人咋说的来着?'黄仙点姻缘,红线拴百年'..."他咂摸着赵泼儿临走时裏带的那股香风。
云祥福立刻蹲下身,捡起地上被黄鼠狼尾巴扫过的落叶,露水在叶脉上勾出个歪歪扭扭的"囍"字。阳光一照,亮晶晶的像撒了层喜糖。他忽然想起三十年前自己娶亲那晚,洞房窗户纸也被什么东西挠得沙沙响,第二天门槛前就摆着对活山鸡——羽毛油光水滑的,颈子交缠成同心结。
"好家伙..."云祥福一拍大腿,裤兜里掉出几个山杏核,骨碌碌滚成个圆圈。他掰着指头算起来:臭头属虎,赵泼儿属马,这不正是"虎马房中乐"的上等婚配?
远处又传来赵泼儿咯咯的笑声,脆生生像刚摘的秋梨。"哎呀,好事啊,好事啊,老云家要添人进口喽!"云祥福美滋滋地啐了口唾沫。
此时望着赵泼儿扭着腰远去的背影,臭头挠挠头,发现手心还留着那截山杏枝。臭头呆立在原地,掌心那截山杏枝突然变得滚烫。赵泼儿的身影拐过晒谷场,像截断的日头影子,可那咯咯的笑声还在他耳膜上蹦跳。
他低头看那截断枝,断茬处渗着黏稠的树浆,沾了灰土的手指无意识摩挲着,竟把树皮搓出淡红的汁水来。远处谁家灶膛爆了个柴火疙瘩,"啪"地一声,惊得他手一抖,断枝上三粒青杏簌簌滚落。臭头突然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里。
云祥福看到儿子这般痴情的样子,凑过来捅捅儿子:"这姑娘比你那个跑了的强,屁股大好生养..."
"爸!她可是赵驼子的女儿,你和赵驼子不是正在闹别扭的吗?"臭头耳根子通红,却把山杏枝小心翼翼插在了农药桶把手上。
云祥福一听这话,脸上的褶子顿时挤成了老榆树皮。他"啪"地往地上啐了口浓痰,黄褐色的唾沫星子在土坷垃上砸出个小坑:"赵驼子那个老倔驴!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卡壳,眼珠子滴溜溜转了两圈,活像只发现粮仓的老耗子。
云祥福突然伸手揪住臭头的耳朵,压着嗓门道:"傻小子,你懂个屁!爸有办法!"远处传来布谷鸟的叫声,三长两短,跟打暗号似的。
山风掠过果园,青涩的果子在枝头轻轻摇晃。
入伏的风凉丝丝的,云祥福眯起眼,突然看到赵驼子向果园走来。立刻提高了嗓门,恨不得举着喇叭喊:"哎呀,好事啊,好事啊……哈哈哈,不得了啦,好事啊!”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