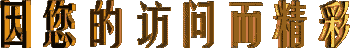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马年巨献——尹玉峰长篇硬汉小说《良马》别一番语言架构,别一番草原风情;人性、野性、眼泪、爱恨、或生或死一一铁与血的交织,在生命荒原中困苦摇曳……这是一首准格尔旗黄河第一弯山曲中流淌着的回肠荡气,即有奇幻爱情,又有铭心酸楚,更有民族民主希望和伟大生命热忱的歌。曲折的故事中一直有圣主的天驹神马,就像一面旗帜迎风飘扬……

作者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长篇硬汉小说《良马》连载
作者:尹玉峰
第一章:寻马(九)
1
夕阳将黄河染成一片熔金,那森与奇子俊父子俩站在河岸高处,望着野马群裹挟着小马驹消失在河对岸的尘烟中。他们的影子被拉得修长,斜斜地投在流经准格尔旗的太极弯上,仿佛两条不甘心就此放弃的绳索,紧紧钉在这片苍茫大地。
那森望着对岸逐渐模糊的马群,心中那股不甘的执念如野草般疯长。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曾像这些野马一样,在草原上自由驰骋,不受任何束缚。那时,他以为自由就是一切,直到父亲临终前紧紧握住他的手,用尽最后力气说出那句:"天驹的血脉不能断在咱们手里!"这句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埋进那森的心田,随着岁月流逝,生根发芽,长成一片执念的森林。
"阿爸,咱们快去追!" 奇子俊的声音打断了那森的思绪。少年攥紧套马杆,手指因用力而发白,眼神中闪烁着与父亲如出一辙的野性光芒。那森看着儿子,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既有欣慰,也有担忧。欣慰的是,儿子继承了家族对马的热爱;担忧的是,这份热爱是否会让儿子像自己年轻时一样,过于执着而失去理智。
奇子俊突然指向河滩上一丛丛红柳,声音因激动而微微颤抖:"野马群恋水草,更恋幼崽。咱们用柳枝编个哨子,吹出母马的呼崽声——它一定会回头!"
那森的眼睛亮了起来,仿佛被点燃的火把。他想起老三爷曾说"心要相依",这句话在他脑海中回响,如同一首古老的歌谣。老三爷是准格尔旗里最懂马的人,他常说,马和人之间,需要一种超越言语的默契,一种心灵上的相依。那森相信,只要用心,就能找到与马沟通的方式。
那森立刻割下袍角,动作熟练而果断。袍角在他手中变成一条柔软的索,他挖出野葱,用随身携带的小石片捣碎,将汁液抹在索上。野葱的辛辣气味混合着泥土的芬芳,那森深吸一口气,感受着这熟悉的气息——这是草原的味道,是生命的气息。他低声自语:"母马的气息能盖住人的味道。"这句话不仅是对儿子说的,更像是对自己内心的确认。
父子俩伏在河畔芦苇丛中,芦苇轻轻摇曳,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在为他们的计划伴奏。奇子俊的柳哨声如泣如诉,混着黄河水雾飘向对岸。那森闭上眼睛,用心感受着儿子的哨声,那声音里充满了期待和渴望,就像他自己年轻时追逐野马的心情。
起初,野马群只是躁动,马匹不安地踏着蹄子,发出低沉的嘶鸣。那森的心跳随着马群的躁动而加速,他担心自己的计划会失败。然而,小马驹突然竖起耳朵,那对明亮的眼睛在夕阳下闪烁着好奇的光芒。它挣脱马群,冲向浅滩,每一步都踏在那森的心上。
就在小马驹涉水时,那森甩出软索套住其前蹄。他的动作精准而迅速,仿佛经过了无数次练习。但他没有用力勒紧,反而松开绳索任它舔舐葱汁。那森看着小马驹小心翼翼地舔舐,心中涌起一股温柔的情感。他想起自己小时候第一次接触马的情景,那种既害怕又好奇的感觉,此刻在小马驹身上得到了完美的体现。
小马驹竟顺着气味一步步走近,最终低头蹭了蹭那森沾满草屑的手。那森的手微微颤抖,不是因为紧张,而是因为一种难以言喻的感动。他轻轻抚摸着小马驹的头,感受着它温暖的体温和柔软的毛发。这一刻,他觉得自己与这匹小马驹之间建立了一种特殊的联系,一种超越了物种的信任。
"阿爸,你看那匹领头的黑马!"奇子俊兴奋地指着马群前方一匹体型健硕的公马。少年奇子俊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眼睛里闪烁着与父亲如出一辙的野性光芒。那森顺着儿子的手指望去,黑马在夕阳下显得格外高大威猛,它的毛发在风中飘扬,仿佛一面旗帜。
那森嘴角扬起一抹笑意:"好眼力,那确实是匹千里驹。"他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声音中带着自豪:"走,我们去兽医布和那里,让他看看我们的新收获。"
"阿爸等下,我要给小马驹套上铃铛!"奇子俊迅速从腰间解下一个小包,里面装着一个青铜铃铛。他小心翼翼地将铃铛套在小马驹的脖子上,动作轻柔而熟练。叮呤当啷的响声立刻响起,在寂静的草原上显得格外清脆。那森看着儿子专注的神情,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他知道,儿子对马的热爱,已经深深扎根在他的心中。
父子俩并排骑行,唱着古老的蒙古长调。那森浑厚的嗓音与奇子俊清亮的声线交织在一起,随着风飘向远方。那森的心中涌起一股久违的满足感——能唤回天驹后裔的人,终将让草原的魂灵都为之臣服。他闭上眼睛,感受着骑在马背上的颠簸,听着儿子清脆的歌声,仿佛回到了自己年轻时的时光。那时,他也有一个像奇子俊一样热爱马的儿子,可惜那个儿子在一次意外中离开了他们。此刻,奇子俊的存在,让他感到一种弥补,一种对过去的释怀。
2
然而当他们接近配马场时,情况却出乎意料。野马群异常躁动,嘶鸣声此起彼伏,马蹄扬起阵阵尘土。布和正满头大汗地试图安抚它们,但收效甚微。那森勒住缰绳,眉头紧锁,心中充满了疑惑。他本以为自己的计划已经成功,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出现了问题。
"怎么回事?"那森的声音低沉而有力,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
布和擦了擦额头的汗水,苦笑道:"那森兄弟,这些野马根本不服管教。我试了所有方法,它们就是不肯安静下来。"他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出了那个建议:"也许...我们应该放它们回归草原。野马是不能降服使役的。"
那森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如同一块乌云遮住了阳光。他想起自己多年的努力,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想起自己与儿子一起追逐野马的情景。这一切的努力,难道就要因为野马的不驯服而付诸东流?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挫败感,仿佛自己的灵魂被撕裂。
就在这时,领头的黑马发出一声长嘶,声音穿透力极强,仿佛能直达人心。那森感到自己的心脏被这声嘶鸣重重一击。整个马群如同得到指令般突然裹着小马驹,冲破围栏向草原深处奔去。那森看着马群远去的背影,心中充满了绝望和愤怒。
"给我套马杆!"那森大吼一声,就要策马追赶。他的声音中充满了不甘和愤怒,仿佛要将整个草原都震碎。
布和在后面喊道:"没用的,没用的!野马一旦决定离开,谁也拦不住!"
那森回头看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悲怆:"我送送它们还不行吗?"不等回答,他已经催马追了上去。他的动作果断而坚决,仿佛在追逐自己的命运。
奇子俊想跟上去,被布和拦住:"让你阿爸去吧,他有自己的方式。"布和的语气中带着一种理解和尊重,他知道那森与马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联系。
草原上展开了一场奇特的追逐。野马群在前方狂奔,那森独自一人在后面追赶。他不再试图用套马杆捕捉它们,而是放开喉咙,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蒙古长调。歌声浑厚悠远,穿透风声,直达马群。那森的声音中充满了情感,既有对野马群的不舍,也有对自己命运的感慨。
"我会一直保护你们,一直保护你们的子子孙孙。"那森一边唱一边喊,声音在草原上回荡,"不管是谁,都不能把你们从我身边带走啊!"
奇迹般地,野马群的速度渐渐慢了下来。那森感到自己的歌声似乎触动了马群的心弦。领头的黑马甚至回头望了那森一眼,眼中闪烁着复杂的光芒。那森心中涌起无限惊喜,他低声自语:"它们会回来的,会回来的!布和啊,你号称懂马,张口闭口'没用的,没用的',看吧:我那森才是在驯马和相马方面具有特殊本领的'敖亚齐'!"
他得意地继续唱着歌,眼看着野马群开始向他聚拢。小马驹脖子上的青铜铃铛叮呤当啷响声越来越近。那森感到自己的心跳加速。他想象着将这群野马驯服,让它们成为家族的新力量,延续天驹的血脉。
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那森的心猛地一沉,仿佛被重锤击中。他感到一种不祥的预感,这种预感如同冰冷的触手,紧紧抓住他的心脏。爆炸声惊得野马群裹着小马驹再次奔逃,眨眼间就消失在草原深处。
那森站在原地,久久无法动弹。他的歌声戛然而止,仿佛被这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撕裂。他看着草原上留下的尘土和蹄印,心中充满了失落和迷茫。他想起自己多年的努力,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嘱托,想起自己与儿子一起追逐野马的情景。这一切的努力,难道就要因为这声爆炸而付诸东流?
3
那森在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那时,跪在父亲那木吉勒的毡帐前,帐内弥漫着浓重的草药味和羊油灯燃烧的焦糊气息。老牧人躺在褪色的羊毛毡上,枯瘦的手腕上还缠着染血的绷带——那是三天前驯马时被野马踢伤的。帐外,暴风雪正撕扯着最后的贵族宅邸残垣,那座曾经雕梁画栋的"苏鲁克"(贵族府邸)如今只剩半截石基,在雪地里像块被啃剩的骨头。
"阿爸,喝点奶茶..."那森捧着木碗的手在抖,碗沿磕碰出细碎的声响。老牧人睁开浑浊的眼睛,目光掠过儿子补丁摞补丁的羊皮袍,最终钉在帐顶悬挂的残破族徽上——那枚鎏金鹰隼纹章已褪成暗黄色,边缘还留着火燎的焦痕。
"那年...那场大火..."那木吉勒的喉间发出风箱般的嘶鸣,突然抓住儿子的手腕,力道大得惊人,"准格尔旗的贵族们说我们是'落日的鹰',可鹰的翅膀断了,爪子还在!"他猛地掀开被子,露出小腿上狰狞的伤疤——那是十年前为保护最后三匹天驹血统马,被马贩子的套马杆抽打的印记。
奇子俊缩在角落,被祖父突然的举动吓得捂住嘴。那森却看见父亲眼中迸发的火光,那是在马市上被贱卖祖传马鞍时都没有熄灭的火。
"听着,森儿。"老牧人用尽力气坐起身,从枕下摸出个油纸包。里面是半块发黑的银锁,锁芯里嵌着根灰白的马鬃——那是天驹"乌云盖雪"的鬃毛,二十年前被偷马贼剪走的。"你爷爷的爷爷,骑着它追过成吉思汗的斥候队..."那木吉勒的嘴唇哆嗦着,突然咬住银锁,用牙齿磕开锈蚀的机关,露出里面用血写就的蒙文:
"血统可以断,但魂不能散。"
帐外,暴风雪卷着残破的族旗呼啸而过。那森看见父亲从怀里掏出个布包,层层解开后竟是三枚生锈的铜钱——那是祖传的马掌钉,本该钉在战马的蹄铁上,如今却成了老牧人最后的家当。
"把它们...钉在..."那木吉勒突然剧烈咳嗽,血沫溅在铜钱上,"钉在..."他猛地指向帐外那片被雪掩埋的石基,"苏鲁克的废墟上!让后世知道,这里曾站着能驯服天驹的人!"
奇子俊的眼泪砸在铜钱上,溅起细小的血花。那森却死死攥住父亲的手,感觉那双手正像漏气的皮囊般迅速瘪下去。老牧人最后的目光越过儿子,投向帐外那片被风雪吞噬的草原,那里隐约传来野马的嘶鸣。
"它...会回来的..."那木吉勒的瞳孔开始扩散,却突然迸发出惊人的力气,将三枚铜钱拍在那森掌心,"记住!天驹的血脉不在马鞍上,不在族谱里——"他猛地扯开衣襟,露出心口处陈旧的箭伤,"在这!草原人的心窝子!"
那森摸到父亲心口那块凸起的疤痕,像摸到一块冰冷的铁。帐外,最后一点贵族宅邸的残垣轰然倒塌,积雪吞没了所有痕迹。只有那三枚铜钱,带着父亲掌心的温度,深深烙进那森的手纹里……
这时奇子俊从远处跑来,脸上写满了担忧:"阿爸,阿爸!您没事儿吧?"
奇子俊的喊声,打断了那森的痛苦回忆。他缓缓转过身,看着儿子,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既有失落,也有坚定。他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声音低沉而有力:"没事,儿子。野马群只是受到了惊吓。它们会回来的,我一定会找回它们。"
奇子俊看着父亲坚定的眼神,心中的担忧渐渐消散。他知道,只要有阿爸在,就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那森转过身,再次望向草原深处,心里暗道:“一定是赛春格这帮王八蛋搞出的爆炸声,我要找他们算账,绝不能饶了他们!” 他在心中默默发誓: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要找回这群野马,延续天驹的血脉,完成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夕阳的余晖洒在那森和奇子俊的身上,将他们的影子拉得更长,仿佛两条永不放弃的绳索,紧紧钉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那森和去蔼地说:
“儿子,回去吧,阿爸没事儿,一个人散散心!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