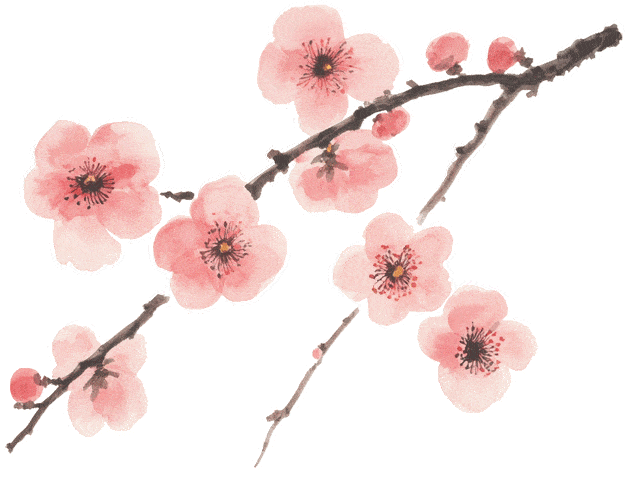◎ 喻 大 发
窗玻璃凝霜时,才惊觉寒意是从骨头缝里渗出来的。霜不像北风那般莽撞地拍打窗棂,倒像母亲当年纳鞋底的针,细而尖,悄无声息地顺着裤脚往上爬——先是脚踝泛酸,接着凉意沿骨缝漫过膝盖、攀上腰背,最后在后颈那道褶子里停驻。一转身,便在镜中撞见了自己。
镜子从不说谎。里头的人,七十四岁了。皮肤松垮垮地垂着,不像水果摊上油亮的蜜橘,倒像屋檐下风干多年的陈皮。日子是双极有耐性的手,一丝一缕抽走了体内的水分与甜意,只余下这皱巴巴、透着清苦的壳。褐斑在皱纹的沟壑里蔓延,像一张未标注的地图——年轻时未抵达的远方,如今都以这沉默的暗褐色,在脸上安了家。头发稀疏,每一根银丝都仿佛挑着枚细针,不扎皮肤,却扎眼。
身子是真老了。每日起床,膝盖“咔哒”一响,像旧门合页转动;端茶杯时,手会不自觉地晃,茶渍在杯口积出一圈深褐的年轮;爬三层楼得停下喘气,胸口像压着吸饱水的棉花,闷得发慌。可怪的是,胸膛深处总窝着一小团火——不旺,也不烫,不是灶里噼啪作响的柴火,倒像埋得很深的炭,只在后半夜被尿憋醒、听见窗外风卷落叶的间隙,才幽幽醒转,用那点残存的温热,一遍遍、耐心地舔着心口最软的地方:想再写篇文章,想回乡下摸摸老槐树皲裂的皮,想把箱底发脆的旧稿纸拿出来,对着光一字一字地改……
这些念头,像被温水泡开的干枣,软软地胀着,却有沉甸甸的分量。翻来覆去时,能听见血液淌过耳廓的极细声响。
总以为活到这岁数该“通透”了,像深秋的潭水,波澜不惊,倒映天光云影,也照得见水底沙石。如今才明白,岁月更像一把凿子,能在皮肉上刻出千沟万壑,却照不清心里那座弯弯绕绕的迷宫。前几日翻出旧笔记本,牛皮封面磨破了边,掀开泛黄脆硬的纸页,一股陈年霉味扑面而来。目光落在那行力透纸背的字上——“要做时代的弄潮儿!让文字像惊雷炸响!”——指尖莫名一颤。那股年少的意气,隔着近五十年的风尘,竟依旧滚烫。不觉丢人,字糙些怕什么?惊的是,五十年像失控的列车呼啸而过,窗外风景糊成一片,而自己竟像还在原地打转:年轻时退稿会失眠整夜,如今写不出满意的段落,照样半夜坐起,在黑暗里默默点烟;年轻时听不得半句批评,如今逆耳的话进来,心里那堵熟悉的墙依旧无声垒起;年轻时痴想的“传世之作”,这根刺竟原封不动,扎在七十四岁的心上。
原来所谓阅历,剥开被时光磨得温润光滑的“果肉”,里头的核不过是“重复”——把同样的天真、撞过的南墙、抱着的执迷,用更从容、甚至更理直气壮的模样,再经历一遍。比如现在收到退稿信,能笑着对人说“编辑不懂我”,转身关上门,却把稿子改了又改。
温柔的讽刺就在这里:总以为自己一路披荆斩棘,征服了岁月;到头来才发现,是岁月用这循环往复的轨迹,悄悄征服了一个文学的痴迷人。
所以,对那些太过“笃定”的姿态,尤其是面对文字时,我越来越警惕。
这辈子见过不少文人。有人把自己的字句当宝贝,对别人的笔墨却不屑一顾——文章非得裱在厅堂最显眼的地方,见人就指:“这是我最好的”;别人的书随手丢在角落,翻都不翻就说“没意思”。写作本是孤身往心里垦荒,是一场沉默的苦役,像站在野地里,手里只有一把锄头,一锄一锄下去默默耕种。可偏偏有人刚垦出一小块薄地,开出几朵稚嫩的小花,就急着摘下来扎成束,逢人便递过去:“香不香?美不美?”眼神灼灼的,像捧着自己活蹦乱跳的心。如今想起那些接花人脸上客套、眼里却无温度的笑——那笑容背后的空旷与寂静,比任何质问都更压人。
至于出书,有时更像一场大家心照不宣的幻觉。前阵子,一位作家恭恭敬敬送来他的新集子,烫金封面上印着他神采飞扬的大照片。翻开书页,扑鼻是甜腻的词儿:“岁月静好”“浅笑安然”“心灵的港湾”……句子裹着厚厚的糖衣,甜得齁人,里头却是空的。他坐在我对面,眼睛亮亮的,身子微微前倾,等着我酝酿好的夸奖。我能说什么?真话是冬天里的冰碴子,会扎破那层脆薄的糖衣;假话是温吞的油,只会让他在虚幻的暖意里醉得更深。在这近乎窒息的沉默里,我不由想起床底旧纸箱里的那些文章——它们正在时光里慢慢发霉、变黄。我也曾因为几篇变成铅字的文章、几句客套的恭维,就觉得脚下生云,仿佛摸到了“不朽”的边,连吃饭时脑子都绕着“下次一定要写得更好”打转。如今站在七十四岁的崖边回头看,才彻骨明白:连自己都说服不了的文字,怎能指望它比这身日渐枯萎的皮囊活得更久?
最耐人寻味的是一次“怀旧”的聚会。一屋子文人窝在茶馆包间,嗑瓜子、剥花生,茉莉花茶的香与被打捞过无数次的往事缠在一起:“当年我在文工团,可是台柱子!”“某某大作家亲口说我有天赋!”“记得那次笔会吗?喝到天亮,全都趴下啦!”……声音摞着声音,人人都在奋力打捞“存在过”的浮标,仿佛那些远去的名字、定格的瞬间,是抵挡眼下虚无的最后一道坝。我却也泡在这喧哗的暖流里,跟着点头、附和,在集体记忆浮华的温热中,忘了自己是谁。
散场后,一个人走进深冬的夜,冷风像醒酒汤,劈头盖脸浇下来,混着路边烤红薯的甜香与汽车尾气的浊味。心跳忽然像擂鼓般撞着胸口:这辈子,除了这些终将散去的热闹回声,到底还剩下什么?是箱底发霉的旧稿?墙上日渐黯淡的奖状?还是别人口中那客气而疏远的“老师”二字?
前几日收拾东西,翻出半袋深秋时和老友老李在公园捡的银杏果。果壳都裂了缝,露出里头褐黄的芯子,像老人豁了牙的嘴。老李不光爱写点东西,还喜欢摆弄这些,说把银杏果埋进花盆,说不定能长出小树苗——他总是这样,对什么都存着点不实际的盼头。可捡完果子没几天,他就住了院。我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跟我轻轻握手时,手背上的老年斑比我的还密,皮肤薄得能看见底下青色血管微弱的跳动。“我们这些人啊,”他气若游丝,字字却清晰,“年轻时没闯出什么名堂,老了,倒总想在死水潭里,掀起点属于自己的浪花。”这话像在冰水里浸透的针,准准扎进我心口最软、最怕疼的地方。是啊,老到这份上了,该淡泊了,为什么心里那点不甘的余烬,总被“虚名”“浮利”的风,吹出猩红灼痛的火星?
恍惚间望向窗外,楼下的叶子一片接一片往下飘,那么从容,像在跳生命最后一支寂静的圆舞。它们在春风里探过嫩芽,在夏日的华盖下青郁,在秋风里也披过金黄橙红的衣裳,如今却安然落进大地的怀抱。老树只是静静站着,不在乎哪片叶子曾经鲜亮夺目,不介意飘落的弧线是否优美,它只是活着,长叶、落叶、再长叶,把葱茏与凋零都当成自然的呼吸。
此刻,我的心忽然和窗外的树通了。心里某个坚硬的角落松动了。或许,“老”所给予的清明,不是练就一双能看穿一切幻象的鹰眼,而是终于学会和那些看不破的迷障、和那簇幽微却不肯熄灭的暗火安然共处。像树容得下每一片叶子,任它早落晚凋,都飘然归根;像大地容得下每一个长夜,不管多黑,都静静等天亮。
看不破为什么还想写?那就写吧。
看不破为什么还在意别人的眼光?那就在意吧。
看不破为什么还是不甘心?那就不甘心吧。
不必逼自己“放下”,不用求“通透”。只要还能和这些迷障、不甘、软弱的念想平平安安地住在同一副身子里,就好。
阳光悄悄漫过阳台,爬上旧书桌,把我皱巴巴的手背照得微微透亮——皮肤下青色的血管像古老地图上隐秘的河脉,隐约浮现。刚写下的字迹在光里很快干透、收缩,变成“存在过”的证据。人老了,或许也该在生命的文火慢熬里,熬出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的、静默的结晶——它不是别人眼里的风光、嘴里的名声,也不是任何能展示、能标价的东西。它或许就是某个清晨,终于能坦荡而平和地看着镜中这橘皮似的身子,不嫌它皱,不在意它老,对自己、也对岁月轻轻说一句:“这辈子,虽没见过多大的天地,没走到想去的远方,没经过惊涛骇浪,也没立下什么值得刻下的功,但至少,提笔时是真心与文字对话,结交时是真心相待,过日子,是真心在过。”
这大概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岁月尽头,能为自己守住的最后一处体面地盘:不骗自己,不辜负自己。
如今,七十四岁的我觉得时间不再是射向未知的箭,而是一片缓缓沉落的叶。我不再问生命还剩下什么,终于懂了:生命从未真正夺走什么,它只是以巨大而温和的耐心,把所有喧哗——青春的争吵、成功的欢呼、失败的哭泣——最终都变成了寂静。
窗外的叶子,落就落吧,落下来能肥土。
我这身橘皮,皱就皱吧,皱是岁月给的、独一无二的勋章。
心里那簇暗火,如果还愿意幽幽地烧着,就让它静静地烧吧——烧着,就证明,我还真切地活着。
作者简介喻大发,网名“草根”,1952年出生,武汉市新洲区人。一个喜欢涂抹文字,在自娱自乐中陶冶情操的农民。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