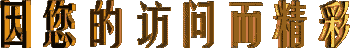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长篇诗境小说《野姜花》连载五
狐仙的爪痕
作者:尹玉峰(北京)
山风偷走野姜花的香,把狐仙的
爪痕,烙在炸开的石壁上。小桃
的哭声碎成卦爻,老辈人说
有些路要绕着坟头的柏树走
哑巴给老狗系上红裤衩,傻子娶了
更傻的新娘,铜锣闷响,唢呐噎喉
1
立夏,野姜花在涧水河的晨光中悄然苏醒,宛如山村写就的一首清新诗篇。
微风轻拂过湿润的土壤,野姜花从青翠的叶丛中探出头来,花瓣如薄纱般晶莹透亮,在晨露的映衬下泛着珍珠般的光泽。那洁白的花瓣边缘,晕染着一抹淡粉,恰似少女脸颊上羞涩的红晕,在立夏的暖阳下轻轻颤动。 花穗低垂,像一串串沉甸甸的思念,缀在淡粉色的花轴上,随风摇曳时,仿佛在低语着夏日的私语。
此时,涧水河村的田野还带着春末的凉意,野姜花却以它独有的清郁芬芳,悄然宣告夏日的来临。那香气不浓烈,却如溪水般沁人心脾,在空气中悠悠飘散,让人想起童年时在山坡上追逐的欢愉,或是故人重逢时那份不言而喻的默契。 叶片宽大而舒展,在阳光下泛着银白,如同出鞘的剑,守护着这份纯净的美好。
山野里的芍药同样开得正盛,花瓣层层叠叠,粉白里透着嫣红,像是少女羞怯的脸颊。风一吹,花枝轻颤,香气便顺着田埂、溪流,飘进家家户户的窗棂。这本该是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季节——夏风清爽,芍药灿烂,村民们该忙着下地锄草,或是坐在树荫下闲话家常。
张寡妇天不亮就挎着柳条筐上山了,专挑那含苞待放的芍药花骨朵,说是要赶在日出前采回来,用山泉水养在堂屋的供桌上——这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立夏供芍药,能保家宅平安。可今儿个,她刚走到云功德家院墙外,就听见里头传来"嗷唠"一嗓子,吓得她手一抖,刚摘的花撒了一地。
"造孽啊!"张寡妇蹲在地上一边捡花一边念叨,"这准是又触犯山神爷了......"她眯着眼往院里瞅,只见云功德媳妇小桃披头散发地瘫在当院,哭得嗓子都劈了叉。她瘫坐在门槛上,头发散乱,眼睛红肿,嘴里不住地念叨:“完了……全完了……”小桃的哭声陆续引来几个婆子围着她劝,可谁的话她都听不进去,只是不停地捶打自己的胸口,仿佛那里堵着一块千斤重的石头。
村民们三三两两地聚在院外,交头接耳,神色惶惶。有人低声说:“云功德这回是真惹上大祸了……”也有人摇头叹气:“唉,早说了不能动那些石头,偏不听,这下好了,狐大仙发怒了,谁也别想安生!”
张寡妇立刻转道去了赵驼子家,她一屁股坐在炕沿上,手里攥着块帕子,嘴里不停地念叨:“哎呀妈啊,这是犯的哪一出啊?好好的日子,咋就闹成这样了?这小媳妇旱着了,真的憋不住了!”赵驼子脸还没洗呢,此刻他正背着手睡眼惺忪地在屋里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个疙瘩。”你什么意思呀,是不是让我去帮帮忙?"
”你个老不正经的?”张寡妇眼睛一瞪,伸手要抓赵驼子的脸。赵驼子忙道:”我有那贼心也没那胆儿呀!”
正说着,云秀的父亲云祥福"咣当"一声推门进来,脸色阴沉得像要滴出水来。他瞪了张寡妇一眼,没好气地说道:“你哪有事哪到,瞎掺和啥?”
张寡妇撇撇嘴,刚要反驳,云祥福已经转向赵驼子,压低声音道:“老赵,我刚刚占了一卦,这事儿……不简单啊。”
赵驼子停下脚步,抬眼看他:“咋说?”
"完犊子了!狐仙爷这回是真急眼了!"说着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里头裹着三枚磨得锃亮的乾隆通宝,"连掷六次都是阴卦,这是要灭门绝户的兆头啊!"
云祥福叹了口气,眼神飘忽,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云功德祖上三辈不信邪,偏偏去凿那些石头,触怒了狐大仙。狐大仙先是让云家单传,男丁不旺,到了他父亲那一辈,连命都搭进去了。现在到了云功德这辈,已经绝后了,可这虎拉巴几的玩意儿,还敢动炸药!这下可好,狐大仙彻底恼了,直接给他来了个‘断根儿’!”
张寡妇听得浑身一激灵,手里的帕子差点掉地上,她哆嗦着插嘴:“哎呀大哥啊,你可别把人吓个好歹的,他断了什么的,跟咱们有啥关系呀?”
云祥福狠狠瞪了她一眼,骂道:“你懂个屁!狐大仙可不是好惹的!你以为狐仙变人都是美娘子的样子?那是在过去!我亲眼见过的狐仙,个头只有板凳那么高,靰鞡鞋,黄皮袄,眼睛溜圆像灯泡,挨家挨户寻仇报!这往后……”
张寡妇脸色煞白,嘴唇直打颤:“哎呀妈啊,是真的吗?吓死人了!“
“你看看你,你不信,跟着掺合个啥?云福说:"你忘了!前年王老蔫偷砍山神庙后的松树,当天晚上就让黄大仙给治了,在雪地里光腚跑了一宿......"
”是呀!“张寡妇一怔,“我想起来了,这事儿当时在村里响动挺大!你说的挨家挨户寻仇报,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可咋整啊?”
云祥福眯起眼睛,故作高深地捋了捋胡子,慢悠悠道:“冲喜呗。”
一直没吭声的赵驼子忽然冷笑一声,撇嘴道:“竟扯猫骚子!人家冲喜,是因为身体不好,或者是精神不爽,利用喜事消灾救命。可你说的什么‘断根儿’,跟冲喜挨得上边吗?”
云祥福也不恼,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赵驼子一眼,叹道:“又碰到一个糊涂虫。老赵啊,你当村长的时候,刨起大山咋呼得最欢,结果呢?狐大仙笑呵呵地轻弹下指头,落下几粒石籽砸在你后背上,你足足半年扬不了脖子吧?后来咋样?变成罗锅了!”
赵驼子一听这话,眼睛一立,拳头攥得咯咯响:“云祥福!你再瞎扯犊子,信不信我揍你?”
云祥福却像是打开了话匣子,根本停不下来:“你变成罗锅后,狐大仙也没放过你,你媳妇紧接着就撒手归西……你的根再壮,也得架手撸;你的犁锃亮,犁下没田亩……唉,啥也别说了,你自己核计去吧!”
赵驼子被他说得脑袋嗡嗡响,眼前一阵阵发黑。张寡妇更是吓得直哆嗦,颤声道:“哎呀大哥啊,还真是这回事儿呢!那咱们不犯狐大仙不就结了吗?”
”不犯也没有什么好果子吃了,云功德炸山端了它们的老窝,它们把全村人都看作是它们的死敌,尤其是年轻力壮的,结婚没结婚的男人,个个逃不掉‘断根`的厄运!“
”哎呀妈呀,那可咋办啊!"张寡妇叫唤起来。
云祥福一笑:“天机不可轻泄,若肯随喜,我就指点一二!”
张寡妇瞅了瞅抽闷烟的赵驼子,”驼子哥,破费一把吧,你有儿,我有女的。”
云祥福摇头晃脑,神神叨叨地念叨:“往后赶上初一、十五,多给狐大仙烧烧香、上上贡,就什么都明白了——有儿有女的都要小心啦,包括我,哎呀,操死心了!”
张寡妇又瞅了瞅赵驼子,赵驼子有些不耐烦了,在裤腰里扯出一张百元大票递给张寡妇,”给给给!”张寡妇接钱的瞬间,眼睛闪金光:”哎呀妈呀,驼子哥太大方了!“云祥福顺手把钱抢了过来揣在兜里,突然压低声音,眯眼掐指:
狐仙门前过,无喜必有祸;屋檐挂苞米,栓绳取红色;红色喜事多,一喜冲百厄!”
屋里一片死寂,只有张寡妇的抽气声和赵驼子粗重的呼吸。窗外,芍药依旧开得娇艳,可山风掠过,却莫名带了一丝寒意。赵驼子和张寡妇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张寡妇猛地捂住嘴,眼睛瞪得溜圆,像两颗泡在凉水里的黑豆子。她扭头看向赵驼子,声音打着颤:"驼子哥,你、你媳妇当年是不是也……"话没说完,赵驼子那张沟壑纵横的脸突然涨得通红,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他抄起炕边的笤帚疙瘩就要砸过去:"闭上你这乌鸦嘴!"
"老赵!"云祥福一把按住笤帚,油纸包里的铜钱哗啦作响,"我爹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说,这山里的石头是狐仙的牙,树是狐仙的毛,动不得!可云功德那愣头青,非要用炸药崩开山神庙后的石壁,说要给村里修路!"
张寡妇的柳条筐"哐当"掉在地上,芍药花瓣沾了泥。她突然想起去年冬天,云功德家的大黄狗莫名死在雪地里,肚皮上还留着几个梅花状的焦痕。当时赵驼子蹲在狗尸旁嘀咕:"这狗崽子,准是偷吃了供果……"
"现在可好,"云祥福用铜钱在炕沿上敲出急促的节奏,"狐仙把云家祠堂的香炉都掀了,供桌上的祖宗牌位东倒西歪。小桃今早梳头时,梳齿里缠着三根白毛,那颜色……"他故意停顿,看着张寡妇脸色由白转青。
院外突然传来"咔嚓"一声脆响,像是树枝折断。三人同时扭头,只见云秀家那棵老槐树的枝桠无风自动,树影里隐约有个毛茸茸的影子掠过。赵驼子手里的笤帚"啪"地掉在地上,他弯腰去捡时,后颈突然一凉——有片冰凉的雪花落在衣领里,可窗外分明是立夏时节。
赵驼子与张寡妇眼神对光:“有些事该信就信!”
张寡妇道:“哎呀妈呀,我是信了!”
"冲喜!必须冲喜!"云祥福突然拍案而起,油纸包里的铜钱撒了一炕,云祥福笑了:“你们俩算是积了善缘了,这往后啊,天天摆大席、办喜事,一个会打锣,一个会唱,三丈内有财神晃悠,财运亨通喽!”
云祥福走出赵驼子家,把那张皱巴巴的百元大票对折再对折,塞进内兜,手指在兜里摩挲了两下,确认纸币不会滑出来。他眼角余光瞥见迎面走来了杨百万,立刻清了清嗓子:
"百万兄弟!"他突然朝杨百万作个揖,"您这步子迈得可讲究——左脚踏青龙位,右脚踩白虎煞,这是要发横财的相啊!"
杨百万愣在当场,黑红的脸膛沁出油汗:"说啥呢?俺不懂。"
云祥福忽然压低声音凑近,"不过嘛...您家灶台朝西是吧?朝着云公德家的方向,云公德现在的情况你知道吧?你儿子的喜事儿是不是还没办?"
杨百万又是一怔,半个月前他刚把灶台改成西向,这事村里根本没人知道。“啥意思吧?你说!”
"三百块钱。"云祥福伸出三根手指在对方眼前晃了晃,"我教您破这个水火相冲。"见对方犹豫,又补了句,"要不等您家母鸡开始打鸣再找我也成。"杨百万立刻就掏出了二百五十元给他,“我现在兜里就这些钱,你赶紧说说咋回事!“
到了晌午,日头很毒,云祥福蹲在村头老槐树下数钞票。几张皱巴巴的纸币被他捋得平平整整——赵驼子的一百块,杨百万的二百五,卖豆腐李婶塞的五个钢镚儿,还有小卖部周瘸子赊账抵卦金的两包大前门。他乐了:”这钱好挣,收获不小!"于是他就地一躺,心满意足,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当夕阳把云祥福的影子拉得老长时,他才感觉到饥肠辘辘,于是就往家走,经过村民偷偷搭建的简陋土地庙时,他忽然停下脚步,摸出三个钢镚儿"叮叮当当"扔进功德箱。"狐大仙莫怪。"他对着粗糙的石头神像嬉皮笑脸,"您吃香火,我吃饭,这年头,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万元户、十万元户、百万元户都冒头了,咱们只是混口饭吃。"
2
云祥福打卦算命生意突然火爆起来。他蹲在土地庙后头数钱,指头蘸唾沫星子能蘸出二两油。赵驼子成了他的金牌托儿,逢人就撩裤腰带:"瞧见没?自打屋檐挂苞米,栓绳取红色;俺这老腰杆——"他突然被张寡妇踹了一脚。"咳!俺是说家里猪崽一窝下十二个!"
张寡妇瞪了赵驼子一眼,”光瞅着云祥福这个老狐狸数钱了,咱们的钱呢?“
赵驼子一斜肩,“他是老狐狸,哼!狐狸最怕啥?狐狸怕虎狼!我是虎,你是狼!“说着,赵驼子就操起铜锣唱起来:
”锵,锵,锵——下月初八宜婚嫁啊,锵,没对象的抓紧挂啊!锵,锵,锵——”
”挂、挂、挂!那是处对象,不是挂马子,你个赵驼子,咋这么不正经?"张寡妇打断了赵驼子的唱词。
”哦,对对对,让我整串了,心里还核计着那个老狐狸的‘屋檐挂苞米’呢!"赵驼子一跺脚,”干脆,把一百元钱买来的原话,照宣!”
“你得懂得合力,什么叫合力,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俩个人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赵驼子又语重心长地说起来,说着说着就下道了:“什么是劲往一处使呢?就像过去你和你老爷们晚上干那种事儿一样,俩人一起铆足劲儿,那架势,天崩地裂!锵,锵,锵——"
”哎呀妈呀,赵驼子你也太流氓了!“张寡妇攥着拳头捶他。赵驼子不躲不闪,还笑嘻嘻地鼓励她:”大点劲,过瘾!你看看,一个虎,一个狼,虎狼联合还干不过狐狸吗?“
第二天,晨雾茫茫中,铜锣亢奋响起:
”锵,锵,锵——打锣打锣,我、老赵打锣,锵,锵,锵——话说,锵,狐仙门前过,锵,无喜必有祸;锵,屋檐挂苞米,锵,栓绳取红色;锵,红色喜事多,锵,锵,锵,一喜冲百厄!锵,锵,锵——锵,锵,锵——南坡的姑娘,锵,北洼的小伙儿,锵,锵,锵——全村的侠客,锵,狐仙不好惹,锵,锵,锵——赶紧办喜事冲厄,锵,锵,锵——冲厄办喜事,锵,找谁最适合?锵,锵,锵——找我!”
"哎呦喂——"张寡妇一拍大腿,红绸裤管抖出三斤香粉味,扯着赵驼子就往村口大槐树下冲,"都来听真佛爷显灵!"她嗓子眼卡着半斤唾沫星子,把云祥福那套"红绳冲煞"的说辞翻炒得油光水亮,末了还抻着脖子补了句:"谁家不照办——"突然压低嗓门,"祖坟冒黑烟都是轻的!"
经这么一通呼悠,山村里就热闹了。一时间凡有男丁的人家,纷纷把玉米棒栓上红绳挂在屋檐,三天两头就有成亲办喜事的。山里人家东拼西凑的桌椅占据了很大一片山坡,杀猪宰鸡的热水满地流溢,山坡上散发着大团大团的雾气。
李木匠家十六岁的闺女被塞进花轿,新郎是隔壁村五十岁的杀猪匠——"冲喜要紧!聘礼?要啥自行车!"王铁匠连夜给儿子和母猪办了订婚宴,酒席上二踢脚崩飞了半边房檐。连村头哑巴孙婆都哆嗦着给自家老黄狗系上红裤衩,嘴里"啊啊"比划着要给它娶媳妇。
温雨滋万物,暖阳痒裤裆。 赵驼子异常亢奋: 赵驼子打铜锣,赵麻杆儿吹唢呐,张寡妇唱山曲小调,唱二人转。这山曲小调,张寡妇一口气能唱上十几首;唱二人转,就得有个好搭档了,这时的赵驼子恰好派到用场。张寡妇唱的浪,赵驼子逗的欢,同唱婚庆戏,财源滚滚来。
这天正赶上杨百万的儿子杨大傻的喜事儿,赵驼子心想:你杨百万的钱来的不干净,生了个傻儿子,又娶了个傻拉巴几的二五子儿媳妇,遭报应了吧,我得好好刮刮你的财。杨百万为傻儿子点燃的鞭炮从山顶到山底噼叭作响,为前来帮忙操办喜事的乡亲也备足了答谢红包,尽显暴发户的阔气和傻气。
想当初,杨百万挺着啤酒肚,金链子在领口若隐若现:"驼子哥,咱这穷山沟能有啥出息?要我说,还是得出去闯!"他说着拍了拍鼓囊囊的腰包,里面装着刚从林场倒卖木材赚的第一桶金。”听说了吗?南边都发大财了!人家说现在政策放开了,是骡子是马都能拉出来遛遛!"
半个月后,赵驼子背着行囊站在村口。他穿着唯一一件没有补丁的藏蓝色中山装,驼背似乎挺直了些。张寡妇来了一句:”驼子哥,城里人精着呢,你可别让人骗了。"
赵驼子咧嘴一笑,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天底下能骗了我老赵的人还在他娘的腿肚子里钻筋呢!"
与赵驼子同行的还有杨百万和村里几个年轻人。火车上,杨百万神秘兮兮地凑过来:"驼子哥,我有个门路,林场的老刘答应给咱们批条子,一根上等红松能赚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
赵驼子摇摇头,从怀里掏出一本皱巴巴的收藏类杂志:"我要干就干正经买卖。你看这上面写的,现在搞古董收藏最来钱!"
省城的古玩市场人头攒动。赵驼子蹲在一个地摊前,眼睛死死盯着一堆灰扑扑的玉器。摊主是个精瘦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河南口音:"大哥好眼力!这可是正儿八经的红山文化遗物,刚从内蒙古那边挖出来的。"
赵驼子拿起一块形状奇特的玉璧——它呈椭圆形,两头大小不一,中间有孔,表面刻着粗糙的纹路。"这...这是啥物件?"
摊主挤眉弄眼:"这叫双联璧,老祖宗祭祀用的,现在城里文化人可稀罕这玩意儿了!"他压低声音,"听说跟古代的生殖崇拜有关系,那些有钱的老板就爱收藏这个,摆在办公室里,寓意生意兴隆,子孙满堂!"
赵驼子心砰砰直跳。他想起了村里老人讲的那些荤故事,脸不由得热了起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他用全部积蓄买下了二十多块"双联璧",小心翼翼地包在旧衣服里,像抱着个金娃娃。
与此同时,杨百万的"生意"却做得风生水起。他租了辆卡车,夜里从国有林场往外拉木材,白天就躺在宾馆数钱。才两个月,他就买了大哥大,金戒指在阳光下闪闪发亮。
"驼子哥,你这破石头能卖几个钱?"杨百万吐着烟圈,不屑地看着赵驼子擦拭那些玉璧,"跟我干吧,保证你一个月挣的比你种十年地都多!"
赵驼子梗着脖子:"你这是犯法的勾当!我这是正经文化生意!"
转眼到了六月,城里举办性文化节的消息传得沸沸扬扬。赵驼子眼睛一亮,觉得机会来了。他精心挑选了几块纹路最"生动"的双联璧,用红绸子包好,兴冲冲地去了文化节会场。
会场里人山人海,到处都是售卖情趣用品的摊位。赵驼子找了个角落支起地摊,刚把双联璧摆出来,就引来不少人围观。
"老哥,您这卖的是什么呀?"一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好奇地问。
赵驼子神秘地笑笑:"这可是红山文化的宝贝,古代人拜的神物!能保佑夫妻和睦,多子多孙!"
眼镜男拿起一块仔细端详,突然笑出声来:"老哥,您让人骗了吧?这哪是什么古董,分明是树脂倒模的仿品!您看这纹路,都是用机器压出来的,连做旧都没做好!"
周围爆发出一阵哄笑。赵驼子的脸涨得通红,驼背似乎更弯了。他固执地辩解:"你懂什么!这可是我花大价钱从内蒙古收来的!"
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者摇摇头:"看来你真的被人骗了,红山文化的玉器我研究几十年了。真品玉质温润,做工精细,哪像这些粗制滥造的玩意儿?"
文化节三天,赵驼子一块双联璧也没卖出去。他蹲在旅馆门口,看着杨百万开着新买的桑塔纳扬长而去,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现在趁杨百万给傻儿子办喜事,捞他一把,理所当然。
杨百万家张灯结彩。从山脚到山顶,鞭炮声震耳欲聋。赵驼子和张寡妇穿着大红大绿的戏服,在临时搭建的台子上卖力表演。
"张妹子,今天可得给杨老板长长脸!"赵驼子眨眨眼,铜锣敲得震天响。
张寡妇扭着水蛇腰,嗓子又脆又亮:"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傻兄弟娶天仙。"
台下哄笑一片。杨百万的傻儿子流着口水,新娘子是个目光呆滞的姑娘,据说是杨百万花大价钱从邻村娶来的。
赵驼子即兴编词:"杨老板财大气粗啊,儿子娶妻众人夸啊,"他故意拉长声调,"就是不知这钱财来路正不正啊——"
杨百万在台下脸色变了变,但碍于喜庆场合不好发作,只得往台上扔了个厚厚的红包。
表演间隙,赵驼子解开褂子扇风,腰间露出那串无人问津的双联璧。有眼尖的村民起哄:"驼子哥,你这挂的是啥宝贝啊?"
赵驼子索性解下来给大家看:"这可是正经古董!城里文化人都抢着要呢!"
赵驼子铜锣一打,顺口就唱: "锵,锵,锵——打锣, 打锣——我, 锵——老赵打锣! 锵,屋檐挂苞米,栓绳取红色,,锵,好使不好使,我不想费口舌!锵,锵,锵——我腰间的双联璧,锵。保根不断——绝对避邪!锵,锵,锵——这玉有五德,锵,仁义礼勇洁,锵——人养玉三年,锵,玉养人不歇,锵——君子常佩玉,锵,小人搞破鞋!
村民们一阵鼓噪,有的问:“这玩意真灵吗? ”有的说:“赵驼子是神人,他可是当过村长的人啊,鼓捣的东西不一般。张寡妇急忙上前捏弄双联璧,嘻笑道:“哎呀妈啊,这也太流氓咧。还滑溜溜的!”赵驼子撇嘴道:”你懂啥?还知道滑溜溜的,那是把玩出“包浆”了。说点内行话,那叫‘润'!”
张寡妇笑得直捂肚子:“你这老流氓,倒是麻溜痛快,还没怎的呢,就把‘浆’给整出来了,立马就‘孕’了!"
大家伙儿暴笑,一片笑声中,云祥福上前就拽赵驼子腰间的双联璧。赵驼子一扬手,道:“拿钱,八百元一件!”云祥福笑道:”拿钱多伤感情啊,都是乡里乡亲的!我出道道让大家伙儿屋檐挂上栓红绳的大苞米避邪,也没挨个要大家伙儿的钱啊。多做善事少提钱,这——你得向我学习,做人别那么缺德,别把事情做绝了! ”
赵驼子立马眼珠一瞪,狠狠道:”你那红绳大苞米纯属胡勒儿!告诉你——不用双联璧,裆下不好使。你就等着绝后吧!你媳妇早就跑了吧,这事儿不提,就说你儿子臭头吧,结婚才几天呀,媳妇就被人拐走了……”
云祥福气得要打赵驼子,被大家伙儿劝开了。云祥福愤愤道:“把你家的大苞米摘下来,别他妈的得便宜卖乖!赵驼子笑着反驳道:”你那大苞米不好使呀,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不化钱的是烂货!大家伙儿快来买双联璧吧……”
新郎杨大傻第一个央求:”我买——爸呀,快掏钱啊,我买……”最后,还有一些村民忍痛舍金求买下,赵驼子的腰包,自然又是一番鼓胀。张寡妇的眼珠滴溜转,“哎呀妈呀,驼子哥,分脏得均匀啊!”
赵驼子急了:叫唤啥呢?傻了吗?没见过钱吗?红山文化双联璧人见人喜,夫妻和睦,婚姻圆满!我在城里每一件忍痛出手八万成交,我老赵不忍心挣那么多钱,钱多,烦事多,但是钱算什么,我老赵是把钱看得比命还重要的人吗?嘿嘿,老赵我是有良心的!”
3
暮色降临,涧水河村在一片昏黄的灯光里。赵驼子蹲在自家门槛上,手里攥着一大把钞票,指节因用力而发白。按理说,这收入够他喝上半年烧刀子了,收获不小,可心里那股子空落落的感觉却像野草般疯长。
屋子里传出儿子赵麻杆儿的唢呐声,《纤夫的爱》飘进赵驼子的耳朵。他佝偻的背脊猛地一颤,浑浊的眼珠里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今天杨大傻娶亲,新娘子是邻村有名的"二五子"——这绰号既暗指她脑子不太灵光,又暗示她作风不检点。赵驼子嘿嘿一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
"听壁去。"这个念头像毒蛇般缠上他的心。虽然这陋俗早被年轻人嗤之以鼻,可对五十多岁的赵驼子来说,却是为数不多能让他血液沸腾的乐子。他驼背的身影隐入夜色,像只觅食的野兽般悄无声息地摸向杨家新房。
六月的山乡夜晚,月亮像个煎得半熟的荷包蛋,稀溜溜地挂在杨家的房檐上。晚风裹挟着苞米地里的青草味儿,混着谁家灶台飘来的大酱香,在村子里慢悠悠地转悠。赵驼子撅着个腚趴在杨家后墙根底下,后脊梁骨硌着砖缝,活像条晒蔫吧的蚯蚓。这老光棍儿心里跟揣了二十五只耗子似的,百爪挠心啊!
"这杨家娶媳妇,咋连个响动都没有?"赵驼子心里嘀咕着,把耳朵贴在墙上。墙皮上的青苔凉丝丝的,蹭得他耳根子发痒。突然"嗷"一嗓子,墙上的夜猫子让他惊得扑棱棱飞走了,翅膀扇起的风带着股子腥臊味儿。屋里传来"刺啦刺啦"的动静,跟老母猪拱白菜帮子似的。
赵驼子抹了把脑门上的汗,手指头在砖缝里抠窟窿眼当儿,昏黄的光亮从窗帘缝里漏出来。赵驼子一侧脸,心中暗喜,“真是天意啊!不用抠墙缝了,窗帘本来就露缝。”于是他悄悄向窗口移去,眯着三角眼往里瞅,眼珠子都快瞪出眶了。
"哎呦我的亲娘咧!"赵驼子看得直吧唧嘴,哈喇子顺着嘴角往下淌,"这新娘子脱衣裳跟剥葱似的!"二五子背对着窗户,瘦得跟麻杆儿似的,脊梁骨凸出来活像老赵家那架用了三十年的搓衣板。大红嫁衣"唰"地滑到脚脖子上,露出两排肋骨,一根根支棱着,就像谁家晾衣裳的竹竿子。那大红裤衩往床脚一甩,飘飘悠悠地落在地上,活像菜园子里蔫巴的洋柿子。
再看杨大傻,穿着崭新的西服,领口歪得能塞进个土豆,袖口沾着油渍。这傻小子站在炕沿边上,脑门上的汗珠子亮晶晶的,跟抹了猪油似的。他突然开始抽自己大嘴巴子,"啪啪"声跟放二踢脚似的,震得房梁上的灰都扑簌簌往下掉,落在新铺的被褥上,跟撒了层胡椒面似的。
"你个完蛋玩意儿!"二五子一嗓子震得窗户外头的蛾子扑棱棱乱飞,"你爸没教过你咋当新郎官啊?"她一把揪住杨大傻的耳朵,指甲盖都掐进肉里去了。
杨大傻厚嘴唇哆嗦着:"教、教了..."他眼球上翻露出大片眼白,"我爸说...不能随便和女人睡觉..."粗短的手指比划着,"那是...耍流氓。"最后三个字说得极轻,像含了口水。
"放你娘的罗圈屁!"二五子气得直拍炕席,震得杨大傻直捂耳朵。"这叫明媒正娶!懂不懂?"说着抄起炕笤帚就要往杨大傻身上招呼。
窗外的赵驼子肩膀直抖,憋笑憋得眼泪都出来了。只见二五子散乱的头发像团乱麻:"那让你爹来跟我睡!看看你爹是咋耍流氓的!"
令人意外的是,杨大傻竟嘿嘿笑起来,露出参差不齐的黄牙:"你以为我傻呢?我爸是我爸,我爸是我儿!”这颠三倒四的话让二五子愣了片刻,突然笑得前仰后合,"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杨大傻又嘿嘿笑了起来,"我儿是我爸,我爸是我儿……反正不是孙子,我爸是我爸,我爸是我儿!你以为我傻呢?”
外头赵驼子正乐得直拍大腿,忽然,一只手搭在他的肩膀头上。把赵驼子吓得腿都突突了。
他一扭头见是张寡妇,三角眼顿时瞪得溜圆,活像两颗泡发的黑豆掉进了面缸里。
"哎呦我的祖宗奶奶!"他压着嗓子嚎了一嗓子,声儿颤得跟拉破风箱似的,哈喇子星子喷了张寡妇一脸。张寡妇倒是不见外,顺势把沉甸甸的胸脯子往赵驼子驼背上压。她那件靛蓝褂子蹭着赵驼子后脊梁,发出窸窸窣窣的动静,跟耗子啃米缸似的。
赵驼子只觉得后背热烘烘的,汗珠子顺着罗锅沟往下淌,把裤腰都洇湿了半圈。"要死啊你!"赵驼子缩着脖子往旁边躲,"别整动静,这要让杨百万瞅见..."话没说完就叫张寡妇掐住了大腿里子,疼得他直吸凉气,漏风的门牙缝里嘶嘶冒气声。
张寡妇凑到他耳朵根:"装啥正经?你裤裆都支帐篷了!"这话说得赵驼子老脸臊得通红,他低头一瞅,可不是嘛!裤裆果然鼓出个尖儿。
屋里突然传来"咚"的一声闷响,像是谁摔在了炕上。赵驼子顾不得害臊,三角眼又粘回了窗缝。这会儿他倒跟张寡妇成了同伙,俩人的脑袋在窗台下此起彼伏。
张寡妇那张抹了厚粉的脸在月光下泛着青白,活像刚从面缸里捞出来的发糕。她踮着脚尖往窗缝里凑,头上的银簪子晃得赵驼子眼晕。
"哎呀妈呀!"张寡妇突然掐住赵驼子的后脖颈,指甲陷进他那层老牛皮似的褶子里,"这傻小子裤腰带系的是死扣儿!"她嗓子眼里挤出咯咯的笑声,跟老母鸡下蛋似的。
屋里二五子正抡着笤帚疙瘩追打杨大傻,笤帚苗儿在空中划出弧线,带起的风把喜烛火苗吹得东倒西歪。杨大傻抱着脑袋往炕角缩,西服后开襟"刺啦"一声挂在了炕席的竹篾子上。
窗户外头,张寡妇突然往赵驼子背上重重一拍:"快看!新娘子要动真格的了!"她袖口蹭着赵驼子的耳朵,散发出一股子腌咸菜缸的馊味。二五子这会儿已经扯开了自己的红肚兜,两根锁骨深得能舀水,胸口瘦得能看见青紫色的血管一跳一跳的。
赵驼子突然觉得裤裆发紧,原来张寡妇那只戴着铜顶针的手正往他裤腰里钻。他刚要叫唤,就被张寡妇用汗巾子堵住了嘴——那汗巾子一股子头油味,熏得他直翻白眼。
屋里突然"咣当"一声响。杨大傻被二五子按倒在炕桌上,压翻了装着红枣花生的喜盘。窗外两人同时一哆嗦,张寡妇的银簪子"叮"地戳进了窗框缝里。这会儿月亮正好照在二五子光溜溜的后背上,那脊梁骨起伏的弧度,活像山南坡那道被雨水冲出来的沟壑。
"要了亲命了..."赵驼子从汗巾子缝里挤出半句,用肘拱了一下张寡妇,给她吓得一激灵,顶针"当啷"掉进了赵驼子的鞋子里。
赵驼子急着哈下腰伸手去取铜顶针,不抖栽个大跟头。突然"咔嚓"一声——把人家晾在窗台一侧的黄瓜架子给碰塌了。青黄瓜"咕噜噜"滚了一地,有个还直接砸他脑门上了,疼得他直咧嘴。
"这新娘子咋还咬人呐!"她压低嗓子惊呼,声音里混着兴奋和惊恐。
赵驼子脖子一缩,却见窗内二五子正骑在杨大傻身上,一口咬住他耳垂,留下两排牙印。杨大傻的傻笑卡在喉咙里,变成一声呜咽。月光透过窗帘缝,把两人的影子投在墙上,像两只撕咬的野兽。
"这哪是冲喜,分明是喂狼!"张寡妇的唾沫星子溅在赵驼子脸上,她突然拽住他胳膊往屋里拖,"快!把门闩撬开!新娘子要咬死新郎官了!"
赵驼子被拖得踉跄,裤裆的帐篷撞在门框上,疼得他倒吸冷气。他摸出随身带的铜锣,"哐"地砸向门板:"都别慌!赵驼子在此!"锣声震得窗棂发抖,屋里"咚"地又是一声——这回是炕桌翻了,酒菜泼了一地。
张寡妇趁机挤进门缝,看见二五子正用绣花鞋踩杨大傻的脸,鞋底沾着血渍:"这傻货连洞房都不会进!"她转身对赵驼子挤眉弄眼,"你上!教教他咋耍流氓!"
屋里顿时炸了锅:"哪个缺德带冒烟的!"二五子尖叫起来:“来人啊,抓贼呀!”杨百万闻声披着褂子从西屋跑了出来,站在月光下,叼在嘴里的香烟在黑暗中明灭不定。
赵驼子一转身,和张寡妇的鼻尖差点相碰。他俩一下子跑出二里地,赵驼子吆喝张寡妇停下喘口气。“黑灯瞎火的,估计张百万认不出来我们,现在咱们各回各的家。”于是,一个往南走,一个往北走。
往北走的赵驼子感觉身后有人跟了上来,一回头,傻眼了,跟上来的人是杨百万。
【版权所有】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