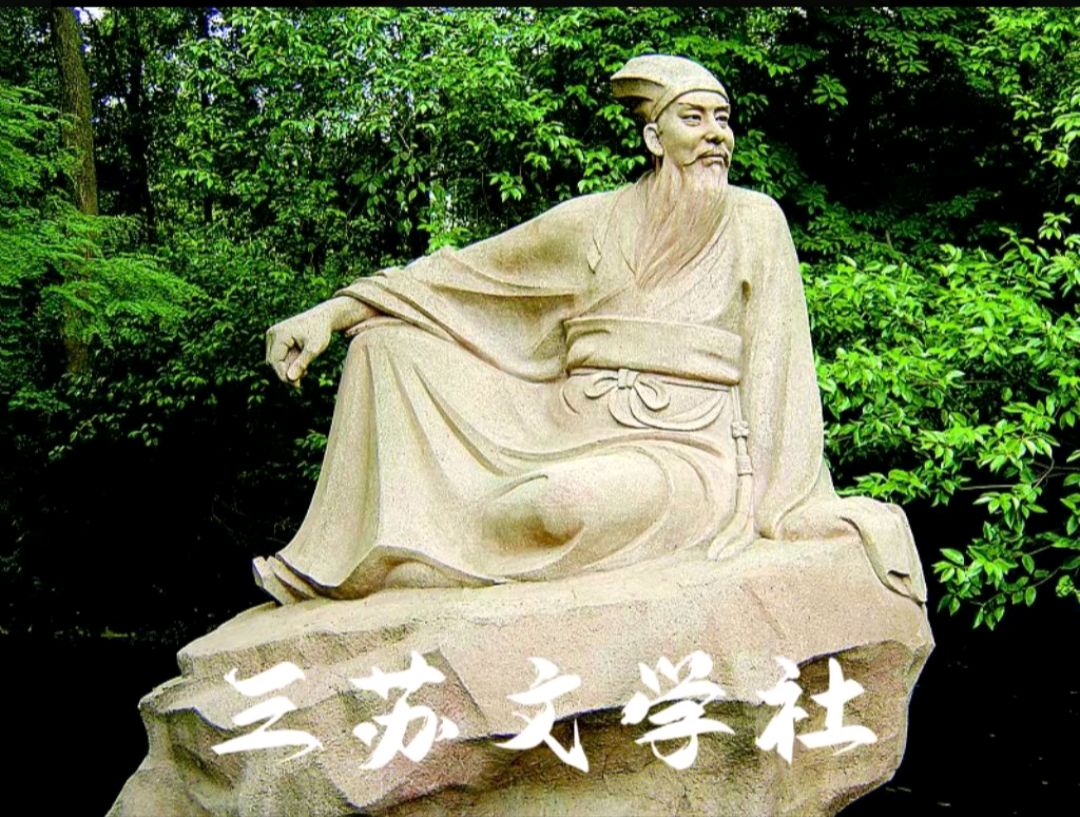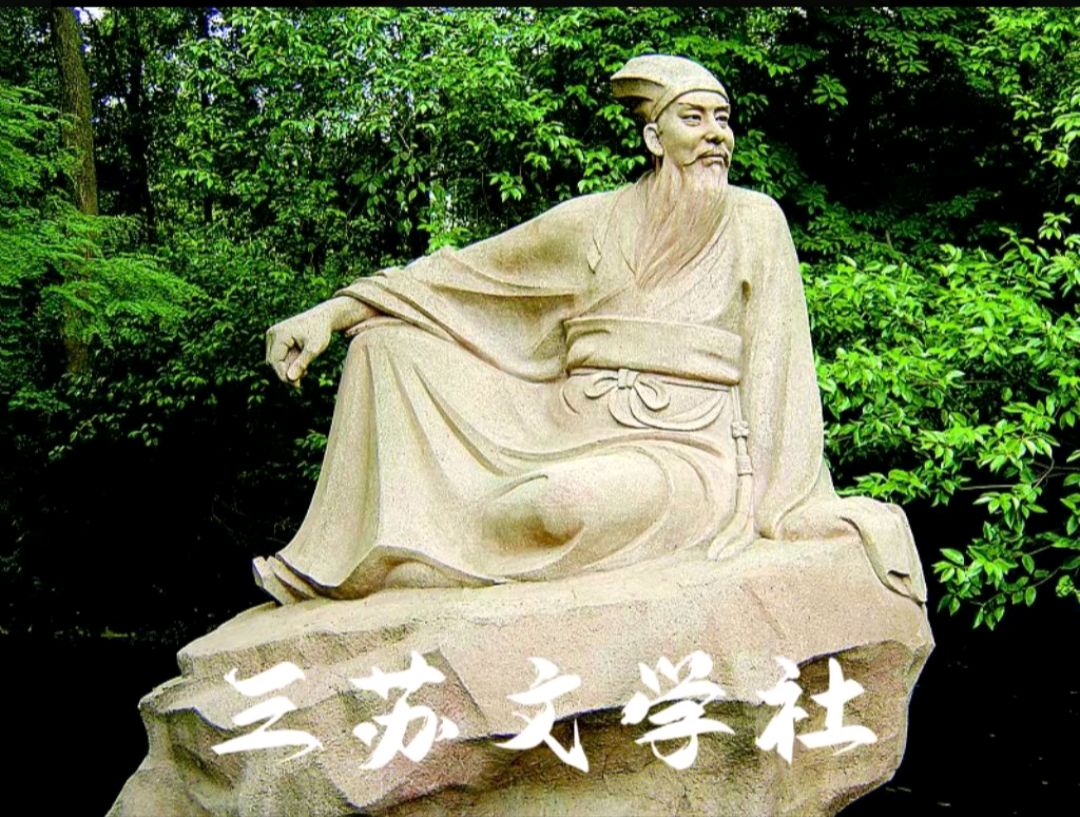任四维(湖北)
又是江南的多雨天,雨是极细极细的,无声无息地下,便濡湿了窗外的竹叶,也濡湿了书房案头那本诗集雅致的封皮。
封面赫然印着几个字,《山雀子衔来的江南》,在氤氲的水汽里,仿佛也成了一抹雨烟。
那个将江南赤壁的雨烟,布谷的清亮,黄鹂的婉转都缀成诗行的人,已经离开烟火人间整整三十年了,他的名字叫饶庆年,从赤壁羊楼洞石板街走出的一位诗人。
我的思绪随着绵绵的雨丝,飘向了那片多雨又多情的土地,那里有被鸡公车碾出深深辙痕,用青石条砌成的小巷,那是万里茶道的起点。
那里有三泉之水汇成川字的青砖茶,在明清小镇的旧巷里悠悠地流淌茶香。
羊楼洞乡的彭家垅,一个被群山温柔环抱的小山冲,便是诗人梦想萌芽的地方,我仿佛看见许多年前,一个衣衫不整的少年,赤脚䠀过桃花溪畔,清凉的溪水漫过脚踝,看见了鸭舌草旁羞涩的水仙,看见野蔷薇在山崖初吐芳蕊,他的叹息声,他童年无言的亲昵,或许都在溪流中被轻轻浣洗。再后来,这所有童年湿漉的记忆,都像山葡萄一样,繁多酸涩而又甘甜,长在诗人生命成长的藤蔓年轮上,最终酿成笔下无声的,不知不觉便湿了窗棂和少女花裙子的江南雨。
我总认为能写出这样婉约清灵诗句的人,必是浸染着江南的秀润与沉静的气质。然而他却是个浓眉大眼,笑口张裂很大的黑壮汉子,诗人有着青石板的质朴与坚韧。在诗人质朴的生命中,却承载了太多的曲折与负重。他从穷乡僻壤枫桥中学的三尺讲台到蒲纺总厂的报社,再到南方经济特区的漂泊,生命从未给予他丰盈的羽翼。直到一九九五年那个冬季,疾病如一场暴雪,骤然覆盖他四十九岁的人生,一切戛然而止。诗人就这样走完人生的路,上了天国。可诗人真的走远了么?

当我打开诗集,闭目沉思,那山雀子噪醒江南一抹雨烟的妙句,便自动在脑中勾起,带着柳笛在晨风中轻颤,露珠绊响牛铃的叮当在耳边响起,他的诗魂,早已与多雨江南赤壁融为一体。
他的诗文,不是书斋里精巧的盆景,而是鄂南土地深处生长出的植物,散发着故乡的温热,柴草烟火气的淡蓝。以及新摘的山茶浸润着爱的香甜。
正因如此,他的声音才能穿透时代,诗就具有了长久的生命力。
诗人逝世三十周年之际,来自全国的诗友,聚在赤壁,诗人故乡来凭悼这位著名乡土诗人。
他那空濛灵动的诗,再度被朗诵艺术家长吟,在银屏传颂,是你为无数诗歌的崇拜者衔来了如画的,多雨的,梦幻般的,山雀子噪醒的江南。
故乡羊楼洞,是诗人最好的归宿,纪念的碑碣会掩盖在故乡白杨山的苍翠之中,而真正的艺术的丰碑,永远耸立在每一颗被饶庆年诗句浸润的心田。
他的诗魂,凝练成故乡大地上多情的种子,诗歌的种子。今日赤壁已被授予诗歌之城,诗词之乡的金字招牌。
诗人的忌日,江南赤壁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在这永不止息的雨声里,我仿佛听见,那雨仍在细细密密地同种子们议论着萌芽的机缘。
窗外的雨,仍在江南赤壁下着,下得温柔而又固执,这不是三十年前的雨,但每一丝雨线里,都晃动着那个从羊楼洞的雨巷中走出来,那个高大壮实而执拗的身影。
诗人饶庆年将一个湿漉漉的永恒江南,永恒鄂南赤壁留给了我们,诗人也将自己的灵魂变成了这江南雨季里,不绝如缕的一抹雨烟。诗人饶庆年永远活在中国田园诗史册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