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赵云飞 《绕过人间去灿烂》
1
地铁,一度给都市生活的人们以兴奋,仿佛是不经意的某一日城市公交一下子就变成地下列车的疾驰。这在古典演义小说中,也只有玄幻的土行孙才能做到。那种地下的、封闭的快速运行极度缩短了人们的交往距离和行程,所谓“穿过大半个城市去看你”似乎只需一个短暂的瞬间、一节超近的路。其间还赋予了地下过程以光影和速度,还有各种意外吧。有一部电影就叫《地下铁》,1985年吕克·贝松拍摄的一部商业电影。1960年法国导演路易·马勒又拍摄了《扎齐在地铁中》,尽管他强调了作家的剧情,但无情节的意识流给新潮流影视带来了先锋性。我在想,这差不多类似于诗歌了吧。当然,诗是语言的感受,电影来自视觉的冲击力。地铁在这里成为风景,并构成文学的一个抒情方式。20世纪中期之后,地铁在欧洲先锋小说和新浪潮电影中登场,并成为文学想象空间的一个重要场景。从几米的绘本、雷蒙·基诺的小说,到德米特里·格鲁克夫斯基的《地铁2033》、村上春树的《地下》……地铁,再也不是空洞的过道——在这么一个狭窄的空间,人们邂逅爱情,潜逃者躲避追杀,流浪者短暂栖身,梦幻者的梦境也通过这一隧道抵达另一空间……
地铁,也意味着艺术?史载,1860年,在伦敦帕丁顿的法灵顿街和毕晓普路之间建造了第一条长6公里的地铁;1898年巴黎开始建造一条长10公里的地铁,叫巴黎地铁。巴黎地铁最初的法文名字是Chemin de Fer Métropolitain,译意即“大都会铁路”,是从英文“Metropolitan Railway”直接译过去的,后来缩减为“métro”。中国第一条地铁线路,是1965年7月1日北京开建的一条地铁,四年后曾经有过一场大火,经过线路改造1971年继续运营。在台湾地铁系统又称“捷运”(Rapid Transit)。有人这样描述:“地铁中,人出现了。他们穿梭迅疾,却纹丝不动。他们分秒必争,却日夜不分。他们总在人群之中,却个个独立无援。”这就是地铁带来的现代人的气息,并赋予遐想和想象。这一切其实都与艺术无关,只不过用通常说的那句话:生活模仿了艺术,因此关于地下铁,也即是艺术活在其中。可以说,地下铁载着诗意的想象在穿梭,不管是1号线或者是5号线,都像是一次短暂的旅行。前边说到毕晓普路,不由也想到美国诗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她在《旅行问题》中说:
此刻,旅行者取出笔记本写道:
“可是缺乏想象力使我们来到
想象中的地方,而不是待在家中?”
地下铁,旅行?非旅行?不管怎么说,算是地铁上的行走吧,或者说是地下地理学的旅行。而且带来了不安分的想象、比较、以及自我的疑问。它是生活的一个变数,就像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说到的机器作为文明的象征所带来可疑与忧郁,“……人从来没有被放在这么一个地方,在其中他们竟能几分钟甚至数小时之久地相互盯视却一言不发”“在戒备的眼睛里白日梦没有向遥远的事物投降;堕落到这种放任中甚至让人感到某种快感。”①他在寓言的意义上试图探讨时代与体验的内在图景,以波德莱尔的“我的眼睛朝后看,在耳朵的深处,只看见幻灭与苦难,而前面,只有一场骚动,”阐释了在都市现象或者说在骚动的人群中一种独具个性的诗歌所释放的灵魂的光辉。
在本雅明隐晦的意图里,一个抒情的诗人是以社会性为主体的,他甚至引用波德莱尔的一个自我辩驳:“我是一个社会诗人”。这里也想到另一个问题——地铁在成为都市生活中的人们、尤其是作为普通人出行或说交通的一个方式的当下,中产阶级,更高的资本者,出入动辄是豪车吧?不知道这一阶层的人对地铁做何感想,他们也乘地铁吗?没有做过调查,大概率也无从调查。但2021年那个特殊的郑州的夏天,我读到子非花的一首诗,其名字叫《地下铁》,或取自同名电影——
地下铁
——所有的消逝都和我们有关
湿漉漉的地铁车站
挂满眼睛
大雨透过雪的幻象
秘密的降临
从生到死
雨水持续地浇灌两端
晶莹的泪珠
永不停歇地旋转
啊啊,尘世啊
为什么透明的……
总是眼泪??
嘴唇所收拢的幻觉
使你一下子坠入周围的空白
世界沁入水中
一条通道骤然打开
“爸爸,这是回家的路”
花朵们醒着,铺满一地
如我返回的漫长路途
而你端坐如一夜的路牌
多年以后,一个早晨
陈旧的地下铁
崭新的人们
寂静的阳光注满一只碗
——这黄金的照耀是持续的钟
在尚未抵达的地方走动
写于2021年8月4日中午
一种从现场、到泪目以至于内省的“持续的钟”,语言直指现实和生命,像地下铁在哀歌。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一场雨水难道只是雨水?地铁和雨水怎么就有了一种诗性的关联?而且每一滴雨都在承载着生命之重。诗人以“所有的消逝都和我们有关”开篇,将诗人的哀痛升华为社会的悲鸣,使这首诗成为当代汉语诗歌直面灾难的诗性见证。“大雨透过雪的幻象/秘密的降临”,诗以雪的冷色调进入到我们的视野,而“秘密的降临”的暗示是什么,是真的不可预测吗?一个悲剧的开端可能就在这个“预测”上,虽然预测的诗学指向不等于预警。而“从生到死/雨水持续地浇灌两端”,就这么从自然现象成为了生命的一个隐痛。地铁隧道在旋转,时间在轮回,竟然在这里是透明的泪水。这不是一个幻觉的生命空间,而是一种戛然而止的生命之痛。庞德也有《在地铁站》,那个静止的瞬间意象是多么优雅。而这里,水的多重流转:雨水、泪水、洪水,却是格外的揪心。不同的画面,湿漉漉的诗的变奏。这种表达,也是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使生命的流动完全现实化的一种选择”——抒情诗人已不再表现自己,诗人的眼睛感受到一种以自发的形象捕捉到的反应。
这首《地下铁》写于2021年一场洪水之后。那一年子非花的诗处在一种快速变化之中,上升是显而易见的,尤其作为诗人也是他最为“谦逊和沉实”的一个阶段。诗的敏感,往往使诗人在一个谷地甚至疑惑的时候,触及到了语言的本质。无疑,子非花在这时的敏感或叫反应,是诚实的,是一个诗人进入了属于他的诗的时间。在这首《地下铁》中,“一条通道骤然打开”,另一个维度上说也是诗人的语言的打开,由此一种画面似幻非幻地超现实而来——“爸爸,这是回家的路”这呓语般的孩子的声音,令人想起电影的一个镜头——《地下铁》中那个寻找父亲的女孩。但这里,回家的路被“铺满一地”的醒着的花朵覆盖——这些花朵是祈祷也是抗拒,是死亡也是守望——醒着的历来就是诗和诗的意识。那个“端坐如一夜的路牌”的父亲形象凝固成了永恒的指引,在生与死的边界点亮微光。
这首诗的一个微妙之处还在于有一个时间辩证法。“多年以后,一个早晨”仿佛一种遥想抑或时空穿越。“陈旧的地下铁/崭新的人们”悖论并置,在消失与想往之间,一个辩证的视野是:“寂静的阳光注满一只碗”——碗这个容器意象,像是寻找的或盛接恩典的“圣杯”,而“黄金的照耀是持续的钟”仿佛诗性的光芒在提醒着,鸣钟一般。子非花的预设在于:“在尚未抵达的地方走动”,为一种历史的创伤找到了一个前移的视角。这一预设也是诗的一种光影。本雅明深刻地说:“魔鬼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万恶之源,另一方面却又是伟大的被压迫者,伟大的牺牲者。如果人们要问是什么迫使波德莱尔把自己对当权者的激烈反抗置入一种激烈的神学形式中,那就得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问题了。”②诗的光影中,揭示也是反思,说出某个事实即是诗的品质。
现在来看看庞德的《在地铁站》——
In a Station of the Metro
The apparition of these faces in the crowd;
Petals on a wet, black bough。
地下车站
人群中幻影般浮现的脸
潮湿的,黑色枝条上的花瓣
在庞德这里,就是一种幻影般的存在和状态——静止的而又是湿漉漉的。但那黑色之上显影的花瓣是那么耀眼,像光与影,像明与暗,甚至是一种生与死,是死亡之后变奏的意象之魂。静止中有一种难测的东西?一如那些地铁电影里的镜头、片段,子非花《地下铁》里的泪水、颤栗,以及历史记载的如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纽约世贸中心下地铁坍塌、韩国大邱市地铁发生纵火……每一个幸存者都成为了记忆的通道,而诗歌本身,像是那条逾越灾难依然通向回家的路。
如此,地铁以一个文学镜像,在诗意地前行。我们更是祈愿它带来美好的记忆。记得几年前武汉地铁的出入口,装置了诗歌的影像,一个个诗人的作品就在那些站点的影像墙面上,我的诗也有幸曾添列其中,每当看到的朋友告诉我,“在武汉地铁口读到你的诗了”就觉得随他们做了一次短暂的地铁旅行,如同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对视、一次告别。这种地铁里的诗歌影像,据说最早出现于1986年的伦敦,说是伦敦大学的朱迪斯·舍纳克,乘坐地铁北方线时突发奇想,致信伦敦地铁公司,提出地铁上应有诗歌海报,愉悦旅人也有艺术感。当然参与的还有另外的诗人。在被采纳之后,一场“地铁诗展”在几位诗人的策划中开始了,诗歌一次次出现在英国各地地铁的广告车厢中。后来还将这些诗歌结集出版,叫“地铁诗歌”,如今还陈列在伦敦地铁博物馆商店,散发出诗歌独特的光影……
2
光影就是抒情。林间空地上斑驳的光影在风的吹送下极为协调、放松;而地铁下随着列车的呼啸来去和旅人的匆匆上下仿佛在拉动着光的线条,光影有了不同人的姿势和形象。每时每刻在赶路的人没有谁注意到光影的存在,他们目的鲜明地朝着一个方向,在本雅明看来,唯有像波德莱尔那样的“游手好闲者”在漫无目的的东张西望中找到了一个城市“情感的方式”——“当毒辣的太阳用一支支火箭/射向城市和郊野,屋顶和麦田,/我独自去练习我奇异的剑术,//有时碰上了长久梦想的诗行。”③ 读波德莱尔,会感受到他的诗就是光影之魂。关于光影,在其阐释里有一个哲学的维度,如清代王夫之的“但于光影取之”,确切地说算是浮光,这不是我们想要的命题。于诗而言,应倾向于这个哲学维度的反面——一种深刻的诗性。寒山有诗云:“光影腾辉照心地,无有一法当现前。”读之,似有诗的清辉从身体里飘来,一种肌体之感。但诗在现代语境的当下,光影也不再是如此单纯的自然符号,它是一种光影交错,其迷离状必须拆解开来方有一个画面或真相。光与影,等同于诗的语言和它观照的事物。子非花用更直接的语言写到——
每一片树叶都是新的
穿着四月最新的时刻
闪着光的,战栗的,隐匿的
在初夏的黄昏偷走光晕的
到底是谁?
——子非花《光影》
在这首题目为《光影》的诗中,诗人并非简单地描摹光影,而是将“光”作为一种方法论,一种审视存在以及情感、切割时间并进行重组的多棱镜。在“四月最新的时刻”那种隐秘的战栗中叩问,“偷走光晕的到底是谁?”这里的关键是:光晕,是什么?诗人没有过多的铺垫,就像前边提到的《扎齐在地铁中》电影,没有叙事(甚至连铺垫都省略了),只有意识在流动。或许,这里边有一种无以言说的隐秘,还有影像——既是颤栗的新却内含着隐隐的不安。正是这样的场景在子非花的意识里流动,成为记忆的存在而又在渴望的“崭新的时刻”,他的这样一组诗——《崭新的时刻》大抵都多多少少带着这个心境——有一种挥霍的、碎片化的语言行动。语言就是行动的本身,但又不得不隐去其中的影像。叶赛宁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在我们的肌体感觉的冰层下,有一个迷人而冷酷的美女在为我们歌唱,”坦言之,事情就这么简单且直接,诗人为此而动身。但艺术有着扑朔迷离的一面,像诗中的爱情,叶赛宁深有灼见:“从外表上就可以观察清楚的一切事物,无论何时何地也不会诞生于双眼闪着星光、头上罩着神秘光轮的马槽中。星辰与圆环,乃是引导读者走向新生活和新鲜愉悦的花园的那种基本常识符号。”④或许,这就是诗之所以称为诗的神秘性所在。一个诗人的语言就是他自己的星辰。也就是说,语言有它的夜空,语言是在某个暗的时间的一次投射。
一首诗最终可能就是一种光影。不可多解,解了都是心结。比如“细小的可能”也会带来长久思忖的某种宿命感——子非花也有言,“直接抵达人类永恒的宿命感的一种方式”,一种行动是以直线的方式冲撞而去,而后有了全新的可能,这不仅是眼睛的乃至身体的惊奇,也是诗的一次历险记——从昨夜的沉醉、颓废以及悲伤到早晨又一个新的时刻,语言有了它承载的光影。崭新的抵达,在这里有了一个纠缠的内涵——我们无法以一片空白的状态迎接新生,每一次抵达都背负着过去的痕迹。“新的景象屡次重叠 / 早晨印满脸庞”。脸庞,是多么具象而完美的存在,在夜与昼的交汇点上,在明与暗的光影上,充满质感地构成了一次审美。
诗人就是对语言注入想象的人,但一首诗的语言一定是起源于诗人所见的那部分影像,当然在诗中多数时候就是一种真实、真相,进一步引申也叫真理。正如苏珊·桑塔格说到的,在摄影者美化世界和努力撕下世界的面具之间,不存在哪一方更有大的美学优势。“由于每张照片只是一块碎片,因此它的道德和情感重量要视乎它放在哪里而定。一张照片会随着它在什么环境下被观看而改变。”⑤苏珊·桑塔格也由此引入了维特根斯坦对词语的论断——意义就是使用。摄影和词语一样,在暗示着一种非想象的存在——现状。词语使我们所在的世界成为抒情的对象,具体于某一物或人,所抵达的是自己的现实,而摄影“通过揭示人的事物性、事物的人性,而把现实转化为一种同义性。”二者从本质上说,都属于光影的艺术,都从一个片面的瞬间传达了我们所要知道的现实\真相。在这里,一个重点所在:即光的投影。光不具备穿透性,但有了穿透性的暗示。
光影,是一种诗性的发现。曾好奇于子非花抒情主题的一个“崭新的时刻”。光影在时代的影像移用中有一种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泯灭自我的法术,让我们在沉醉地赞美的时候有一个迷蒙的梦境。没有哪一个人会从梦境中看清事物。由此,想到“崭新的时刻”的一个来处——在光与影的交错、新与旧的重叠、抵达与逝去的辩证之中,诗歌在“发现”,词语在抵达。“问题集结/在时间的底部/雨滴在不间断的应答中/过滤出隐藏的细节”(子非花《雨夜》)。你是诗的眼睛时,眼睛也是你的诗。诗歌就是发现的眼睛,它带着人类的精神去发现美也发现问题和晦暗,并赋予一切事物以生命。当心碎于一个人的离开“星辰的驰离/光影的离散”;当想起流失的光影,却再回不到那个“此刻”“一只孤岛/已经离开无限远”;当一切都在变幻,在成为阴影般的记忆,甚至所要的“最新的抒情/卡在到达的中途/和眼泪中间”……甚至有一天终于不再拘于自己忧郁的情感,可以在大自然中抒一把情的的时候,一群咩咩的嚎叫的羊的悲伤中还又围拢着更深的、难以释怀的悲伤以及悲悯——
我的小碎片悬停着泪珠
在汽车玻璃里流淌
我想到:内心的孩子
也在疯长,像噼里啪啦的青草
——子非花《羊孩》
诗歌,是光影的承载者。在我们遇见了太多的事物\事件及其晦暗时间,我们的抒情便不再是前边说到的摄影的模式,尽管本雅明说,“照片变成了历史事件的标准证据,并隐含政治意义”,我们的抒情面对这一时间也会是最现实的时间,也会是直接的、智性的审视世界,还有自己和世界的关系。诗在凝固或冻结了某一光影,光影默许了词语的傲慢、尖锐和进入。但始终带着温度的、柔软的力量的,是诗人的内心。如子非花写给孩子的那首《树屋》——
是的,未来是一颗微小的松针
正躺在一缕光影里
风,像粉末一样幸福地向我们吹着
3
“未来是一颗微小的松针”,这听起来是多么惬意的乌托邦的情调。瓦尔特·本雅明在《巴黎,十九世纪的都城》谈到建筑及其新的生产方式、乌托邦等问题时,引用了一句诗:“每一个时代都梦想着下一代”——来自米什莱的的《未来,未来》。⑥其讨论的维度,无论下一代或最近的将来,都指向了未来。未来的确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最近一个较有热度的诗歌话题就是:新抒情主义及其未来。本不想谈论这一类带有概念性的问题,因为诗歌的突破在于一个人的经验与生活的摩擦,其间灵光闪现的瞬间有了新的语言,但这些问题一经出现不得不去思考,关键还在于像子非花这样身边诗歌朋友所提出,“新抒情主义之维度”“新语言”等问题,颇感意外并欣慰地想到,本雅明关于艺术“迎向灵光消逝的年代”那种带有觉醒意识的声音。
而事实上,“抒情”是一个宏大且虚空的词,它框定在诗歌语义上有了其抒情主义的诸多内涵,就新诗百年的演进来看,也是一个不断纠正的过程,如同西默斯·希尼“诗歌的纠正”,其根本必然是与一种相应的现实所对称。所以诗歌的新抒情主义,首先基于的是传统的或某种既定的动作之上的一个考量。如果要追溯一个历史语境的的话,会想到40年代的穆旦所提出的“新的抒情”。穆旦本人是诗人,也是翻译家,其间指定有一种微妙的东西在词与物中间像是一个信息系统为他的诗提供了新的路径,或叫做“翻译的影响”?但他的理论内涵却是在一个战火年代特殊背景下诗歌去向的问题。穆旦提出了“新的抒情”的诗学主张,不简单否定传统抒情,而是引入了理性精神——所要的新的形象,即赋有时代内容的——“发现底惊异”。穆旦的“新的抒情”可以理解为在个人情感与时代精神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与超越。穆旦对这一理论的思考主要体现在他1940年的两篇评论文章中,他明确反对两种诗歌倾向:一种是枯涩的语言,指向当时国防文学和部分左翼诗人;一种是“贫血的堆砌的词藻”,所谓现代派诗人“牧歌+自然”的抒情。在他看来,前者过于直白而缺乏诗意,后者则过于空洞而逃避现实。因此提出“第三条路”——“新的抒情”——既有饱满情感又有思想深度的诗歌。李章斌在文章中说:“应该注意到,穆旦提倡的‘新的抒情’并不仅仅是一个文体问题,它强调的是诗歌与‘时代’的谐和,诗歌应该表现历史‘朝着光明面的转进’,‘新的抒情’的本质就是‘新生的中国’的本质,可见,‘新的抒情’主张背后隐藏着一套历史理念和民族意识,它们体现为一种民族进步的理念……”⑦可是穆旦也未能实现自己预设的这个方案。随着穆旦思想的转变,其诗歌风格逐渐发生了变化。譬如写于1940年的《蛇的诱惑》显示出他诗歌中的宗教维度和批判意识。这种转变使得穆旦的诗歌创作,充满了情感的冲突和沉郁的基调,走向了更加复杂的可以说是福柯所说的现代性的一面。
由此想到子非花“新诗的抒情主义”思考,有一个穆旦的“新的抒情”的传承?在我看来,是洞见了穆旦与历史语境之后,有了一个当代诗的“新抒情主义”的诗性思考而走向一种理论内涵的新维度——新抒情主义诗学。
尽管尚未读到子非花的系统性的理论阐释文章,尽管每一次新抒情主义维度的提出\讨论都有一个指向性尚待理论性融合,但并不妨碍作为诗人的子非花的深度思考。尤其相对于穆旦那个战争与历史存亡的历史背景,当代的诗人在历史语境变迁的当下,在思考什么并如何写下与时代相对称的诗歌,这几乎是一个使命,虽然子非花轻描淡写地说到了“愉悦”,但其核心主张还是带来了值得探究的问题。可以说子非花提出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抒情取向——
历史境遇——全球化时代和个体悬浮。
核心主张——新语言与神性写作。
意象特点——超现实的断裂性。
时间维度——多维和块茎时间。
终极追求——人类永恒的宿命感。
诸多当下境遇下的问题,的确是诗学应该思考的一个动向。从子非花稍微零碎的观点看,也是一个有思想的诗人所特有的一个鲜明的方式。有意思的是,他在提出“新语言”这一新抒情维度时,他的一个系列的诗歌叫作《崭新的时刻》,这在意识深处甚或可以说是潜意识上的吻合,似有“神性”的一面。从子非花这几年的诗歌探索和语言变化看,《崭新的时刻》就是一次“新语言”实验。那种突如其来的、无铺垫的、碎片化的、断裂的语言,被一些论者说成是“词语暴动”,因为没有平滑的叙事,没有日常的逻辑性,带来了歧义的东西和想象空间的神秘。如《光影》中,“昨夜的痕迹依然在井喷:啤酒,残渣,碎裂和眼泪”,带有暴力的方式侵入意识。秩序?非秩序?一个秘境在意识上有了一次呈现的瞬间。这一神秘表达通常被人们看作超现实主义手法。深层现实是什么?诗人想要的效果是不同的人有一个对应的维度,甚或可以说是不讲理地就这么说出了,什么也不必考虑包括读者甚至自己。诗歌的确也不需要讲理,它有任性的权力。如果把这一方式看作是子非花激进的语言实验和神性追求,那么,这些诗歌意味着子非花在朝向专属于他的风格。当然,所有的语言都在路上。子非花说诗歌是“人们孤寂心灵最后的安慰”,诗歌也是“喧嚣尘世里最后一滴纯粹的眼泪”,与其说这种说法是对诗歌的理解,不如说是他对这个社会及其前文说到的地铁、光影所带来的幻象和现实的洞察之后的一次审美,或情感重量。在《木头的故事》中,他写道:“你内心的碎屑,全部的柔软/在刹那完成”,个体生命在某一时刻、甚至是生与死的边界上,一个刹那间,词语和内心一起柔软起来——一种对现实的无奈不是悲悯能够完成的对视,语言这时仅仅是对生命最卑微的一种守护。有了这种对生命、以及现实的探视和理解——一种有着深沉背景的存在——进而可以延展为诸多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也就清醒地觉悟到了诗所要的语言该是什么样子。暴动?暴动这个说法在这里显在地有了它本质上的合理性——
让空间离奇的失踪,
再召唤一些新叶。
——《雨夜》
在今天以至于过去的一段历史中,诗歌的社会功能越来越被缩小、挤压,在一种汹涌的社会洪流中,诗歌只是那个形单影只的智者,拥着一条溪流穿过荒野或城市。尽管如此,诗也必然是从最远的过去涌向最近的将来的一次次行动。未来是什么?用子非花的一个隐喻:崭新的时刻。这里边有一个时间意识——一种在时代深处对时间本质的揭示。这一揭示方式,有时候是用一种“最微小的单元”那种透视,看见一种存在状态,甚至是存在的深渊,并试图以诗的微光作为救赎的方式。诗人也意识到这尘埃般的世界,即便“碎屑”的东西也可能有着双重性:“孕育着无所不在的危险”与“你们是最卓越的精灵”。这里的一个辩证认知在于:一种超现实的或者说后现代的抒情,既承载了存在之重又有着生命之光。诗的本质在这里得到了诠释。在子非花的语言里,时间可以是断裂的,甚至可以是一种幻象——超越现实而抵达一个秘境——或许是体验过的或许是将奔赴一个新的体验,这使他有了玄学一般的句子:“水滴空中碎/水滴水中碎/水滴镜中碎。”时间之水在三种不同的空间(或可看作自然、内心和幻象这三维空间)有着什么样的指向?那面镜子碎了以后,还能镜照出什么或者说看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古时候的人在游走或生存之中,常困惑于周围的境遇,就向夜空的星星祈祷,期望神的降临。而当下,我们依然带着诸多生活的疑问寻找语言的神祇。子非花“水滴”的玄学抒情延续到另一个《早晨》,“掌纹急切地/攥住时间颗粒”。为什么是掌纹?显然“掌纹”既是一个人生命的独特印记,也暗示了命运的不可抗拒;而“攥住时间颗粒”则是一种把握存在的可能。这样的句子的确蕴含了对人类永恒宿命感的思考意味,合乎诗人所说的:“诗歌是直接抵达人类永恒的宿命感的一种方式”。
这是一种深远的方式,对于一个有使命感的诗人来说。这一终极问题也带来了我们的诸多思考——
诗人只主导自己的意识就够了;
相对于自己的个人化写作,新抒情者也当更是社会诗人;
每一次都是一个投影,重点在于发现什么样的影像;
纯粹的语言里有一个抗拒的力量;
来自现代的文明必须有诗的一个形象;
诗担负着向未来的一个使命……
在诗人的认知里有着深度存在宿命感。一个人的语言指定是内在于自己的意识之中,不是思考所能呈现的,所以一种独特性也就是诗的神性。这也不是想有就有的,它是在某个瞬间从时间里崩裂出来的东西,如电光石火的一个初始体验 ——一次爱情,一个事件,一个神秘的时刻……只有那个在身体或说心灵深处有着独特东西的人才有自己的神性。所谓诗歌走向神性,也就是一种存在成为诗的永恒时间。对于一个诗人来说他的独特性就在于他有一个历史的镜照也有一个灵魂的镜照。新抒情维度需要的是开放的诗学视野,需要在工业化、再造的文明、甚至都市的噪声中找到自己的声音和情绪体验,甚至在混沌或断裂之中,也有一个内心的自明。因此,新抒情主义所建立的是一个新的现代化的时间秩序。
注释:
①《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瓦尔特·本雅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第165页。
②《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瓦尔特·本雅明著,三联书店 1989年,第40页。
③同上,第89页。
④谢·叶赛宁《玛丽亚的钥匙》,见《国际诗坛》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197页。
⑤《论摄影》苏珊·桑塔格,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107页。
⑥《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瓦尔特·本雅明著,三联书店1989年,第179页。
⑦李章斌《“感时忧国”与宗教视镜的角力——重探穆旦的“新的抒情”》见《南方文坛》。

高春林,当代诗人,兼事诗歌评论。主要著作有诗集《夜的狐步舞》《时间的外遇》《漫游者》《神农山诗篇》《听见身体里的夜莺》《空镜之下》,和随笔集《此心安处》等。曾获第三届河南省文学奖、第二届(2017)十大好诗奖、诗东西诗歌奖等奖项。主编有诗歌选本《21世纪中国诗歌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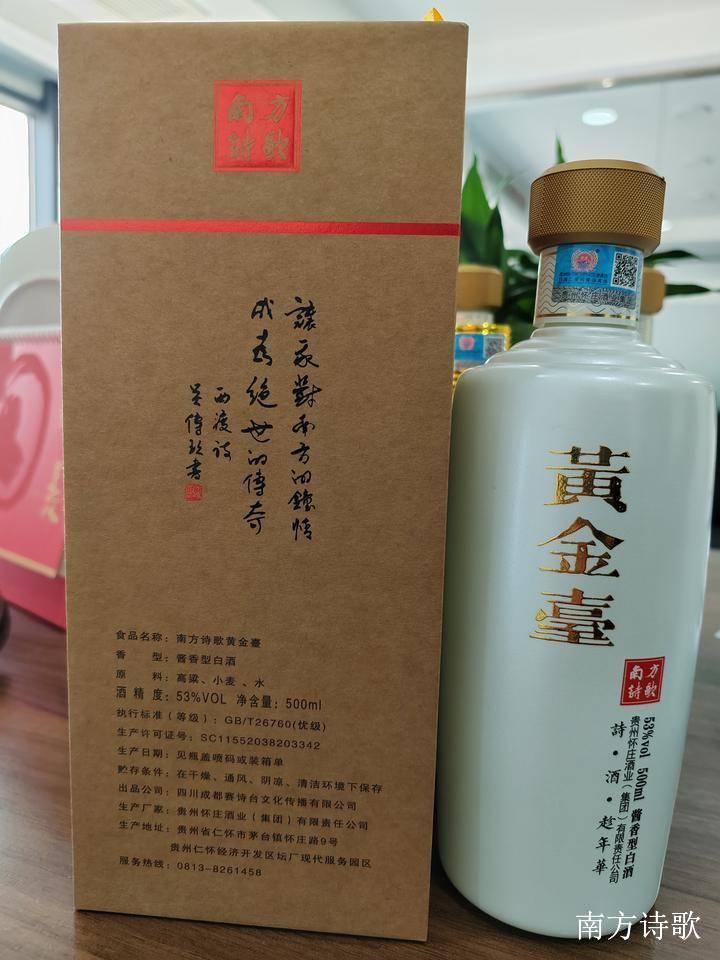
让我对南方的钟情
成为绝世的传奇
——西渡
南方诗歌编辑部
顾问:
西 渡 臧 棣 敬文东 周 瓒 姜 涛
凸 凹 李自国 哑 石 余 怒 印子君
主编:
胡先其
编辑:
苏 波 崖丽娟 杨 勇
张媛媛 张雪萌
收稿邮箱:385859339@qq.com
收稿微信:nfsgbjb
投稿须知:
1、文稿请务必用Word 文档,仿宋,11磅,标题加粗;
2、作品、简介和近照请一并发送;
3、所投作品必须原创,如有抄袭行为,经举报核实,将在南方诗歌平台予以公开谴责;
4、南方诗歌为诗歌公益平台,旨在让更多读者读到优秀作品,除有特别申明外,每日所发布的文章恕无稿酬;
5、每月选刊从每天发布的文章中选辑,或有删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