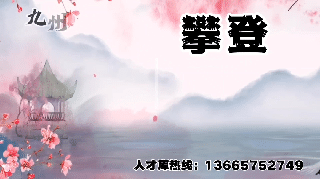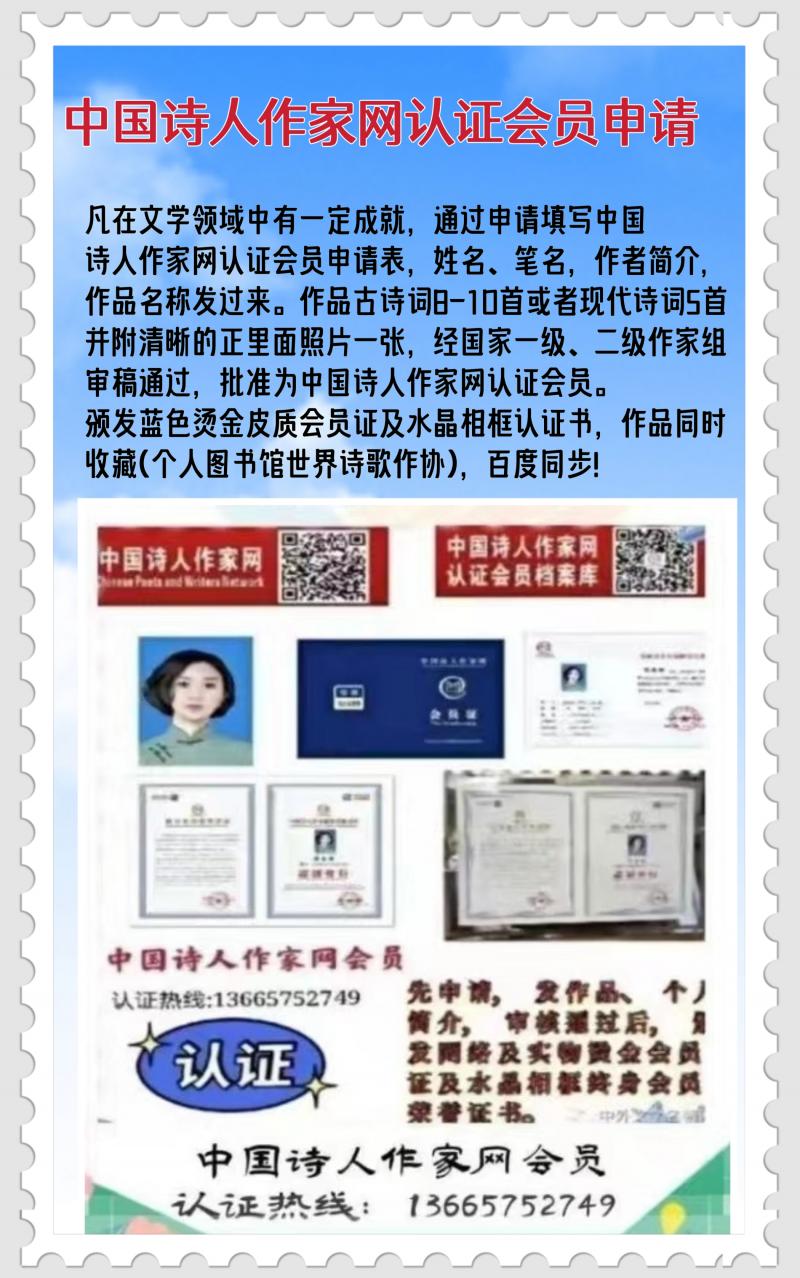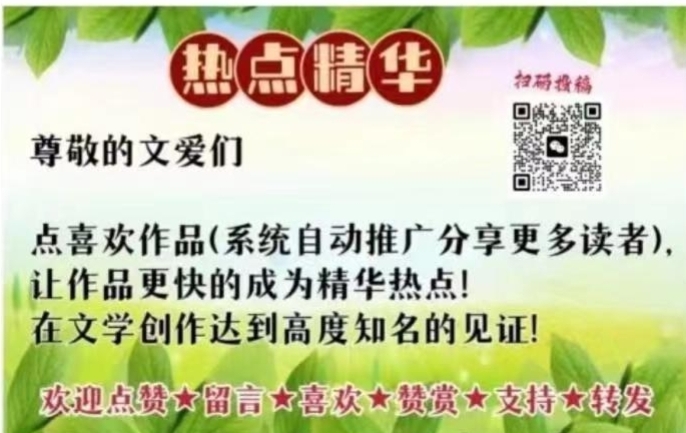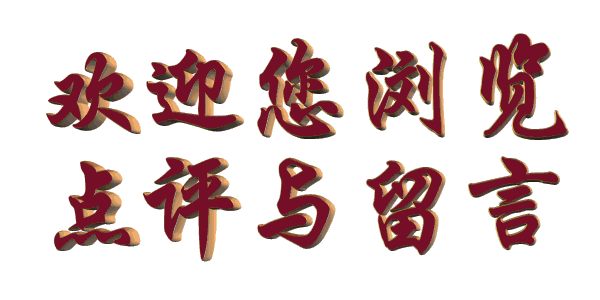瓮井:散文诗两章
金V诗人: 童光红
网络主播:艾飞
文学总监:阿紫
执行部长:张 明 .冷雪.武立群
执行总编:玫 瑰
1
檐角漏下的光在陶瓮上洇开时,我正用竹片刮去内壁的积尘。
那些被岁月啃噬的裂纹里,还凝着三十年前的米香,那年大旱,母亲把最后一捧粟米按进瓮口,釉面裂开的声响轻得像叹息,却让整座瓦屋在冬夜里发抖。
现在它搁在老灶旁,腹径处的凹痕是我十二岁那年摔的。
父亲蹲在门槛上补它,粗麻线穿过碎瓷片时,他的手背蹭过我额头,温度比灶膛里的火还烫。
后来我总摸那道缝,指腹陷进去的弧度,竟和母亲纳鞋底时顶针的凹痕重叠。
清晨的雾漫进来时,瓮里的水开始说话。
不是叮咚,是极轻的震颤,像有人隔着陶壁在叩门。
我舀起半瓢,看水纹在碗底洇成圆,又碎成星子,原来那些裂纹从未真正愈合,它们只是学会了藏起尖锐的棱角,把每道伤口都磨成透光的窗。
灶膛里的柴噼啪响,火星子溅到瓮身上,又倏地缩回去。
我忽然想起去年春天,邻家孩童举着石子砸它,碎瓷片飞起来时,我下意识去接,掌心被割出血珠。可那些碎片落在地上,竟没有一片扎进泥土,倒像是被谁轻轻托住了,散成一片银亮的河。
此刻瓮口浮着层薄霜,是昨夜我搁了半块腌梅。
霜花沿着裂纹攀爬,像谁在替它补一件透明的衣裳。
我伸手擦净瓮身,指痕里渗出细密的水,顺着指缝滴落,在青石板上敲出细密的鼓点,原来所有的破碎都是伏笔,等时间来把它们串成项链,每一粒珠子里,都盛着没说出口的圆满。
2
老井的青苔又厚了三分。
我用枯枝拨弄井沿的苔藓,碎屑簌簌落进水里,惊得半尾红鲤摇尾而去,波纹撞在井壁上,碎成一串摇晃的星子。
这口井比我老。
听奶奶说,她嫁过来时,井边那棵皂角树才手腕粗,如今树冠已遮住半座院。
井绳磨出的凹槽里,嵌着三代人的指纹:祖父的粗粝,父亲的温厚,我的指尖还带着未褪的奶渍。提水时,桶绳绞紧黄昏,水桶碰着井壁,叮咚声里混着皂角花的甜,和着奶奶喊我乳名的尾音,在井里荡成涟漪。
记得七岁那年,我蹲在井边洗菱角。
菱角的尖刺划破手指,血珠落进水里,井里的月亮突然碎了。
我慌忙趴在井沿哭,奶奶用蓝布帕子裹住我的手,帕子上的皂角香混着井里的水汽,渗进我每道褶皱里。
她说:“井是大地的眼睛,你疼,它也疼。”
后来井台边多了石凳,母亲在井边搓洗床单,棒槌声惊飞了啄水的麻雀。
我趴在石凳上写作业,墨水瓶倒了,蓝墨水渗进青石板的缝隙,像一滴凝固的夜。井里的水晃了晃,倒映着我的字迹,把“永远”两个字泡得软软的,像要化在风里。
现在井台上落满枯叶。
我放下水桶,听见井绳摩擦井壁的声响,和三十年前的一模一样。
提上来的水晃着,映出我鬓角的白,和井里晃动的月。
忽然明白,井从来不是在装水,它是在装时间,装祖父的烟袋,父亲的草帽,我的纸鸢,装所有被风卷走的、被雨打湿的、被岁月揉皱的,却始终不肯沉底的故事。
暮色漫上来时,井里的月亮又圆了。
我蹲在井沿,看自己的影子沉进水里,和那些未说出口的话一起,慢慢沉,慢慢沉,沉成井壁上新的苔痕。
风掠过皂角树,落了几片叶子在水面,荡开的涟漪里,我仿佛看见奶奶的蓝布帕子,正轻轻擦去井沿的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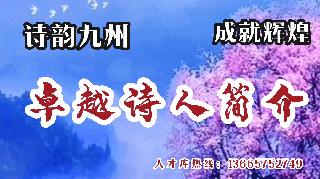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童光红,男,70后,安徽凤阳县人,草根文学爱好者,喜欢写作,忠于原创,酷爱散文诗。
曾有作品发表在《滁州日报》、《散文诗选萃》、《黄河诗报》、《中华诗词报》、《南疆诗刊》以及《橄榄绿诗刊》等。
近期作品主要散见于《凤阳文学》,《定远文学》,《乡村文学》,《众望文学》,《山水田园之约》,《名家美文欣赏》,《三江文学散文诗刊》《三江文学》,《江南文学》,《神州散文诗》,《灌河文学》,《诗博刊》,《安徽诗歌》,《辽宁散文诗》,《中国诗歌网》以及《中国作家网》等网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