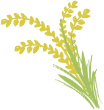在龙船调故乡遇江柳先生
◎郑能新 中国作协会员
清江源头的碧水如同大地深藏的一脉诗行,自利川的山峦间蜿蜒而出,在龙船水乡,那碧水与两岸的吊脚楼相映成趣,木楼的倒影在水中轻轻晃动,仿佛一幅流动的水墨画。水面上偶有乌篷船划过,船桨搅碎了倒映的天光云影,也搅起了阵阵带着水汽的清凉。岸边的杨柳依依,枝条垂落水中,随风摇曳,像是在与这清澈的江水低声絮语。偶尔还能听到远处传来的龙船调歌声,悠扬婉转,与这水乡的景致融为一体,让人恍惚间不知是在画中还是在现实里。
沿江边南行数百米,便是“天下第一水洞”的峡谷奇观。继续前行,山体忽然张开大口,如同一道被巨斧劈开的山门,高近百米,宽约六十余米,灰褐色的岩壁上布满了青苔与藤蔓,更显岁月的沧桑。
我们乘着小舟,悄无声息滑入洞中,霎时清凉的水汽裹挟着地底的微息扑面而来,尘嚣顿失,仿佛潜入一个被时光精心窖藏的梦境里。
船行于暗河之上,幽蓝的灯光如沉落的星星浮映在水面,照出船底晃动的流痕。洞壁两侧,钟乳石如凝固的瀑布、倒悬的森林、垂落的巨莲,万年光阴以滴水之慢工雕琢出这地宫的无言奇观。彩灯如神笔点染,柔光在石幔上流淌,似给这些沉睡的精灵披上了霓裳:此处金红如霞光蒸腾,彼处青碧似春水凝脂;石笋在光影里拔节,恍若有生命在无声滋长。最是那水纹灯效,将粼粼波光映射于穹顶,洞顶竟化作一片倒悬的清江,我们的小舟恍然在倒转的天地间浮游。身在此境,人如坠入龙王的水晶宫阙,流光溢彩间,只觉此身已非尘世所有。
正沉醉于这水石光影的迷幻时,一缕清越的歌声如洞中清泉,裹着石壁温润的回响,澈越清灵地传入耳鼓:“正月里是新年哪咿呦喂,妹娃子去拜年哪呵喂,金哪银儿索,银哪银儿索,那阳鹊叫啊捎着莺鸽。妹娃儿要过河,是哪个来推我嘛……”那熟悉的龙船调旋律,字字句句,如清江之水深情脉脉流来。原来是导游小姐引吭高歌,她身着靛蓝土家织锦,站在船头迎着水汽轻吟浅唱,尾音在钟乳石间流转,仿佛千年时光都在这歌声里苏醒。歌声渐起时,洞内的光影似也随旋律起伏:灯影在石笋上跳跃成音符,水波在船舷边漾作歌谱,连洞顶倒悬的“江面”都似泛起应和的涟漪。船上同游的友人们在导游的调动下齐声和唱,他们是真的被这歌声勾动了心弦,你一句我一句,粗粝的嗓音混着清润的女声,竟在这水晶宫里织成了新的乐章。
一曲终了,导游小姐笑言这是龙船调的故乡小调,当年便是这样的歌声,顺着清江的水、乘着溶洞的风,飘出了峡江,飘成了响彻神州的“东方小夜曲”。
船工这时也插话进来:“这曲儿啊,原本土里生长,叫《种瓜调》,是土家人逢年过节划彩龙船的伴奏曲目。后来,利川文化人将它整理压缩改编成为《龙船调》,它顺着清江漂流,又漂洋过海,唱响了人间……”
在大家的一至要求下,船工唱起了《种瓜调》:“正月里是新年哪啊,瓜子才进园哪啊,哥呀么哥哥,妹呀么妹妹,种瓜要种黄杨瓜呀……”他的嗓音带着清江浪涛的粗粝,却又裹着山野草木的清甜,每个字都像从土里刚刨出来的瓜籽,带着湿漉漉的生气。船儿犁破水面,歌声便顺着水波荡开,与洞壁碰撞出嗡嗡的回响,仿佛整座溶洞都成了天然的共鸣箱。先前和唱龙船调的友人们此刻都静了下来,只听那朴实的歌词里,藏着土家人辛勤侍弄庄稼的勤恳,藏着田埂上男欢女笑的逗趣,还藏着烟火人间最鲜活的模样。”
歌声渐歇,洞中的回响却久久不散,仿佛还在空气中打着旋儿。船工缓缓开口道:“这《种瓜调》啊,才是《龙船调》的根。你听那‘种瓜要种黄杨瓜’,多实在的愿望,就像土家人过日子,一步一个脚印,不慌不忙,却自有甘甜。”顿了顿,他又说,“土家的歌谣,就跟这清江的水一样,看着平静,底下却藏着千回百转的故事。每一句唱词,都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念想,是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话音刚落,不知是谁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混着洞中的水汽,也成了这歌谣余韵的一部分,让人心里泛起一阵暖融融的感动。
出得洞来,回首那吞吐船只的幽深洞口,龙船调的余韵仍似水纹在心头荡漾。船工朴素的话语如一把钥匙,悄然打开了我理解这片土地的心门。这龙船调,原不过是清江之畔一粒微小的种子。幸有慧眼之人拾起,借这“天下第一水洞”的奇景沃壤精心培育,竟使这粒微尘绽放出惊艳世界的奇葩,为故乡撑开一片繁荣的荫凉。
游人熙熙,却少见熟面。正跟几位鄂州文友感叹:“以往,每到一处,都会碰到几个熟人,这是第一次没有碰到故旧的旅行!”
话音未落,一声颇为磁性的男中音就在耳边响起:“能新,你怎么来了,采风啊?”
突兀之间,竟让我一时有些惊愕:真没有想到,在此,竟然碰上了江柳先生!
江柳先生曾主政我的家乡黄冈多年,有着很好的政声口碑,他兴文化、重民生,留下了很多标志性建筑,博物馆、黄梅戏大剧院、遗爱湖公园,哪一处都可以载入史册。尤其是他还是个颇有文化的官员,对东坡文化的研究,竟令许多专家学者都深感汗颜!这样的人,我自是发自内心的尊敬,一番亲切交谈,方知江柳先生是带着家人到利川休假,在此与我不期而遇也!
江柳先生尚在工作岗位,位高权重。如若他稍事透露一点口风,肯定会有不少地方随员陪同,但我仔细观察了一下,除了家人,竟无一人随行,当下,心中又是一番感叹!
由此我想,一件文艺精品,哪怕产生于乡土民间,只要它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根脉与真挚的情感共鸣,便拥有穿越地域与时空的力量。就像这《龙船调》,从清江船工的号子到唱响世界的歌谣,正是因为它扎根于这片土地的生活肌理,饱含着人们对自然的敬畏、对劳作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它就会体现出一种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而一个好官,只要心系民众,真正把百姓的冷暖放在心头,用心倾听基层的声音,用行动解决实际的困难,就能在群众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江柳先生正是如此,他不慕虚华、不搞特殊,以朴素的姿态融入生活,这份淡泊与务实,恰如《龙船调》中那份源于乡土的本真,虽不事雕琢,却有着直抵人心的力量。
此刻,在这龙船调的故乡与江柳先生偶遇,仿佛是一种奇妙的呼应,让我更加坚信,无论是文化的传承还是为官的操守,其核心都离不开对本源的坚守和对真情的呵护。这种坚守,不是墨守成规的固执,而是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对初心的敬畏;这种呵护,也并非刻意为之的作秀,而是发自内心地将责任扛在肩头、将情感融入日常。就像这清江的流水,生生不息滋养着岸边的草木。而文化的本源与为官的真情,唯有深深扎根于生活的沃土,才能在岁月的沉淀中愈发醇厚,在人心的滋养中历久弥新,或许,万物皆同此理也!
作者简介:郑能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黄冈市文联副主席、黄冈市作家协会主席,现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家协会散文专委会副主任。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300余万字;有40多篇入选《小说选刊》《读者》《新华文摘》《短篇小说选刊》等国家级选刊、选本;有多篇作品被选入大、中学生课本、课辅以及学生考试、公务员考试题例。曾获“西班牙华语小说奖”、“孙犁文学奖”、“曹雪芹短篇小说奖”以及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文学奖项60多次。曾获“湖北省文联系统十佳青年文艺人才”、“湖北省宣传文化系统‘七个一百’百名文学人才”称号。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冈市文联(黄冈市遗爱湖公园风情街文兴阁)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