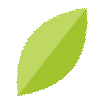左宗棠抬棺出征收复新疆

◎王建生 中国作协会员
参观伊犁将军府,所见的第一个人便是大清帝国的钦差大臣左宗棠。
孤悬边陲的伊犁历来都是外人的觊觎之地,从乾隆爷收复到同治帝丢失,也就十来年功夫。那年是同治十年(1871年),沙俄趁新疆内乱之机,寻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代管代守”,夺走了包括惠远城在内的伊犁九城。明明是抢劫,还硬装好人,说是帮大清守护。据说,强盗们擅自拆毁了惠远城的房屋,将木料运至宁远城修建他们的住宅,如此行为哪有代人守护城池的蛛丝马迹,完全就当成了他自家的财产。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历史的笔锋总是在苦难和辉煌的交织中刻下永恒。新疆人民忘记不了挺身而出,挽狂澜于既倒的民族英雄,忘不了忧国忧民为百姓造福的清官和好人。
伊犁将军府的门前广场上,左宗棠大丈夫身高一丈有余,弹衣正冠,神情矍铄,左手握宝剑,右手持文章,脚下生风云,古铜色的面庞渗透出凛然而不可侵犯的君子之气。墨黑大理石护砌的基座上,铜牌镶嵌,雕刻着左宗棠的手书:“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穷且益坚,心襟浩荡,其人生座右铭昭然天下。
不少的史学家(也包括执政者)潜心研究左宗棠收复新疆经略新疆雄才伟略,他们依据核心史实,综合《左文襄公全集》《清实录》及近代研究成果,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四个维度加以陈述。也有人概括成八个字:“剿抚兼施、兵农并重”。而且,断言这八个字将被后来的实践证明,甚至搁在现代文明的时代也还凑效。
然而,大众百姓不是咬文嚼字的史学家,他们喜爱的左宗棠,是那个抬棺出征以命相拼的左宗棠。老百姓的这种喜爱这种敬仰与生俱来,无须任何教导便先天具有,这大概就是骨子里民族精神,血脉中的民族力量,中华民族其所以能生生不息,全赖这种精神和力量。
晚清的天空是灰暗的,晚清的历史交织着痛苦与悲壮。鸦片战争失败后,大清帝国岌岌可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列强们年年月月都在张牙舞爪地梦想瓜分中国。就新疆而言,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在英俄两国支持下趁新疆民乱入侵,几乎占据天山之南全部和部分天山之北,建立了他们的“哲德沙尔汗国”。1871年,沙俄以“代守”名义强占伊犁九城,声称“待清廷收复乌鲁木齐即归还”(实为永久吞并的借口)。还有,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帝国侵略台湾。由此,清政府高层打起了“海防”与“塞防”之争的口水战。以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方主张放弃塞防,放弃新疆,说“徒收数千里旷地,增千百年漏卮(认为戍边耗资巨大,不如专注海防)”;海南巡抚王文韶等人则主张重视塞防;左宗棠则主张海防与塞防并重,他在《奏复陈新疆情形折》中作了大局分析,说:“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时虞侵轶,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以军机大臣为代表的部分朝廷高官支持左宗棠,赞成“海防”与“塞防”并重,朝廷不仅多了疆土,而且还少了骂名,一桩天大的好事情。但是,此前曾派出两将领出征,结果输的一败涂地。谁能领兵收复?自然是左宗棠。清廷下诏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的身份督办新疆事务,全权节制三军。同时,命一个名叫金顺的将领为帮办军务,择机出塞平叛,收复新疆。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既缺人,又缺武器,更缺少钱和粮,这仗怎么打?不仅要打,而且必须打赢。左宗棠,算是被架到了火上烤。好在,真金不惧烈火,天大的困难也难不倒以命相拼的左宗棠。此处有必要简单地说说左宗棠,他出生于湖南湘阴的私塾先生之家,少年时代穷困潦倒,好在教书先生的父亲早早地把他带进了课堂。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中举人,时年二十整。从此,遍读群书,钻研堪舆和兵法。他得曾国藩赏识并举荐,出仕为官,成为清末湘军首领之一,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中历练立功。
领得清廷收复新疆之命,左宗棠不敢丝毫马虎。他精心筹备,厉兵秣马,办成了几件事情:一是制造武器,创办“兰州制造局”,自产枪炮,改良俄式“劈山炮”;二是屯田积粮,主要是哈密以及巴里坤屯田,据说仅光绪二年就收获粮食5000多石,同时,他还在河西走廊设粮站收粮,用驼队、大车“层层转运”,储备足够的军粮;三是修路植树,东起潼关,穿越河西走廊,至哈密,再分别向南向北延伸,修路栽柳,既防风沙又作为行军路标,后人尊其树为“左公柳”;四是整编军队,裁减冗员,精选六万湘军为主力(一说开往前线的兵力仅为二万人);五是筹借军费,户部下拨200万两(一说慈禧给了五百万两),远不够塞牙缝,左宗棠只能自筹,除典当家产外,还请胡姓红顶商人向外国人借款,凑足2000万两。六是研究战略,提出“缓进急战”“先北后南”方略,战前准备充分,战中速战速决。
此处有诗为证:“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1876年,时年64岁的左宗棠在酒泉(肃州)登坛点将,算是今天的誓师大会吧。左宗堂身后赫然放置一口黑漆杨木棺材。 他对三军疾呼:“西事艰阻,乃我辈马革裹尸之时!老夫此去,不破伊犁终不还!”
会场上,全军将士泣血立誓,悲壮之气直冲霄汉。
帅卒齐心,这样的战争结局肯定是光明的。然而,战争也是残酷的。1876夏,清军按部署在北疆拉开战争序幕,接着便是一仗赶着一仗地打,其中有名的战役是古牧地之战,清军夜袭黄田,切断叛军水源,继而兵不血刃地克复迪化城(乌鲁木齐)。第二年春寒料峭之时,左宗棠的队伍跳到了南疆,借古人之兵法,火攻达坂城,全歼敌守军5000人。左宗棠开批量释放战俘之先河,极大地瓦解敌方军心。于是,连下托克逊和吐鲁番两个重要城池。至此,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连连后撤。清军千里奔袭,给敌人的最后一击,在库尔勒打败驻守于此的阿古柏幼子,并追歼其残部于喀什。阿古柏自知大势已去,服毒自杀。
至1878年初,除沙俄强占的伊犁九城之外,新疆全境光复,用时仅一年半。左宗棠用伤亡3000多人的代价歼敌数万,创下大清朝西域战事的奇迹。
清军收复了乌鲁木齐等城池,而俄方并没有兑现当年的诺言——归还伊犁九城。左宗棠没有贸然出兵,而是胸怀全局,上书朝廷,建议“外交途径和平解决伊犁问题”。随之,左宗棠又着眼边疆长治久安,奏本朝廷“谋划设立新疆省”。
史学家把收复伊犁形象地比喻为虎口夺食,其难度可想而知。
清廷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派出了谈判使者。
光绪五年(1879年),清使者崇厚在俄方的压力下,擅自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仅收回伊犁孤城,反倒还割让土地七万平方公里。
左宗棠闻讯极其震怒,他上书说:“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并提出:“为今之计,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臣虽衰慵无似,敢不勉”。话不多,理至极,字字都在点子上,不仅力主备战再谈,绝不割地求和,而且挺身而出。
第二年(光绪六年),清廷再派曾纪泽(曾国藩之孙)出使沙俄,在圣彼得堡重启谈判 。
也就在这年,68岁的左宗棠二次抬棺出征。他高声唱喝道:“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苦也,老怀益壮。”他说到做到,坐镇哈密,指挥三路大军压境伊犁,摆开了血战到底的阵势。
自古来,“打得赢才谈得拢。”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伊犁条约》等条约一并签订,较之《里瓦几亚条约》,虽仍失去霍尔果斯河以西领土,但争回伊犁九城及特克斯河谷2万平方公里险要之地,算是清朝外交的一次胜利。
三年后(1884年),清廷宣布“新疆行省”设立,治所为乌鲁木齐,首任巡抚刘锦棠(原西征军将领之一)。
依据左宗棠的思路,新疆省作为边疆政府,着眼边疆的长治久安,着手发展农业生产,建设民族团结是新秩序。史料有载,短期内办成了多方面的好事大事: 兴修水利,垦田60万亩 ; 推广棉桑,“教民植棉,利倍于粮” ; 减免赋税、铸造钱币(“光绪银钱”),恢复商贸;开始文教启蒙,据不完全统计,全疆设义塾超过600所,部分地方编制了维语教材;同时,开办起“新疆书局”,刊印典籍,促民族交融……
左宗棠的经略新疆时间虽短,但是,政治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得以完全展示,二百多年后的我们仍有醍醐灌顶的观后感。
左宗棠两次抬棺出征,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民族壮歌,彰显了中华民族“寸土必争”的钢铁意志。抬棺出征不仅是悲壮仪式,更是“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无数事实证明,当国家核心利益受到侵害时,敢于亮剑比权衡利弊更重要,国难当头,每个中华子孙都应该有“死志”的担当。
他所采取的一系列军事、政治方略,大至“先北后南”“缓进急攻”“剿抚并用”的战略战术,小到屯田植柳、买粮运粮等后勤创新之策,环环相扣,行之有效,保障了战争的胜利,说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爱国需要热血,更需要科学”。
收复新疆之后,他推动行省设置,安定了边疆。成功的实践告诉后人:社会治理之路漫长,“长治久安在于人心建设”。
国土之重,重若千钧;守护山河者,山河永铭。
新疆的胡杨林深处,左公柳依然枝干苍劲,人们永远记得左宗棠。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