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流火这词儿绝对是个北方人发明的——李大壮边想边看着自己滴在钢筋上的汗珠刺啦一声化成白汽,仿佛被看不见的灶火燎了一下。他拧着脖颈上湿透的蓝毛巾,嗓子里灌满了滚烫的沙尘:“老张头,咱这汗珠子摔八瓣,怕是能直接和水泥了吧?”
“美得你!”工头老张的笑纹在黝黑脸膛上刻得更深了,像干涸河床的裂痕,“这点儿咸淡,和出来的水泥还不酥成渣儿?”他抹了一把脸,汗水混着灰尘流出一道道灰褐色的印痕,“都给我铆足了劲儿!趁太阳爷打盹,赶紧把这层顶板拿下!”
老张的吆喝在灼烫的空气里劈开一条路,蒸腾的热气扭曲了远处脚手架上工友们奋力劳作的身影,他们犹如一群在巨大熔炉中沉默搏命的蚂蚁,扛着钢筋水泥,正一点点构筑城市看不见的骨骼。
那毒日头悬在当空,把钢铁烤得烫手,李大壮一屁股坐在地上,拧开硕大的军用水壶,水流咕咚咕咚冲进喉咙,却仿佛浇在烧红的铁块上,瞬间又被蒸干了。
他撩起汗衫下摆胡乱抹脸,露出一截晒得脱皮发红的腰背,笑道:“这太阳,可真比翠花那口热锅还烫人!”
王翠花在远处工棚门口择菜,听见了,遥遥甩来一句笑骂:“嫌烫?晚上别进家门啊!”惹得大伙儿哄笑起来,笑声在热浪里挣扎着浮沉片刻,旋即被工地上机器的轰鸣无情吞没。汗水流淌的咸涩中,这点点苦中作乐的微光,是钢筋丛林里珍贵的盐粒。
时光飞逝,季节悄然翻转,日历掀到了腊月深处。凌晨四点,寒风如剔骨尖刀,直往骨头缝里钻。李大壮蜷缩在薄被里,听着外面北风在工棚顶凄厉地打着旋儿,像无数只饥饿的野鬼在哭嚎。他猛地掀开被子坐起,寒气立刻像冰水泼遍全身,牙齿不受控制地咯咯作响。他摸索着套上冰冷的工装棉袄,冰凉的布料贴在皮肤上,激得他一个哆嗦。他重重拍醒了旁边的老张:“老张头,再不起,咱俩可就真成冰雕作品,可以立工地上展览了!”
老张半梦半醒,裹紧被子,声音闷在棉絮里:“展览?那得收门票!五块一位,概不讲价!”他挣扎着坐起来,摸索着套上那件油亮反光的老棉袄,寒意依旧透骨。
工地上,惨白的大灯把冰冷的钢筋骨架照得如同钢铁坟场。李大壮和老张负责绑扎钢筋,戴着厚实的棉线手套,手指却依然冻得像五根毫无知觉的胡萝卜。老张试着弯了弯冻得发木的手指,关节发出细微的“咔嚓”声,他对着僵直的手哈了口白气,那气瞬间凝成霜花,挂在胡茬上:“瞧瞧我这‘冰棍’,现在啃一口,保管嘎嘣脆!”

李大壮咬着牙,把一截冰冷的铁丝在冻得发白的钢筋上费力地拧紧,手指早已失去知觉,仿佛那手已经不是自己的:“可别!留着它们干活吧,等春天来了,还得靠它们给咱翠花挣红烧肉呢!” 寒夜如铁,他们呼出的每一口白气都像微弱的挣扎,很快被无边的冷吞噬,唯有钢筋在手套下传递着刺骨的冰寒。
凌晨收工,李大壮拖着灌了铅似的腿脚回到工棚。王翠花端来一盆热水,盆沿热气袅袅。他脱掉浸满寒气的鞋袜,把冻得发青、几乎失去知觉的双脚猛地沉入热水里,那针刺般的麻痛瞬间从脚底直冲头顶,他“嘶”地倒抽一口冷气,整个人都激灵了一下,片刻后才缓缓吐出一口浊气,仿佛冻僵的魂儿终于被烫回了躯壳。
窗外,一弯寒月清冷地悬在墨蓝天幕上,工地归于沉寂,只有远处未熄的灯火勾勒着庞大建筑的轮廓。王翠花坐在床沿,借着昏黄的灯光,轻轻抚摸着儿子寄来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纸页在灯下泛着柔和的微光。她的目光长久地停驻在那几行字上,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寒夜的寂静:“大壮,再熬熬……等娃毕业了……”
李大壮仰靠在床头,热水带来的暖意正一丝丝从脚底向上蔓延,驱散着深入骨髓的寒气。他闭着眼,月光勾勒着他疲惫而坚毅的侧脸轮廓。半晌,他含糊地应了一声,那声音低沉而笃定,带着白日里指挥绑扎钢筋时的余韵:
“嗯,等路修好了……”
寒月无声,静静地照着这间简陋的工棚,也照着外面那庞大、沉默、正在拔地而起的骨架——那由无数汗珠与冰霜反复浸染的筋骨,正默默托起人间滚烫的期望。夜风掠过空旷的工地,仿佛在低语:每一粒嵌入钢筋的冰晶,都暗含着一个春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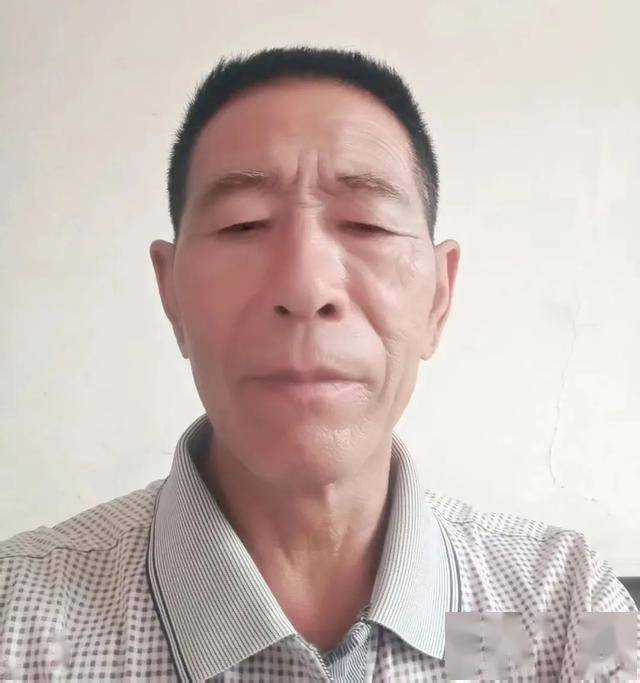
作者简介:贺占武,男,汉族,笔名绿原,河南洛宁人,热爱文学,一个不起眼的文学爱好者。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