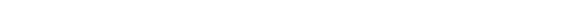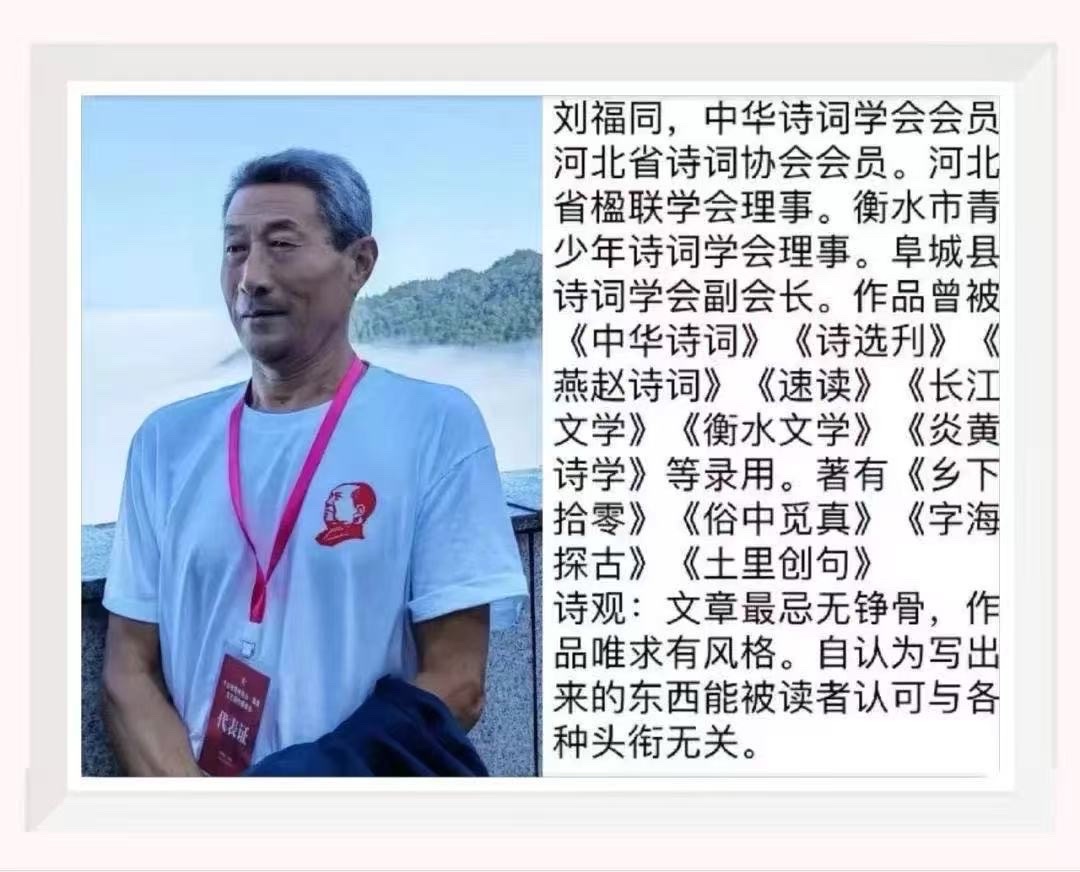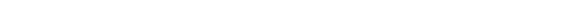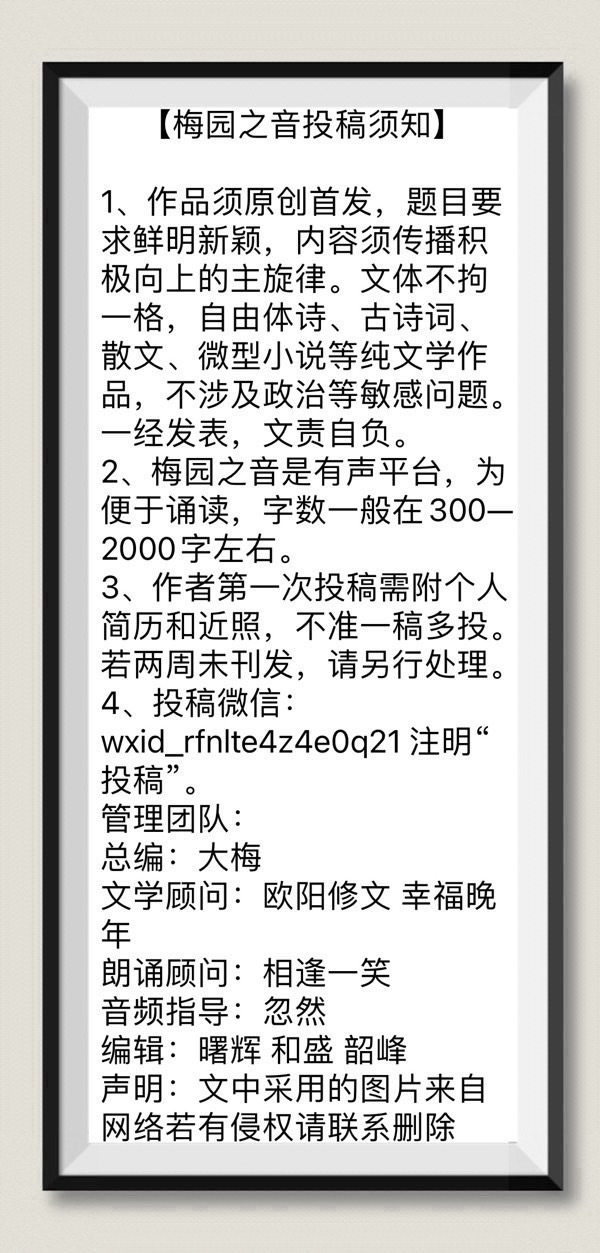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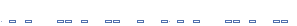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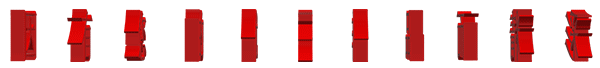
《修 河》
作者:刘福同
朗诵:夏天

“一辆花车一对筐,两把铁锨放中央。谷草苫子铺盖卷,酸甜苦辣里头装”这是当年对修河民工队伍的精确描述。
我修过河,时间为1980年春季,工地位于㵚东排河衡水段,是国家根治海河这个伟大系统工程的组成部分。
修河的民工队伍庞大,实行的是半军事化管理。县里的组织叫根治海河指挥部,公社这一级设连,以连为单位设伙房,管着近二百余人的吃饭。连以下设班,每个班的人数在四十上下。以班为单位住一个工棚,班长由连部临时任命。这人选嘛,大多找得是那些“河油子”。因为这类人常年参与修河,熟悉并掌握工程期间的所有程序与环节,揣摸得透领导们的意图和民工们的心思。当然了,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技巧,是领导和民工之间不可或缺的纽带。班长不脱产,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是当班长的一大特色,他们与民工唯一不同的就是时不时地被连部召去开个会,中间可以有这么个把小时或更长点的时间不干活,算是享受到了班长的待遇了。

“亲爹后娘,送我到河上”。是修河民工们时常挂在嘴边的自嘲语,民工一进工地便再无闲日。
工地上的活分为三种,推车装车和拉车。哦,至于那些测量的,举杆的,开机器抽水的,伙房里做饭的虽然也是民工,但人数不多而且这种差事一般人也徬不上边,咱.就不把他们计算进去了啊!
独轮花车左右两个柳条筐,上层土一筐能装二百斤。到了下层连泥带水的就得到二百五十斤左右,一车的重量就是四百到五百斤的样子。呵呵,吓着了吧!但这对于那些一年两季转战于各个工地上的民工来说已不算什么啦。你看他大襻往肩上一搭,两头襻扣往车把上一套,一哈腰这车子便呈现出起步的状态了。再看前头拉车的,半米长的铁钩子往车上一挂,回头一躬身,随着一声响亮的号子响起,这座小山便缓缓的向前走去。怎么样?这配合默契的动作是不是也值得伸指叫绝?
装车的为左右两人,各自负责自己那边的筐。用的工具叫捅子锨,也叫瓦楞锨,光锨板就约半米长。一锨下去能切下近三十斤泥土来并行云流水地装到筐里去,中间没有缓冲的机会。双方要保持进度一致,否则车子便失去平衡。装满载的车子刚走,另一辆空车便不失时机地放到你的面前。这空间运转的计算精确度直让我这当年的数学尖子满脸生愧。

新手入场,班长便让你在这三个活中自选。推不了车你就去装车,装车也干不了就只能去拉车了。呵呵,你别以为拉车就算饶了你了,“一根大襻一根绳,勒到肉里别喊疼!”两趟下来保你呲牙咧嘴叫苦不迭。
关于吃饭。一日三餐管饱,早饭窝头咸菜玉米粥。午饭是馒头炖菜,菜里有粉条,偶见几片白肉膘。哦,这所谓的馒头我得多说上几句,因为这种馒头你不光没吃过,没见过,可能你都没听说过。一斤面蒸一个馒头是工地厨师们的一大创举,民工们给这馒头起的名字叫“大颤”。这大颤厨师们做着省劲,开饭时分着省事,民工们拿着方便,可谓一举三得。
每人一个大颤是定量配给的,饭量大的可通过班长申请加“蛋”,这个蛋就是二两一个的小馒头。晚饭继续着窝头和菜汤的搭配。
我的饭量不大,中午的大颤能节余下二两的样子,给自己的晚饭增加了细粮。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

每周一顿包子算是改善生活了。馅是白菜加肉,肉是大片的白肉膘,菜上的蚜虫依稀可见,民工们将其称为高蛋白,吃得津津有味。
厨师们剁菜的方式说来你也没见过。白菜剝去外层老帮往筐里一扔,七八棵为一组,手起刀落一番手腕力量的输出便成了馅。至于菜馅的大小不均和肉片的厚薄不勻都不是你挑毛病的理由,爱吃不吃。哦,差点忘了告诉你,这包子皮是二两面一个,够个吧!
关于住,以班为单位几十号人住在一个工棚里,说是有助于管理。中间60公分左右的过道,两侧的人头顶头的睡。床?把你捎来的草苫子往地上一铺便是。
晚饭后,工棚里便热闹了起来。侃大山的,讲笑话的,发牢骚的,说荤段子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好像一天的劳累与这些人无关似地。热闹过后,困意袭来,工棚里进入短暂的安静期。随之而来的便是从小到大的呼噜声,咬牙声,梦呓声,混合着脚臭,汗臭,腋臭和屁臭充斥于工棚的每一个角落。

条件的艰苦和劳动强度的增大,使人们开始寻找偷懒耍滑的机会和办法。蹲上十几分钟的茅坑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了,被人嘲笑一番反而丢了面子。人们早已不再玩这种套路了。装病,不知是谁发明的又一个无奈之招。按规定,只要能拿到随队医生的条子便可以堂而皇之地躺上两天,还可能吃上碗飘着油花蛋花的病号面。
随队医生常和民工们打交道,深知他们的那点小心思,一般人很难在他面前蒙混过关,我们班的二蛋也因此闹出了个天大的笑话,被人津津乐道了好多年。
二蛋十八岁,是个孤儿。生产队里之所以派他来修河,一是考虑在工地能吃个现成的饭,二是队里还给他记着最高的工分,可谓两全其美,谁知这孩子两天没干下来就哭着闹着要回家。这时有人发坏撺掇二蛋装病去开条子,并让其捂着肚子说得了卵巢炎。这孩子也不知卵巢炎是什么病,心想只要能歇两天管它什么炎呢。于是他便找到了随队医生。

傍晚收工后,连部通知全连民工现场开会。会上,连长铁青着脸指名道姓地把二蛋骂了个狗血喷头。
班长官不大,但肩上的担子不轻。催大家起床,解决民工之间的小矛盾以及处理工地上的各种纠纷让这个最小的领导疲于应付,也因此成了众矢之的。
我的工棚是二班,班里有个民工叫老黄,说得一口流利的西河大鼓,这得益于其父亲的言传身教。只可惜这满身的艺术一直没派上用场,以至于年年混迹于这泥土之间。老黄经常拿班长取笑,班长也把他当作戏弄的对象,以此逗乐解闷而已。
这天晚饭后人们觉得无聊,一直起哄让老黄来段西河大鼓娱乐一下。这老黄瞅了瞅身边的班长眼珠一转便应了下来。破脸盆扣过来当鼓,折根树枝便是鼓槌,鸳鸯板那是随身带着的。至于段子嘛,张口就来:闲着这没有事我到东庄,在东庄碰见了一个同行。

我见同行微微笑,同行见我眼泪汪汪。
我问同行有什么冤事,他言说,俺娶了个媳妇爱尿炕。
一更天尿了红绫被,二更天尿了新衣裳。
三更天尿湿了绣花鞋,四更天尿透了象牙床。
五更鸡叫天大亮,屋里可成了太平洋。
一伙子渔翁来把鱼打,大船小船尽显张扬。
一个王八跑得快,七网八网也没有扣上。
你要问这王八那里去,他来到二班当上了班长。
鼓掌声,欢呼声,口哨声响成一片,班长手里举着棍子嘴里骂着娘围着工棚把老黄追了三圈。
历史眨了下眼,时光已去44年。

这天,我乘着秋日的暖阳登上了滏东排河的大堤,望着脚下缓缓流淌的河水,万千滋味涌上心头。我似乎看见了西坡沿下还留有我车轮碾过的沟,我似乎看见了堤边上还有我布鞋踩下的印。堤下不远处的那块棉田应是我当年打饭的伙房,旁边那棵老榆树下应是放我被窝卷的地方。
哦,我记起了为我装车的黑牛,为我拉车的赵马。我记起了伙房里给我多盛了两块肉的王金贵,我记起了偷吃我一个包子的孙大龙。还有那一脸憨厚的魏全和一脸狡黠的老黄。这一个个鲜活的面孔轮番跳跃在我的面前挥之不去。
对岸,那苍了皮的玉米,红了脸的高粱摇晃着身躯似在向我诉说着什么。我张了张嘴,喊出来的竟然是:我的民工兄弟,你在哪里?
泪,夺眶而出,随之被风裹挟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