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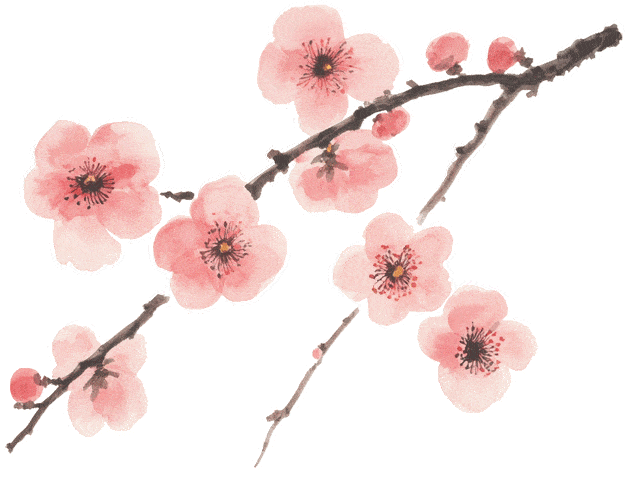
鄂东名家新奉献

□ 郑能新 中国作协会员
一
启明星还挂在地坪河的天幕上,万窑匠已经赤着脚在泥池里踩泥了。
两丈见方的泥池子咕嘟咕嘟冒着泡,老黄牛甩着尾巴在不远处的竹林边嚼草,蹄子把地上的鹅卵石踢得叮当响。
万窑匠左脚掌外侧的厚茧在泥浆里若隐若现,这是五十年如一日斜切踩泥留下的印记。
“国儿,把筛子递过来!”万窑匠抹了把汗,从泥池里走出来,灰白胡子沾着泥星子,“加土!这窑泥比粮食还金贵,得筛得比面粉还细嘞。”徒弟张其国踩着露水跑来,裤腿卷到膝盖,露出黑黢黢的小腿肚子。
褐红色泥土在八十目竹筛上簌簌流泻,细得像三月里的春雨。 老窑工的手突然顿在泥池东北角,这里的淤泥泛着暗红色。
五十年前那个暴雨夜,他亲手埋下炸窑裂开的三十六只婚宴酒瓮。新媳妇的哭喊声仿佛还在耳畔:“我爹说炸窑不吉利,这婚……”他甩甩头,挖起团泥摔在木泥板上,“啪”地溅起不少泥点子。
“师傅,这泥成了?”徒弟国儿凑过来。
“你摸摸,”万窑匠把泥团掰开,“得跟猪板油似的柔润,搓起来滋滋响又没疙瘩。”
阳光穿过他指缝,照见泥里闪烁的云母碎,像撒了把银粉。
二
幽暗的泥房里,天窗漏下的光柱中有浮尘在起舞。万窑匠眯起眼,透过那浮尘,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多年前。那时,同样是这样的泥房,他的师傅也是在此,手把手教他如何感受泥性。师傅耐心地讲解着,眼神里满是对这门手艺的热爱与执着。他说,泥就如同有生命一般,每一块都有独特的脾性,只有真正用心去感受,才能让它们在手中变成精美的器物。
如今,自己也成了师傅,看到徒弟国儿,就如同看到当年的自己。他希望能将这门手艺毫无保留地传承下去,让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精美瓷器,继续在世间绽放独特的魅力。此刻,身旁的国儿,正好奇地盯着那光柱,眼中满是对这门手艺的新奇与渴望。万窑匠深吸一口气,空气中弥漫着泥土特有的气息,他拿起一块泥,在手中缓缓揉搓,似乎要将一生的技艺都融入这泥团之中。
万窑匠盘腿坐在辘轳车前,脚趾勾着松木踏板一蹬,转盘便呜呜唱起祖传的歌谣。陶泥在他掌心往上窜,转眼就长成个浑圆的坛肚。
“拉坯要像哄娃儿睡觉,”他沙哑的嗓音混在转轴声里,“手往上提,得比大姑娘绣花还轻巧。”
国儿盯着师傅的手,那双手的裂纹里嵌着洗不净的陶土,指甲盖也有些残缺不全,却在触到湿泥的瞬间变得比绸缎还柔软。
忽然有燕子从梁上掠过,翅膀扫落几缕积尘。万窑匠眼皮都没抬,拇指在坛口轻轻一抿,泥坯立刻收成朵含苞的莲花。
“师傅,您这‘观音手’绝了!”国儿看得眼睛都直了。
“狗屁的绝活,”老窑工往泥坯上弹了点水,“当年你师爹拿着竹篾条,我手上没少挨抽。”
泥坯渐次摆满木架,从拳头大的酒盅到半人高的米缸,个个泛着湿润的幽光。万窑匠眯眼打量这些泥胎,恍惚看见它们盛过新麦酿的头道酒,装过新媳妇回门的红鸡蛋,在无数个晨昏里吞吐着地坪河的烟火气。
三
装窑的那一天,周围十里八乡的狗都跟随人们一起向窑场疯跑。土窑在晨光的映照下,像是等待点火的卫星发射场,人们围在四周,脸上满是期待。
万窑匠往窑门插上三根紫香,青烟刚袅起来,就被河风扯成碎片。
“东青龙,西白虎,窑神爷爷来护佑!”他吼完老话,羊皮袄往后一甩,“上轿喽——”二十几个后生扛着陶坯列队,打头的汉子捧着只描金喜字罐,正是村长家闺女腊月出门子要用的嫁妆。
“万师傅,这对喜罐可得摆在窑心啊!”村长媳妇攥着红布条直念叨。
“晓得了晓得了,”万窑匠往窑膛深处指,“火路从坎位进,离位出,保准给您烧出个金镶玉。”转身却往窑眼处塞了三个粗陶碗,碗底还沾着去年祭窑的香灰。
国儿看得真切:“师傅,这碗……”
“你师爹那会儿就有的规矩,”万窑匠往窑砖上磕烟袋,“三阳开泰镇窑眼,比啥温度计都灵光。”
帮工们一趟趟将泥坯稳稳地搬进窑膛,摆放得整整齐齐。万窑匠在一旁指挥着,眼神专注而严肃,容不得半点差错。孩子们则在人群中嬉笑打闹,兴奋地说着一些与之有关或无关的话题,不过,他们的兴奋点主要是热闹的场面,人来疯才是小孩子的天性。
等到泥坯全部装完,窑口被严严实实地封上,就只等那关键的点火时刻,众人都知道,这一把火,将赋予这些泥坯全新的生命,开启它们从泥土到陶器的神奇蜕变之旅。
四
暮色刚刚染红西天,窑顶的烟囱吐出第一缕青烟。
万窑匠往手心啐了口唾沫,五尺长的铁火叉在地上拖出火星子。“点火!”松明子扔进窑膛的瞬间,火龙“轰”地蹿起来,映得地坪河半边水都泛了红。
“柞木硬,桦木旺,栗木烧出琉璃光……”老窑工围着窑膛打转,火叉挑起柴堆的姿势就像是在给火龙梳理鳞片。
到后半夜,东南天忽地滚过闷雷,国儿抬头看天:“师傅,怕是要下雨咧。”
万窑匠抄起竹笠就往窑顶爬,六十岁的人比猴子还利索。
冰雹似的雨点砸下来时,他正趴在窑顶糊黄泥。“老天爷不帮忙!”雨水顺着他的蓑衣往下淌,“快搬棉被来!”众人顶着棉被冲进雨幕,却见老窑工弓着背伏在窑顶,像只护崽的老龟。火舌从裂缝里窜出来,在他后背的棉被上咬出焦黑的洞。“刺啦”一声,浸透雨水的棉被冒出白汽,混着皮肉烧焦的糊味在雨里弥散。
五
第七天开窑时,霜花在巴茅杆上结出银穗子。
万窑匠后背裹着草药倚在窑门边,看着后生们卸窑的眼发飘腿打颤。
当晨光照进窑膛的刹那,满窑陶器泛着的不是寻常的青灰色,而是透着虹彩的琉璃光。
“胭脂红!”人群炸开了锅。
那三只镇窑的粗陶碗,此刻像浸了晚霞似的红得透亮。村长的两只喜字罐更是流光溢彩,金粉在釉面下如水纹荡漾。万窑匠却盯着窑眼处那只龙凤呈祥罐,罐身火痕蜿蜒如凤尾,正是那夜棉被烧穿时,火龙在他背上烙下的印记。
县文化馆负责非遗的小陈激动得有些结巴了:“万、万老,这是现代柴烧的窑变奇迹啊!”
老窑工没搭话,用缠着纱布的手摩挲罐身。手上传来的温热让他想起师父临终的话:“记住咯,我们烧的不是泥巴,是火魂。”
六
腊月里,村长的闺女出门子,两只喜字罐排在火盆两边。新娘子跨火盆时,万窑匠悄悄往盆里扔了把窑灰。火苗“噗”地窜起尺把高,映得新娘子头上的银饰灿若桃花。
众人都被这突然窜起的火苗吓了一跳,随即爆发出一阵惊叹。新娘子微微一颤,却很快稳住身形,迈着轻盈的步伐跨过火盆。万窑匠看着新娘子的身影,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村里的老人们围了过来,纷纷夸赞这窑灰带来的好兆头。这时,不知谁喊了一句:“万师傅,再给大伙讲讲烧窑的门道呗!”众人的目光一下子都聚焦在万窑匠身上,万窑匠清了清嗓子,开始讲述起窑火与土坯之间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在这腊月的喜庆氛围里,窑匠的声音仿佛带着岁月的温度,将古老的窑文化缓缓道来。
地坪河的窑火就这样生生不息,它总在每一个晨曦与日暮里,映照着村庄的变迁,也温暖着村民们的心。万窑匠的故事,如同窑中跳跃的火苗,点燃了大家对传统窑艺的热情。
时间一晃又到了冬末,国儿发现师傅最近总在泥塘转悠,有时蹲着扒拉碎陶片。国儿满心疑惑,却又不敢贸然打扰师傅。他悄悄跟在万窑匠身后,观察着师傅的一举一动。只见万窑匠时而捡起一块碎陶片,对着阳光仔细端详,时而又在泥塘边比划着什么。国儿忍不住走上前去,轻声问道:“师傅,您这是在做什么呀?”万窑匠抬起头,目光深邃地看着远方,缓缓说道:“国儿啊,这儿的陶片,都是先辈们留下的宝贝,我在琢磨着,能不能从它们身上,寻回一些失传的烧制技法。”国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内心对师傅的敬佩又增添了几分。
立春那天,万窑匠把徒弟领到西坡的老窑遗址前,指着遍地青砖说:“等我这把老骨头烧不动了,你就在这儿起新窑。”
河风掠过废墟上的狗尾巴草,把老窑工的话揉碎了撒进春雨里。对岸新修的公路传来一阵阵的汽笛声,而地坪河的窑火,或许正在某个少年心里悄然苏醒……

作者简介:郑能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为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湖北省作协散文专委会副主任。已发表、出版文学作品300余万字;有40多篇入选《小说选刊》《读者》《新华文摘》《短篇小说选刊》等国家级选刊、选本;有多篇作品被选入大、中学生课本、课辅以及学生考试、公务员考试题例。曾获“西班牙华语小说奖”、“孙犁文学奖”、“曹雪芹短篇小说奖”以及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文学奖项60多次。
作者单位:湖北省黄冈市文联(黄冈市遗爱湖公园风情街文兴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