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中国小说的起源发生,传统多认为来自于稗官,这一认识主要来自于《汉书·艺文志》:“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颜师古注:“稗官,小官。如淳曰:‘细米为稗,街谈巷説,其细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闾巷风俗,故立稗官使称说之。’”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然文辞之有谐隐,譬九流之有小说。盖稗官所采,以广视听。”
何谓“稗官”?有解释为小官,小官者何官?却并不能落在实处,除此记载之外,亦并无其它史料之佐证。班固作为东汉明帝时代的大儒,其《艺文志》对于上古之文学文艺多有编造之说,如诗三百之“采诗”说即从此公处所由来,而其所编造之渊薮,又多由西汉末期之刘向、刘歆而来,刘向父子为王莽篡权而作舆论准备,故重在强调文化之民间创造说,以淡化皇权之天授。班固承接此说,以与儒家“民本”之说吻合。
小说起源于稗官这一认识,与其说主要来自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毋宁说最终确认于鲁迅。而鲁迅之说,主要阐述在《中国小说史略》,故理应从鲁迅之论谈起,其《中国小说史略》开篇即言:
小说之名,昔者见于庄周之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庄子·外物》),案其实际,乃谓琐屑之言,非道术之所在,与后来所谓小说者固不同。……而征之史:源自来论断艺文,本亦史官之职也。
鲁迅开篇之论,虽然征引庄周在前,但最后归结于“本亦史官之职”,这是较为贴近历史的真实。但随后的引述,却从“稗官”之说,引向班固《汉书·艺文志》“小说者,街谈巷语之说也”,并最终得出了小说起源于“民间”之说,不知其所据为何?鲁迅说:“稗官者,职为采集而非创作,‘街谈巷语’盖出于民间,固非一谁某之所独造也,探其根本,则亦犹他民族而言,在于神话与传说。”则小说起源于稗官之说,也就似乎成为定论。
班固所谓的“小说”是稗官所收集的街谈巷语,先不说是否有这种“稗官”的存在真实性,即便有,也如余嘉锡所考证,亦系指收集庶人之言传达给天子的“士”(参见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可以视为宫廷文化的外延文化;同时,探索中国小说的源流发展,也就不能单纯从狭义的小说角度阐释,而是需要将戏曲的源头并入小说而为一体,不仅如此,诗词散文中的相关因素,音乐史表演史的相关内容,都应该融入汇通而为小说的共同源头。
按照传统说法,一代有一代的文学,先秦诗骚、两汉辞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就给读者戏曲小说最晚兴起的直观感受,但如果深入思考小说戏曲的起源,却是与中国的诗歌同本同源、同源共生的。总体而言,中国的戏曲早于小说,诗文早于戏曲,宫廷文化是中国文学产生的温床。可以分列以下几个方面:
1、小说戏曲的最早源头同样是在《诗经》:如《大雅·凫鹥》以活人扮演祖先,即“公尸”的形式来进行祭祀活动,可以视为最早的戏曲表演的雏形;《大雅·生民》首先出现神话写作,对有周先祖后裔的诞生进行了神话描写,可谓是最早的小说萌芽。这种神话想象,在战国后期得到发展,从而出现《山海经》这一神话地理历史的作品,成为以后志怪小说的源头;诗三百进入到平王东迁的礼崩乐坏之后,郑卫之音出现大量好色之作,这些作品伴随新兴的房中乐,成为在诸侯中表演的节目,其中叙事长诗《氓》,虽非色情淫靡之作,但却突破了国风以来即兴的比兴写作方式,成为一种创作型叙事作品,富有戏剧情节的演出脚本。
2、《楚辞》:如果说,《诗三百》是礼乐制度下的产物,其作品的产生与传播都是在两周王庭诸侯,《楚辞》则为南方楚国地区的产物,屈原《九歌》应该是在楚地民风乐舞表演基础之上的产物,可以视为中国戏曲产生的源头之一。
3、《左传》:《左传》为《春秋》的文学化、小说化阐释,可以视为中国史传文学的最早源头,直接影响了战国汉初时代文学的演变,与《战国策》《史记》前后呼应共同构建了史传文学,从而直接影响了中国小说的发展,可以视为后来《三国演义》的源头。这种史传文学,可以界说为是以文学的想象、虚构的情节、细节与真实的历史结合,来写作人物传记或是历史事件。
4、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发展到战国中期之后,以《孟子》《庄子》为代表,其中的寓言故事,以“无端崖之辞”,构建了后来小说发展的平台。
5、宋元话本与金元戏曲:明清小说的兴起,与宋元话本和金元戏曲的兴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明清小说和明清戏曲,是建立在宋元市井文化兴起基础之上,宋元小说与杂剧的产生,都是这一新兴市井文化的产物。但由此向前追溯,宋元话本与戏曲的兴盛,还是中国诗词史、中国音乐史、中国表演史自西周制礼作乐以来演变的结果。大体而言,中国诗词、音乐、表演的历史,都在中唐发生质变,由此前的宫廷文化,渐次下移进入到市井文化之中,其中带有表演性质的词乐歌舞,经历士大夫、州刺史的家宴歌舞文化,渐次进入到勾栏瓦舍的市井文化,成为具有商业性质的说唱表演文化,从而成为宋元话本小说与戏曲产生孕育兴起的摇篮。
纵观中国小说史,大约经历了几个历程:先秦到六朝,可以称之为宫廷贵族小说阶段,中唐传奇的发生,主要与新兴的科举制度有关,由此产生士大夫传奇小说;宋代新兴市民阶层兴起,遂产生市井文化白话小说。到明清时代,则市井文化小说与士大夫文人小说并进,遂有长篇章回小说的兴起。
中国小说戏曲的起源发生,就文学体裁而言,首先萌生于诗体文学——在诗三百的演变历程中,经历了《周颂》的祭祀散文体之后,进入到《大雅》对有周历史的颂诗阶段,其中多有神话描写,可以视为中国叙事文学的最早萌芽;随后,在小雅和风诗写作中,又不断增补细节描写,这些都为后来的史传文学做出了写作方法的准备。随后,“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之后,《春秋左氏传》的出现,标志了纪传体文学在阶段上取代了诗体文学,叙事文学与抒情文学在战国时代并驾齐驱,孟子、庄子、屈子的作品以及《山海经》等书之中,都有大量的寓言和神话故事。
这个阶段,不仅仅是叙事文学的兴盛,而且是文学精神、想象、虚构、夸饰、神话等走向极致的时代。这种时代思潮,一直延续到汉武独尊儒术,司马迁的《史记》,名为史书,实则文学,乃“无韵之离骚”,开辟了中国史学的特殊体例,即文史一体化的史传传统。这一史传传统,正是后来中国小说以及戏曲之来源、发源、滥觞。
司马迁之后,正是“独尊儒术”发端的时代,中国从此走向了儒家一统的思想禁锢,司马迁开创的史传文学传统,其精神从《汉书》之后的历代史书写作形式中不得不消泯,虽仍旧以人物为中心带动史实,却抽去了文学的、情节的、细节的、描写的内涵,而仅剩下政治的、儒学的人生简历。但司马迁史传的写作方式,并未消失,而是分流到文学写作之中。
由《左传》发端而到《史记》大成的这一文学史传传统,从史学领域分离开来,散见于随后的诗歌、散文之中,并成为中国小说独立于诗文体裁的直接源头。正由于这种史传传统,中国早期的小说作品多以“传”为书名,如初唐的《补江总白猿传》,中唐的《莺莺传》《霍小玉传》等。到了明清时代,长篇白话小说兴起,仍有《水浒传》等,《金瓶梅》最早的书名为《金瓶梅传》,透露了书中人物原为实录的写作背景,正式出版的时方才落实而为《金瓶梅》,以后由冯梦龙改编为《金瓶梅词话》,从而宣告了脱离史传文学母体的新历程;《红楼梦》原名《石头记》《金陵十二钗》,后者其实就是“十二钗传”的意思,不仅显示了中国小说从史传文学脱胎而来的影响痕迹,而且,暗示了此书所写并非男性人物传记,而是十二钗代表的女性传记,更深一步则暗示了此书为女性所写的作者背景。凡此种种,都显示出“史传”文学对唐传奇特别是明清小说的强大影响力,简单而言,中国小说的直接源头,就是史传文学。
小说与戏曲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从小说史源流关系的角度来看,一部中国戏曲史就是一部小说史故事素材的主要来源地;一部戏曲文本及表演史的演变,同时也是中国小说史写作经验升华的演变史。
如果将中国的叙事文学,小说戏曲视为一体的文学史现象,它们同本共源都产生于先秦宫廷文化之中。其中的戏剧演出系统,主要来自于宫廷演出的俳优文化,在宫廷文化漫长岁月的演变之中,渐次走向市井,宫廷俳优演出变成市井伶工;作为叙事故事的文字脚本,则来源于史传文化,史官同样属于宫廷文化的一部分。戏曲表演的音乐部分,主要来自于:歌诗——曲词——戏曲,其音乐的品类主要经历:先秦雅颂音乐——国风房中乐——两汉食举乐——曹魏清商乐——(北朝胡乐——隋代初唐燕乐)——盛唐清乐法曲——唐五代词乐——金元诸宫调——元曲的演变历程。
在以上的阐述之后,重回从班固到鲁迅所谓的小说起源“稗官”说问题:就学术方法而言,探讨中国小说之起源发生,应从中国文学之文本原典出发,而不能偏信这种所谓的记载之说。小说与诗歌之间,就中国文学的实际而言,两者皆主要为贵族的、士大夫的、思想家的、精英文化的产物,除去中唐宋元的话本小说,其余基本都是所谓的“文人小说”,或说士人小说、士商小说。
以上所说“主要”,指的是本质上的、主要的历史阶段,其中唐宋时代市井通俗文化的产物,话本小说兴起,则是市井文化的口头小说作品的标志,到《三国演义》的完成,则标志了这一历史进程的终结。李贽作为时代思想巨人全力参与小说写作,其作品进入“四大奇书”之中,标志了市井话本小说的衰落和小说写作重回精英文化的历史范畴之中。
在将中国戏曲起源演变史历程与小说演变整合而一的基础之上,所谓的稗官,很有可能是宫廷中的俳优文化,如汉武时期的东方朔就是这种典型的为帝王排忧解闷的早期宫廷演员。到曹魏时代各种胡乐胡舞进入中原北方地区,歌舞表演与俳优小说相互影响激发滋生,从而成为后来戏曲小说的源头。曹植兴趣广泛,《魏略》记载曹植会见邯郸淳:“科头拍袒,胡舞五锥锻,跳丸击剑,诵俳优小说数千言。”被邯郸淳称之为“天人”,从这段记载来看,“俳优小说”是一种技艺,大体属于“百戏”的范围,戏谑调侃之类,为后来“说话”技艺的早期形态之一。
只不过,俳优演出原本专属于宫廷文化之一种,指古代以乐舞谐戏为业的艺人。一般都将俳优解读为“表演者之称呼,古代称呼以歌舞谐戏表演为职业之艺人为俳优”。这种解释固然不错,但却并不准确,俳优最早见于《韩非子·难三》:“俳优侏儒,固人主之所与燕也。”所谓俳优与侏儒,并非宋元市井演出的演员,而是专指“人主之所与燕也”,是人主,也就是帝王宴饮中的表演者,提供给宫廷的娱乐文化品种。因此,俳优文化也就是中国小说与戏曲共同的最早的文化形式,这就重回了本书的主要观点:中国小说戏曲与最早的诗书文化,同样都起源于宫廷文化。
综上所述,中国小说虽然具有通俗文化的特性,但却并非来自于民间,“道听途说者”之流仅仅是小说的素材,而非作为文学的小说。小说文学真正进入到市井文化,就到了宋元话本小说阶段,此与宋代都市文化的繁荣,市井文化、说唱文艺的兴起有直接的关系。由于作为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才开始了以白话取代文言的历程,宋代话本小说在其中起到了这一变革的枢纽位置,从而成为明代四大传奇与《红楼梦》的滥觞。
《史记》首先是史书,为“史家之绝唱”,中国纪传体通史之祖;其次是文学,为“无韵之离骚”,为中国散文史之重镇;但其对中国文学史影响至深者,乃为小说。《史记》当然本身不是小说,但却深刻影响了后来中国小说史的起源发生演变,堪称中国小说写作方式及小说理念之渊薮。
换言之,中国小说史中的小说理念,万变不离其宗者,即为小说的史传基因,从根本上决定了小说的两大基本特征:其一,以人物命运、人物性格为中心而非以事件始末为中心,故事及其情节服务于人物命运,人物命运决定于人物性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小说的史传体式以及真实社会属性的本质特征;其次,在真实史传文学的根基之上,放飞缪斯想象的翅膀,任由小说中人物的性格而发展演绎其自身的必然命运,庄子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成为中国小说演变的第二大特征。
以长篇章回小说为例,《三国演义》《水浒传》都直接来源于史传文学,只不过水浒演绎的成分更多一些;《西游记》看似远离史传文学,但其本质精神却是王阳明心学的小说化表达;《金瓶梅》原名《金瓶梅传》,更体现出史传文学的生命基因;《红楼梦》曾名《金陵十二钗》,其创作的本意,也正是为天下女性立传。所谓“千红一哭,万艳同悲”。
《史记》当然不是最早具备此两大特征因素,先秦特别是进入到战国时代的《左传》《战国策》《庄子》《山海经》,皆可谓中国小说的直接源头,但战国时代的诸多小说源头,皆可谓《史记》产生之前的涓涓细流,到司马迁手中,方才完成了将战国时代的诸多分流合并而为江河。因此,《史记》固然是中国散文史之重镇,但却更是中国小说史之源头。
以上从思想史、文化史的传承角度,论述了司马迁小说化写作的源流关系,以下从其家族个人的角度,来看司马迁这种富于文学激情式的写作方式的源头。
司马迁,字子长,陕西韩城人。出身于世代史官之家,父司马谈为太史令。司马迁说自己曾“耕牧河山之阳”,这不过是说他少年时代是在京城之外的乡间生活,司马迁五岁左右(约公元前140年)时,父亲接受了太史令的职务,在此职位上约三十年。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于太史公这一职业,由此拥有的便利条件、文化氛围、兴趣志向等,无不深深影响了司马迁。
司马谈所生活的时代,主要还是文景时代及汉武初期,黄老思想是当时最流行的哲学,也是与“休养生息”最为相宜的哲学。所谓“黄老”,黄指战国以来传说中的黄帝,老指老子。他们以《老子》为依据,认为虚无的“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无不为”,亦即司马迁所说的“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一切皆顺其自然,适应时势。司马谈的哲学思想,亦受“黄老”影响,曾著《论六家之要旨》,对儒、墨、名、法、阴阳诸家皆有所批判,独对道家全力赞扬。这一点,对其子司马迁的思想及人生命运产生深刻影响。
这种影响,一是表现在贯穿其著作中的道家思想意识,另一方面,司马迁不但继承了由文景时代盛行的黄老哲学,同时,几乎是先天地继承了老庄时代“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的虚构故事的写作意识。
司马迁在二十岁之时,访汩水,“窥九疑,浮于沅、湘”。(舜南巡时葬于九嶷山,又称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县境。)“南登庐出”考察“禹疏九江”,在孔里参观孔庙及其车服、礼器;考察本朝刚刚发生那一幕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中的英雄豪杰,在淮阴韩母墓前凭吊,听父老讲述胯夫韩信和漂母救韩信的故事。司马迁在考察中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酝酿了文学创作的感受。
元封元年(公元前110),武帝欲举行盛大的封禅大典。司马谈随行至洛阳,因病滞留。司马迁正从西南出使赶回至洛阳,见到了因不能参加盛典而病情更加严重的父亲。司马谈死前泪眼执子手,以让子承父志完成《史记》而重托,司马迁垂头哭着,接受了父亲的遗命:“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这种生命式的激情写作原动力以及对历史遗迹的踏勘访谈,无疑为这种史学工作加入了浓郁的情感血液。
父亲去世后的第三年(公元前108),司马迁作了太史令。在司马迁从事《史记》著书更作后的第七年,发生了李陵事件。李陵为李广孙子,当时兵败而被迫投降匈奴,司马迁为之情而触怒武帝,审讯得“诬上”的罪名。根据当时律条,或以钱可以赎罪,或是受“腐刑”。以钱赎需50万钱。司马迁为了完成他父亲的遗命,为了自己视为生命的巨著《史记》,决定甘下“蚕室”而受此辱刑。为此,他有一段著名论述: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这就是著名的“发愤著书”论中的一段精彩的论述,其影响后来之中国文人、华夏文化甚为深远。出狱之后,司马迁以宦者身份做了中书令,他把余生都投入到《史记》的写作中。作为史官身受腐刑,这就更加使得司马迁难以站在皇权官府史官的立场,冷静客观不带情感色彩来写作史书,以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发愤著书”的、激情四射的文学写作方式,体现出强烈的主体意识的高扬。
司马迁何时完成《史记》这部巨著的,己不可细考,幸而在太始四年(公元前93),他给任安写了一封信,对这部巨著做了总结。因此,一般以此年为《史记》完成的时间,而以他担任太史令的公元前108年为始点,前后共计16年。
关于《史记》的写作,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可视为纲领性资料:
网罗天下放失旧词,略考共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上计轩辕,下至于兹,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视为纲中之纲,是作者自己对这部巨著的理论性阐述。司马迁的写作宗旨,从开始时设想的继承春秋“采善贬恶”的论人论事,发展为探讨天人关系——神秘的、主宰一切的天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联;探讨古今历史“成败兴坏”的变化规律,其著作不是官修史书,而是“一家之言”(浸透着作者的人生观,哲学思想和文艺审美观念);表述自已独到的历史见解和政治理想。
首先,其体例不再是传统的通史,而是新创的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首创纪传体通史之先河。八书详制度,以叙事为主,是个别事件的始末文献,是全书叙事单一的补充,叙述的是政治、经济、军事、宗教、科学、文化等方面的变化终始。十表系时事,依朝代顺序分阶段制作,是某一历史时期或某一大事件的始终变化。书表弥补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缺陷,使整个历史纵横交织,立体再现在舞台上。本纪、世家、列传是史证的重心、是根据人物不同地位而区分的人物传记。本纪记帝王,是帝王的政绩;世家记诸侯,主要是侯王历史,(其中也有例外,如项羽列在本纪中,孔子、陈涉列入世家);七十列传志人物,除《匈奴列传》等六篇之外,都是社会各阶层人物的历史。
其次,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真实记载了众多历史人物和事件。司马迁著作《史记》的思想意义甚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能远远地纵跳出时代历吏的束缚,表现他的“一家之言”——班固所批评的“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汉书·司马迁传》)当然,另一方面,班固也赞扬了司马迁“实录”的精神,所谓“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其实拥有“实录”精神,就必然要突破当时一些历史之成规。
此处所说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的真实性,与本文所论述的文学性小说话写作方式,并行不悖,互为表里。没有这种真实性,就会从根本上否定了司马迁伟大的史学著作的意义。否定了司马迁写作的虚构性、个人情感性,也就否定了鲁迅所指出的其具有“无韵之离骚”的文学属性。他在汉武帝皇权面前,以实录精神记载真实的历史;又在儒家道学的虚饰、时代的压迫下,勇于以文学中国的精神、以文学的方式表达某种本质的历史真实。
鲁迅所评《史记》的“无韵之离骚”,主要从《史记》的文学性、艺术性及其强烈的主体意识来加以探讨:
1、选取典型事件、典型情节、典型材料塑造了一系列性格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不下百人。《留侯世家》中:“(张良)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如写项羽时,作者主要选取三件大事来描写《项羽本纪》,一是巨鹿之战,先从五面铺笔,写项羽破釜沉舟,先声夺人,而战斗情形,则虚写“九战”,“大破之”,一笔带过,从反面渲染,以诸侯军的角度反衬项羽的神武:“诸侯军救巨鹿者十余壁了、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侯皆从壁上观”;再以诸侯“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做进一步衬托。此段文字“踊跃振动;极羽平生”(刘辰翁语),乃“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茅坤语)。二是鸿门宴,写项王极盛之时,却也透露他失败的消息。写他对项伯(他的背叛者)的说情,“项王许诺”写范增的一再暗示,“数目项王,举所佩玉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对樊哙的指责则“未有以应”,刻画了项羽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妇人之心的性格。三写垓下之战,以美人名骓,悲歌慷慨,极写英雄失路之悲,“一腔怒火,万种低回,地厚天高,托身无所”;又以率二十八骑溃围、斩将、刈旗,临死前惊人的成功表演及不渡乌江等,描绘项羽的英雄形象。
2、采用细节描写法与正统的史书不同。如写樊哙闯帐,迁以“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毗尽裂。项王按剑而跽”等细节,而《汉书》则作:“樊哙闻事急,直入,怒甚。羽壮之,赐以酒。”作者还采用了渲染气氛法,如项羽的垓下悲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将弱与刚,美与力,融为一体,形成悲剧氛围。
3、揭示人物性格的语言艺术。如同写见始皇车列,刘邦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项羽却说:“彼,可取而代也!”同有取而代之之意,前者含蓄委婉,后者却盛气逼人。写陈涉少年壮志:“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写其旧时伙伴来宫中惊叹:“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伙颐,楚人谓多为伙;沉沉,形容宫室之富丽堂皇)用楚地口语,皆具形象逼真之神韵;写李斯,以五处独白写其内心世界。起首用其少时对厕鼠、仓鼠比较而发:“人之贤不贤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初步揭示李斯的人生哲学“斯毕生得丧,在入仓观鼠一段,全罩通篇”(叶玉麟《批注史记》),当他极盛时,他也有如临深渊的恐惧“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但在权势的诱惑下,他不可能急流勇退,而是步步走向深渊,在始皇死而赵高欲乱时,李斯辩驳赵高为“亡国之言”,对其危害及其反动有非常清醒的认识,却终于依附叛逆,乃仰天长叹,垂泪太息曰:“嗟乎!独遭乱世,既不能死,安托命哉。”此一叹,必然地引来他狱中之叹:“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吾必见寇至咸阳,鹿游于朝也。”又引来他临刑之叹:“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以上五叹,正是李斯一生之里程碑,故前人评:“行文以五叹为筋节。”(李景星《四史评议》语)
以上的解读,基本还在传统的文学史认知体系之中,以下,更为深入一个层次,来解读《史记》的虚构性和小说性。关于《史记》的虚构因素,学术界是确认无误的。兹以AI对《史记》的虚构和小说写法的分析作为基础:《史记》作为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史学著作,其独特的写作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兼具历史记载和文学表达的双重特性。
将司马迁《史记》进入到中国小说史中,并且将其视为后来中国小说的源头,乃为此前文学史之所未见,这是笔者将中国文学史打通研究之后的体会。那么,此说是否吻合于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的演变历程?兹以司马迁《史记·老子列传》中所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为蓝本,考察司马迁之编撰孔子问学老子的神话故事。
司马迁《老子列传》:孔子适周,将问礼与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以朽矣,独其言在耳。……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此一段故事,来自于庄子的一段记载。《庄子》中对于孔子和儒家的批判是逐渐加深的,在内篇《应帝王》中记载:阳子居见老聃,尚未有对孔子的正面攻讦。到外篇《天地》,则首次出现孔子与老子的交往和对话:夫子问于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方,可,不可;然,不然。辩者有言曰:‘离间白,若县寓。’若是,则可谓圣人乎?”破译庄子的老子与孔子的交往是否真实,只消看看其中的人物、引述的理论等的时代,即可以洞悉其中的真伪,孔子所谓的“离坚白”,就是所谓的“坚白同异”,指战国时名家公孙龙的“离坚白”和惠施的“合同异”之说。对“坚白石”这一命题,公孙龙认为“坚”“白”是脱离“石”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从而夸大了事物之间的差别性。这一理论出自战国时代,孔子怎么会拿来作为辩论的论题?显然是借用孔子出场,以老子的道家思想正面批判儒家思想。
《庄子》外篇中的《天道》,则开始了神话老子,贬低孔子的故事描写:孔子西藏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老聃曰:“……夫子乱人之性也。”而庄子《天运篇》中的另一则故事,则通过孔子之口,将老子神话而为龙,从而成为绘声绘色的神话故事:孔子见老聃,归,三日不谈。弟子问曰:“夫子见老聃,亦将何规哉?”孔子曰:“吾乃今于是乎见龙。龙,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云气,而养乎阴阳。语口张而不能嗋,予又何规老聃哉?”子贡曰:“然则人固有尸居而龙见,渊默而雷声,发动如天地者声乎?赐亦可得而观乎?”遂以孔子声见老聃。(译诂286页)
显然,《庄子》中的这一段故事,就是司马迁《老子列传》的这一段描写的材料来源:孔子去,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此段故事涉及孔子和诸弟子之间的对话,子贡并且亲自去拜访老子,不但《论语》不见任何蛛丝马迹,《庄子》之前亦无任何记载——显然,这一些故事,皆为《庄子》寓言神话故事。
司马迁明知老子应该为战国中期的人,又要编纂孔子问礼老子的故事,不得不杜撰老子的年龄,为了将真假老子合一,先写一个或曰的“老莱子”,随后说老子的年岁是一百六十岁,又索性或云“二百余岁”。司马迁不仅仅是以人物为中心的体例,而且,往往能写出一个人物的鲜活的生命史、演变史,也就是如同小说家所常说的,让书中的人物按照自己的性格,最终走向自己的命运。
司马迁根据前人编撰的故事来杜撰孔子问学老子,用当下的学术话语来说,不说明此说的来源出处,本身就不符合学术规范,而且,将其混入到以真实为本的史书之中,欺骗了后来无数的读者,甚至有人将孔子、老子的这一所谓会面,视为当时最伟大的两位思想家的文化事件,却不知这是从庄子到司马迁编撰的小说故事,两者之间的生活年代,大约相差200年左右——孔子在公元前551年左右出生,老子生活在战国中期的公元前350年左右。孔子的时代,尚无老庄道家思想的存在,道家思想的产生,需要等候墨子代表的墨家思想统治的时代,才能产生老庄的道家思想。
《战国策》汪洋恣肆,洋洋洒洒,引譬设喻,纵横捭阖,极尽夸饰铺陈之能事,其中多有不实之词,虚构之景,如《战国策·甘罗十二为上卿》,甘罗为了证明十二岁可以作为特使,举例说:“夫项橐生七岁为而为孔子师,今臣生十二岁于兹矣!君其试臣,奚以遽言叱也?”十二岁参与列国重大事务,本身就是神话,列举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更是神话中的神话。甘罗中间过程中的一系列说辞连同计谋,均不可信,而到赵国,赵王郊迎这个童子,更是神话。司马迁对《战国策》种种虚构的记载,基本不加甄别地采用,其中特别是关于甘罗十二为上卿的传说作为历史真实加以采用。
司马迁笔下的种种细节描写,悲情渲染,特别是为史传中的人物安插歌诗,将其中的抒情意味推向极致,是《左传》以来渐次形成的写法,而到《战国策》《吴越春秋》《史记》等,形成了极为特殊的中国传统的史传人物写法。到东汉《汉书》《后汉书》之后的正规官府史书,就逐渐不允许这种写法,而改弦易辙,文史两大畛域从此分道扬镳,文体分明了。这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特别是东汉开国之后进入经术时代、经学统治一切领域的必然结果。
司马迁之《史记》影响之于后世,是极为深远的,司马迁评屈骚之语:“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亦可作为《史记》之评。屈骚之于中国诗歌,《史记》之千中国散文,地位相若也。故鲁迅云:“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更进一步,可以将其纳入中国小说史的源流体系中,视为对中国小说影响至深的史传小说渊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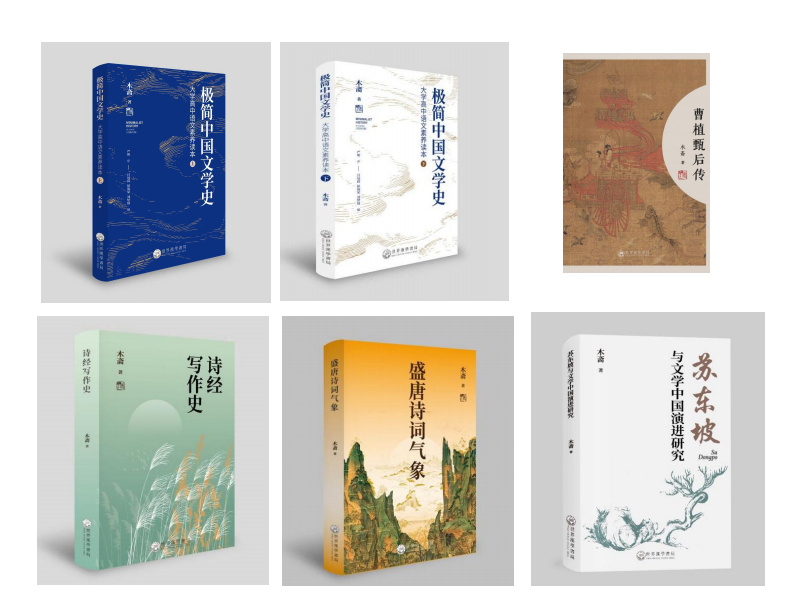
征订说明:新书限时优惠,两本及以上包邮,5月份下单,可享半价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