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墨香深处是吾乡
墨香深处是吾乡
——写在《东楚晚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感恩絮语
吕永超
我与《东楚晚报》,从初读它是街巷故事的熟悉,到持续细品它方知是时代密码的熟知,恰如饮茶者,是嗅得茶香到通晓焙火工艺的进阶。三十年了,一万多个日子,墨香深处是吾乡,我总能在极致熟知中重获初见的悸动。

感恩的絮语,大概要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说起。
那时,正值而立之年的我,血气方刚,出任黄石饭店总经理。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构建现代饭店管理上,我以黄石饭店为平台,大力推行“客人每一次呼叫不是一次麻烦,而是一次赚取利润的机会”的改革实践。这种全新的酒店经营管理理念,以其生机勃勃的原创性、兴利除弊的改革性、“人对人管理、人对人服务”的可操作性,在全省商业系统酒店业引起震动。
那时,《黄石晚报》(《东楚晚报》前身)已创刊一年多时间,记者作风大变,走街串巷,寻找和挖掘新闻素材,产生了一批令人叫好的新闻稿件,让都市五彩缤纷的故事,在新闻纸上重逢,赢得了阵阵喝彩。
一位名叫黎勇的年轻记者,不请自来,走进了黄石饭店,淘洗新闻线索。他深入台前幕后,见缝插针地采访,挖出了那个“震动” 的“新闻线索”,把1996年黄石饭店的冬季搅得热气腾腾。他随即写出长篇通讯《春天的报告——黄石饭店探索现代旅店业管理模式纪实》。我有幸成为第一位读者,欣喜他不是写一个人而是写一群人,并且谋篇布局匠心独运、观点事实鲜活动人、遣词造句分寸到位。这无疑是一篇成功的通讯,我握住黎勇的手说,辛苦了!他的脸好不容易露出笑容,但稍纵即逝。时任总编辑文尚泳先生立即签发了稿件,并安排在1997年1月1日、6日、8日《黄石晚报》二版上连载。
千万不能小瞧这篇通讯,它是1973年开业的黄石饭店运行二十多年来,首次被本地媒体全方位、大篇幅地推介其改革成果、改革经验,文稿导向正确,正能量充沛,如春雷炸响,展现广大职工锐意进取之志;恰骏马奔腾,催征黄石饭店宏图再展。
为感谢《黄石晚报》,我及时主持召开党政工联席会,一致同意,压缩别的报纸征订数量,从1997年元月起,按照黄石饭店客房数量,一次性征订《黄石晚报》196份,做到“晚报到客房,每房有晚报”。这不是为求得心里平衡的喧闹的片刻答谢,而是一家有良知的企业,发自内心的无言回报。
因为这件事情,我对《东楚晚报》高看一眼,并把它放在心里。人生很短,能放在心里的,屈指可数。
2001年,我工作有所变动,到集团公司干常务副总,自主时间相对较多。埋藏在内心的创作爱好,春笋拱土般地抬头露脸。我按捺不住冲动,遮遮掩掩地花了半年时间,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十五万多字的长篇小说《红绳索,黑绳索》。
小说寄给谁?当然是心里头的《东楚晚报》。那个时候我订了一份《武汉晚报》,它的副刊就有小说连载专栏。我贸然地递给《东楚晚报》副刊部主任向天笑先生。都是商业系统的职工,我们早就是朋友,但投稿后我没有向他电话,请他高抬贵手,善待这部长篇小说。
过了一个多月,天笑先生向我电话,告知小说他读完了,好读也好看,符合连载的要求。他已经向总编辑吴刚先生作了推荐。同时,他把修改的小说返传给我。我感谢天笑先生为人作嫁衣,剪刀裁去臃肿的枝蔓,针脚缝合断裂的肌理,那些初出茅庐的文字在他掌心逐渐褪去青涩。我也感谢吴刚先生,他不薄新人、甘为人梯,目光在那一摞稿纸间游走之后,断然决定,留出版面,连载这部长篇小说。
我成为最幸福的人。首部长篇小说在《东楚晚报》全文发表,意味着它每天随晚报进入读者的日常生活,像涓涓细流一样渗透。每天刊登一部分,留下悬念,这种延续性让小说的故事有了生命力,读者每天都有期待,形成了一种持续的互动。好比时光中生长的藤蔓,每天延伸一点,与我们这座城市共同呼吸了。
三年后的2004年,我又一次成为幸福的人。我的农村题材的散文,被时任副刊部主任周明先生看中,在《东楚美文》专版开设“田间拾零”专栏,连载推出《青蛙》《田螺》《蚂蝗》等。朋友们羡慕地说,《东楚晚报》连载散文,你永超是开了先河!
二十四年后,我再次成为幸福的人。我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海观山下》再次在《东楚晚报》连载。我打从心眼里感激各位编辑老师,他们几乎每天都要在《海观山下》的书稿天地里弯腰,或精心制作小标题,审读字词句,或认真校对文字,查漏补缺,多人合作,共同左手承接我的脚步,右手递向辽阔的远方,子夜钟声里,他们在电脑前替我未眠的梦想值更,一次又一次地直到晨曦,为作者的名字加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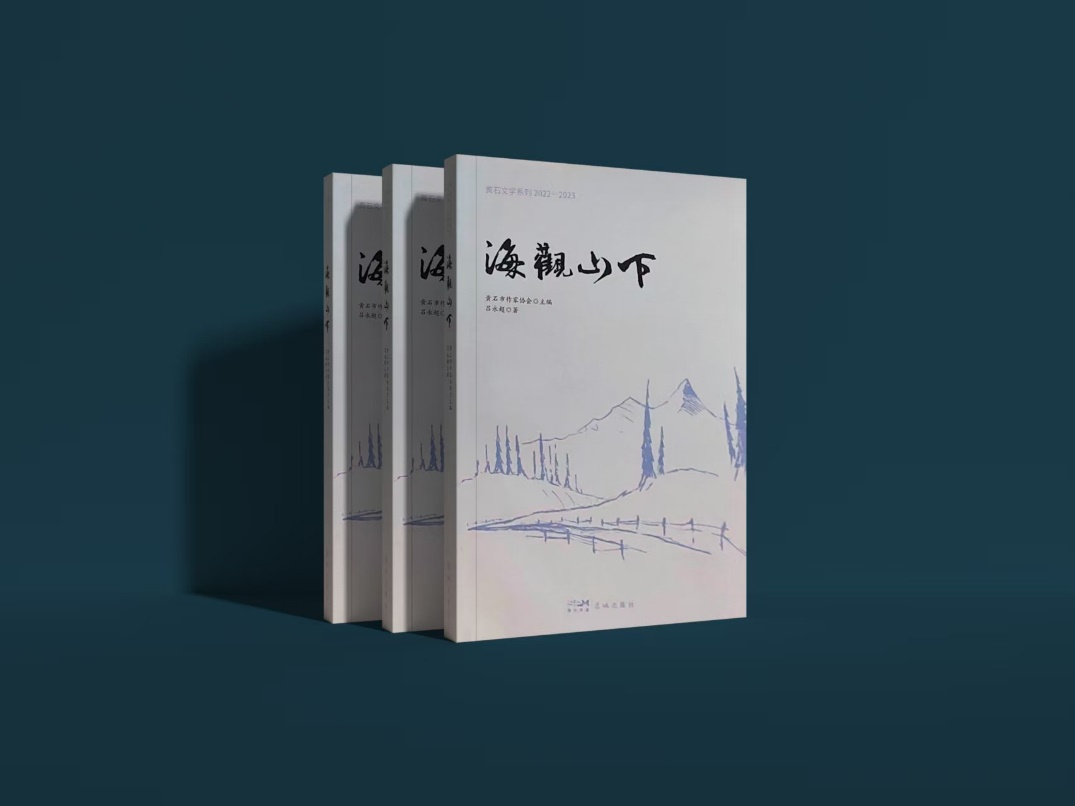
2014年,湖北省作家协会在其官网发布了《<家乡书>散文丛书选题招标公告》。我以《西塞山往事》申报,并洋洋洒洒地附上近万字的“报告书”,直言《西塞山往事》将“以长篇‘乡土散文’形式表达作家独特的家乡体验;用文学眼光去感受、发现家乡的历史、人文和风土民情。”幸运的是,我的选题中标了。多年来,我一直想为西塞山写一本书,终于有了一个契机。
我关注西塞山已经很久了。1984年5月,我在实习间隙,首次登上西塞山。当我弯腰向龙窟寺住持询问它的来龙去脉,这个动作本身,便有了探寻的意味。1985年7月,从学校分配到黄石工作,此生注定与西塞山结缘。然后,我以西塞山为中心,延展至道士洑、散花洲、扬武山、飞云洞、章山城、石龙头、大冶湖、策湖……先后耗时二十余年。这不是简单的行走,而是对大西塞山区域的遗迹、遗址和胜景所深藏的历史细节,一次从头打量。每一处地方,就是一个事关西塞山人文历史的话题,每一个话题源远流长,浩大繁复。在感受沧桑、把握苍凉的过程中,体味古往今来无数哲人智者留在这里的神思遐想,透过“人文化”的现实风景,去解读那灼热的人格,鲜活的事情。当然,在欣赏自然风物的同时,也是从中寻找、发现和寄托自己。

有了这些素材,我日夜不停地敲打键盘,从“神奇石龙头”出发,打开了“爷们西塞山”“白发黄石城”“千年道士洑”“章山古城古事”“活着的国宝”“对话苏东坡”“藏着的钱窖”“石头上墨韵”“非常之人”“沉默的扬武山”等等不再遮蔽的视界,使得我完成“家乡书”课题,得心应手。
这批文稿,被《东楚晚报》“东楚地理”专刊主编刘会刚先生发现后,喜形于色,他认为,文稿“既是黄石地方色彩鲜明的非虚构的文学文本,又不是西塞山地区的旅游导览读本”,“文学性,史料性和可读性,相得益彰”。我记得给会刚先生的第一篇稿件是《寂寞的飞云洞》。他伏案修剪,细细熨平文字、悄然隐去所有修补的针脚后,逐级向专刊主任文林、总编辑华夏送审,这两位负责人也是一路绿灯。至此,《东楚晚报》在2014年4月12日至2015年7月24日这个时间段内,不定期地用两个甚至三个整版,刊登成稿的每一篇文章。然而,署名栏却永远开着刘会刚先生的无名花……
我与《东楚晚报》之间的故事,远远不止这些。
墨香深处是吾乡,行文至此,意犹未尽,说几句感恩絮语:
三十年,《东楚晚报》已经让一粒种子长成亭亭如盖的大树,让稚嫩笔触沉淀为墨香的指纹。当暮色漫过黄石褶皱,你依然如候鸟般准时报晓;在万家灯火将燃未燃的黄昏,你用温热的油墨织就人间经纬。你始终是我们这座城市掌纹里最绵长的脉络,让散落的星火聚成银河……
作 者 简 介

吕永超,出生在武穴市一个叫小金冲的山村。退休公职人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本文首发《黄石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