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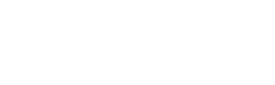

□著名作家 王志钦

人生有许多大喜大悲,许多丧失,许多收获,许多骄傲,许多沮丧,都渐渐被岁月的风沙掩去。唯儒山下的琅琅书声依旧,蟹子湖畔的汩汩桨声依旧以那青春的温柔,抚摸我布满皱纹的灵魂。
——摘自黄自华散文《等待》


(黄自华著作照)

如果说人类因思考而伟大,那么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艺术家便是“伟大者”中的活跃分子。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每一个独立思想者的生命本身,却处处显示着他们的被藐视;他们的生涯往往在黯淡中结束。从他们灰暗的生存境况中,我们往往感受到的是他们沉重的生。司汤达的墓碑上题写的是他自拟的墓志铭:“阿里果·贝尔,米兰人、写作过、恋爱过、生活过。”看似很潇洒,其实未必。思想者总是寂寞的,不是因为他们所处太高,而是缘于周围的沉寂。如同站在舞台上的演员,他们渴望轰然而起的掌声,而掌声迟迟不起,因为台下根本就没有观众。文学评论家黄自华也是一个“渴望轰然而起的掌声,而台下却根本没有观众”的“演员”。没有观众的演员,是最可怜的演员。
黄自华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但他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文学评论体制边缘的“喧哗”者。用他自己的比喻来形容,他是“一只在空旷的沙漠上,孤独徘徊的野狼,声音尖锐而凄厉”。黄自华藉此嘲笑自己,也嘲笑这个世界,但这不是所谓“自虐”的需要,而是基于一种内省的勇气。因为正是从这种对于自我的审判中,他获得了自我解构的尊严。
我们人类自称万物灵长,实际上对于自身的底细,往往处于懵懂不清的状态。大哲学家蒙田曾对人类下过一个严酷的断语:“他们长期以来进行探究的全部结果,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低能。”人类即使不完全低能,却也是迟钝的。只要看看人们对待思想者的态度,人类就会为自身的不智而不堪羞愧。大画家高更去世后,他的遗物被人拍卖。卖得最廉价的,是他平生最后一幅画作。在一片哗然戏谑声中,画作以八法郎成交。倒是他储藏的醇酒、烟丝、罐头,引得全场肃穆起来,件件卖到了好价钱。
其实,这一切都不奇怪,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看待文人,同样也不会以其作品好坏作为价值评判尺度,而是谁掌握了话语权,谁的酒后醉语就成为准则。中国文坛的话语权,牢牢掌握在那些栖息在体制围墙内的主流派文人手中,中国文学的裁判尺度是由他们制定的。尽管那些人的文章,早已格式化为一种固定的官方模式,但它的权威性不容挑战。对于圈子外的任何真知灼见,他们都会嗤之以鼻。文学评论家黄自华的文论,虽然以犀利深邃的思想内容、豪迈旷达的行文风格、丰富生动的语言文字,深受厌倦了当今平庸低俗文学评论的读者所喜爱,但他的名字与他的生存处境一样,始终处于灰暗、困顿、被遮蔽的状态。
黄自华是一个从高炉的烟熏火燎中走出来的“草根”评论家;一个没有进过大学校门,仅仅依靠自己的坚忍和勤奋成才并学识渊博的知识人;一个对腐朽愚昧、虚伪卑劣,永远横眉冷对、无情鞭挞的孤傲斗士;一个身在“江湖”心忧天下,愤世嫉俗的“另类”;一个对新的、真的、善的、美的一切事物声嘶力竭地叫好、对青年作家倾尽全力扶持的长者;一个被过去与未来纠结得痛苦不堪,被理想与现实撕裂得身心俱疲的殉道者。他的纠结,他的愤怒,他的痛苦,他的呐喊,他那颗被撕裂的心,究竟有多少人理会呢?
黄自华清醒地知道,在以主流话语为时尚的当代文坛,自己只能是一个在体制边缘野蛮生长,而且人微言轻的“草根”评论家。但是,他并不在意自己被边缘化的尴尬处境。他曾经在一首打油诗中嘲讽自己:“一袭青衫神情寂落,双目怒睁心底悲凉。激扬文字粪土权贵,笑傲风云睥睨古今。”(《自嘲》)
即使是在西方也被视为“离经叛道”如“斯芬克斯之谜”一样的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和美国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是对黄自华的独立思考能力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者。米歇尔·福柯著作中那些富有冲击力的思想主题和激烈批判现代理性的话语,尤其福柯具有鲜明文学色彩,讲究修辞,饱含激情的行文气势,对黄自华文学评论风格的形成,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而理斯曼对于“群体意识”的嘲讽,对于“自我意志”的张扬,也在黄自华“公共人格”成长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但从本质上讲,黄自华是一个“宿命论者”。他对记者说:“一个人的生死观是许多事、许多人,以及个人经历、甚至包括阅读所共同塑造的。父亲这代人的命运,让我看到个人的渺小和在命运面前的无望。无数个人的悲伤,无数个人命运的不可抗拒,导致我的悲观。我的宿命感好像与生俱来。萨特说‘存在是偶然的,人生是荒谬的’,人活着本身就是一件虚无的事,人生的意义就是‘活着’。人生来就要死的,生是暂时的,死是永恒的。怕死的和不怕死的人,穷人和富人,有权者和无权者,谁也没有能力改变它。这就是整个人类,甚至是整个生命世界的宿命。”
“最初引领我走上文学之路,并影响我终身的,是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恢弘大作《约翰·克里斯朵夫》。”黄自华深情地回忆道。这部思想深刻、语言华丽,气势雄伟的鸿篇巨著,震慑了中学时代黄自华的情感和灵魂。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样一个天赋极高,目标远大,具有崇高理想和坚忍意志的艺术家,成为青年时期黄自华的崇拜偶像。爱上了约翰·克里斯朵夫,从而爱上了文学;爱上了约翰·克里斯朵夫,从而也踏上了一条追求正义和真理、布满荆棘和风暴、跌宕起伏的不归之路。
彼岸,遥遥地面对着人生,它不同于人类追求的现实,也并非不可企及的天国,它是人类知性的最高境界,是一种超越的存在。彼岸虽然是一种超越,但它又以不同的现实具象存在着。拨开惊心动魄的生死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眼花缭乱的生命形态之下,人对本体生命意义的追求恰如他们对待各自事业的追求一样,执著而顽强。在这种追求中所体现的高下卑劣,也如他们在创造世界中的人格一样,丰富着人生。唯其如此,他们孜孜以求的精神,寻求冒险、追求完美、仰慕崇高的品性才能得以实践。因为那些寻找彼岸的人,注定是一些不甘平庸的人。
边缘喧哗——黄自华评传(二)

决定黄自华性格形成的最初原因,应该返回到他的童年经历中去寻找。黄自华十四五岁时,就已经经历了人生第一波打击的疼痛,在疼痛中,他开启了思考的风帆。而这种疼痛和思考,肯定不应该是一个少年期的孩子应该承载的。这就是在黄自华的思想里,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反叛与孤独的最原始起因。同时也决定了他的思想和性格必定曲高和寡,他的命运必定一生孤独寂寞。青年时的黄自华曾经用尼采发出的如下感叹来况味自己的人生:“我在人群中行走,如同置身于人的废躯残体之中,如同零落于战场和屠场之上。”他说:“像叔本华一样悲凉,这是我们有可能获得精神成长的唯一途径,否则,我们一切宝贵的东西就都会流散在世俗和时尚的温暖大海之中;如果我们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我们可能不悲凉,可能很温馨幸福,但是到了晚年,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实际上一无所有。”
黄自华的童年,在严酷而愚盲的教育体制下成长,又过早地承担了一个求学少年不该承担的悲剧——一个敏感的灵魂缺少社会宽容和温情的悲剧。但也正因为他的精神状态和物质生活长期处在无间歇的波动中,过早地接触到了罗曼蒂克的遐想,从而滋养了一种向往伟大和爱好梦想的情趣,使他获得了一种逃出自身,而又躲入另一个“暂时人身”的禀性。他的缺点如同他的优点,都与一个把握不定的“少年疼痛期”密切相关。没有受到高等教育,好像注定他一生会庸庸碌碌,然而,他偏偏由于亲身经受的苦难和不可逾越的命运,奋发自强而不同凡俗。
1941年,黄自华出生在武汉市蔡甸区侏儒山镇一个经济丰实的家庭。父亲是读书人,“自华”这个名字,是父亲从苏轼《和董传留别》诗“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句中提选的。那时候的侏儒山镇,号称小汉口,街市繁华,商贾如云。当年侏儒街上整齐平坦的青条石板路,如今已被深灰色的水泥覆盖。但是,拂去历史的尘埃,仍然能够窥见它昔日的繁华。读书人“唯有读书高”的入世情结,驱使父亲逼迫黄自华从小就在他的“戒尺”下识字读书。5岁读《幼学》,后进私塾读《论语》,背诵不了那些生涩深奥的字句就打手心。7岁进小学,父亲为黄自华奠定了厚实的古典文学功力。但他始料不及的是,从小接受儒学教育的儿子,日后却成了一个对儒学口株笔伐的叛逆者。即使是当下,黄自华仍然经常在自己的博客上,对所谓“新儒家”大加挞伐。他最近还在《儒教亮剑——还乡团回来了》一文的按语中指斥“新儒家”说:“当年祸害老区百姓的彭霸天又回来了,但他们很快又被红军消灭了。历史将会证明,垂死挣扎的儒学,终究也逃脱不了彻底覆灭的宿命。”
“小时候,父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父亲对我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聪慧和勤勉。他常给我讲《四书》《五经》那些我当时根本就听不懂的东西。不允许我阅读《西厢记》《桃花扇》《三侠五义》之类的杂书。父亲强迫我读书,他说,不懂不要紧,但要能背下来,记住它。将来你慢慢会懂的。”但小黄自华还是经常偷偷去隔壁中药店一个老账房先生那里听他讲故事,在说书的老先生那里,听他讲述“薛刚反唐”“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跌宕起伏的英雄传奇。让父亲同样始料不及的是,成人之后,黄自华最喜欢读的书,竟然不是圣人的“四书”“五经”,而是西方哲学、历史、政治、美学、社会科学、经济学,以及中外经典小说、诗歌、散文、明清笔记、古典诗词之类的杂书。但也正是这些“杂书”,成就了黄自华在文学评论创作上独特的视野和博大的胸襟。
初中时期的黄自华,数理化成绩勉强及格,但文史地,尤其作文成绩,还是满足了一个懵懂少年出人头地的虚荣心。想不到的是,初中三年级时,发生了一件影响黄自华命运的意外,他的私人日记被班主任看到,几句表达对班干部不满的稚嫩诗句被判定为“反诗”。这时的他只有15岁。老师在班上召开黄自华的批斗会,对一个稚气未尽的少年进行了无情的羞辱和摧残。父亲摇头叹息,认为这孩子“离经叛道”,母亲因为爱子而黯然流泪。黄自华孤独地伫立在小镇旁的荷塘边,这是他儿时经常与小伙伴们游戏玩耍的地方,这里踯躅着他快乐的童年。而此时,他无意欣赏满眼如诗如画的红莲绿荷。仰望碧蓝的天空,他从心底升起了无限的迷茫和惆怅。
少年黄自华并不知道1958年的中国发生了什么。他还小,中国对于他来说,也许太大了,他不可能弄懂一切。但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变故,其疼痛的感受是真切的。他不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愤怒和抗争却从此在少年的心中埋下了种子。成年后的黄自华,之所以对一切泯灭人性的虚假伪善、扼杀正义良知的强力权威、不公平非正义的倒行逆施,总是进行不知疲倦的抨击,也许源头就在他15岁时所经历的那场批判会上,或者就在他仰望苍天,无奈叹息的那一瞬间。
伟大哲学家卡莱尔说:“不曾哭过长夜的人,能否足以语人生?”东瀛智者鹤见祜辅也说:“一切伟大的人是由泪里生长,从苦恼和窘迫中间迸出来的。”难道人生颤栗的苍凉,真的都是来自于这样的警句吗?如果黄自华生来安逸和平,能够有今天精彩熠熠的文才?犀利深邃的文字,是否因为他在暗淡的人生中体味了太多的悲戚!
初中毕业的黄自华,因政审不合格被高中断然拒之门外。贫苦的家境不允许他在家吃闲饭,母亲四处奔走求情,黄自华得以到镇政府做了一年的信用部会计。1959年,是全国教育大跃进的疯狂年代,大专院校扩大招生,黄自华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求学机会,从远离城市的侏儒山镇,到武汉寻找求学机会。经过几场考试,他同时被华中农学院和湖北煤炭学院录取。正当他准备去华中农学院报到时,不料他在南昌320厂当空军军代表的姐夫,给他寄来一份南昌航空工业学校的入学通知书。尽管这只是一所技术学校,但从这所学校毕业的学生,将会分配到飞机制造厂工作,黄自华果断选择了南昌航空工业学校,从此与大学失之交臂。少年黄自华哪里知道,他放弃的不是一张大学文凭,而是走向“庙堂”的通行证。


王志钦,1946年出生于武汉。作家。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在《长江丛刊》《芙蓉》等多种文学杂志上发表过中长篇小说。著有长篇小说《慕容小珏》《《小仙女安曼与神珠之谜》》。现居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