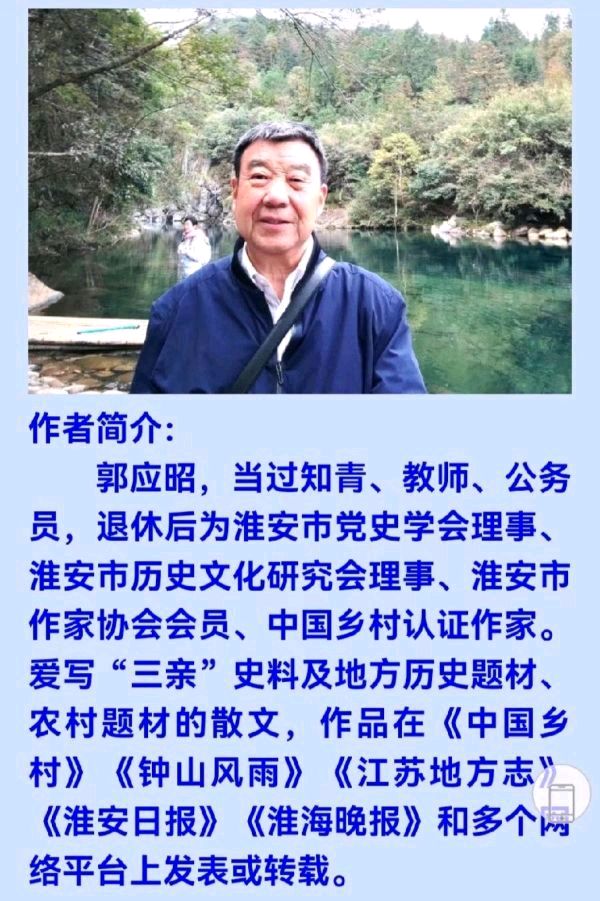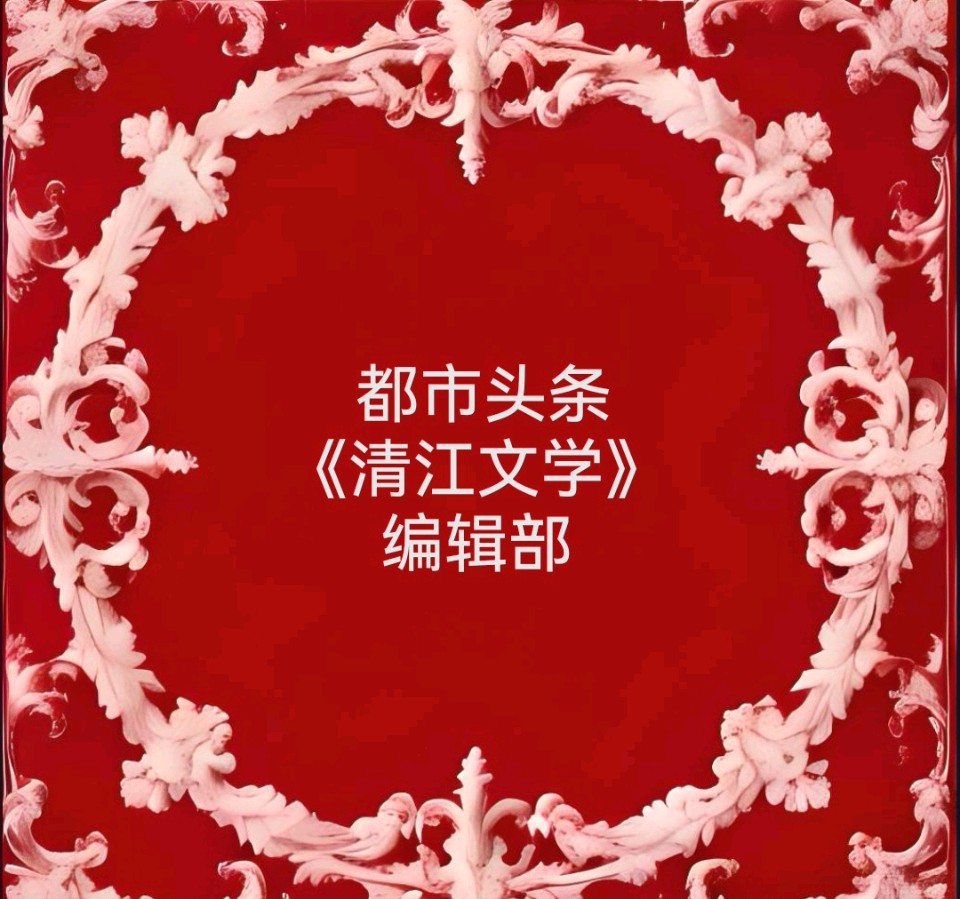郭应昭
我曾和农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脸朝黄土背朝天。那是1968一1974年,我从原清江市(现淮安市)到洪泽湖畔的公河公社双坝大队三队插队当农民。六年中,泥里来,水里去,与那里的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里,散落了我的许多记忆。
那个时期的农村不叫乡镇、村,叫人民公社和大队,农民叫人民公社社员。农业学大寨中,社员每天要“大呼隆”下湖劳动三次。早饭前后各一次,午饭后一次。早饭前两小时劳动记两成工,早饭、午饭后各记四成工。一个劳动日为十成。每年评工分前都要“斗私批修”“心灵深处闹革命”。一个劳动日最高十分,最低四五分,我一个劳动日从未超过九分。大队书记和社员都说知青与当地人无亲无故,办事公平公正,让我在三队当记工员。不要小看记工员的那支笔,它关乎社员们的全年收入和粮食分配,我不敢马虎,认真记下每个劳力的劳动日程,即使有人没上工,我都要在他(她)那天的备注上写明走亲或赶集等,以作备查。记工员相当生产队的“三把手”,18岁的我曾神气活现地吹着铁哨从前庄到后庄通知社员下湖上工。
双坝大队东西十里路长,南北五六里宽,有16个生产队,数西边的三队最穷。双坝大队姓氏有赵、李、王、姚、倪、费、韩、马、高、徐、戴、谢、邓、杨等,其中赵姓是大姓,在全公社亦如是。赵姓辈分高的在西面的一、二、三、四队,当年最长的是“启"字辈,次之为“序”字辈,辈分再往下是“可、长、建、洪、恩……”,东面生产队“建、洪”两个辈分的人居多,五六十岁的“洪”字辈见到西面十几岁的“可”字辈要叫老太爷。辈分就是这样,“百家姓”中第一姓也概莫能外。
洪泽湖水灌溉着湖畔万顷良田。 双坝大队沟渠成网,多种水稻。比较而言,东面8个队要比西面的三队粮食产量高出50%至一倍,社员收入也水涨船高。那几年,我所在的三队10个工分值仅三毛多一点,而东面队多是五六毛以上。
在乡下,我干过许多农活。打过秧线挑过稻(麦),挖过田沟破过垡(犁起的灰黑色大黏土块),扛过木棍看过青,大队粮食加工房里开过机、收过加工费……
下乡第二年的栽秧季节,队里人告诉我,被蚂蟥叮住了要用手打,我听后真有点吃怵,心想不要让我碰上噢。谁知第三天的下午,我在三队队房西旁边的冒着黑泡泡的水田里栽秧,突然觉得左小腿肚痒了起来,低头一看,一条蚂蟥正叮在那里吸血。瘆人啊,我鸡皮疙瘩顿时暴了起来,慌忙用手去拽,谁知蚂蟥被拉得老长就是不松口……“用手打!”有社员提醒,我才甩起手对准蚂蟥狠抽了两三下,蚂蟥掉下来了,只见被蚂蟥叮的地方向外汩汩地流血。
金秋季节是社员最开心的日子。大队加工粮食的宁波独缸柴油机轮流到生产队帮助抢收脱粒。社员们白天忙不过来,夜晚得挑灯加班。加班既得工分,又可吃到免费的有猪肉的菜饭,社员们个个都笑嘻嘻的,像过节一样。那些年的水稻品种多是农垦46和57,机出来的米没有耐肥的水稻“桂花黄”好吃。桂花黄”煮出的饭和粥粒如珍珠,香气沁脾,至今想起还满口生津。“桂花黄”口紧,脱粒费劲,须人工用滚筒机(长龙机)打,四五人一组,顺着脱粒机挡板站成一排,用一只脚一起用劲踩踏板,使滚筒向前转动,双手紧抓小捆稻把摁在旋转的嵌有排排钢筋的机筒上左右反复打。而农垦46和57则需用铁叉将其喂进乱膛机(脱粒机),稻秸秆和稻粒便自动分开……
那里的农民善良、朴实、热情、大方,就像那盈盈长流的洪泽湖水欢快地顺渠而下,浸入心田。
1970年,我被安排到离三队五里路远的大队碾米磨面房开“飞子”(收据)收加工费。加工房在八队,我接触到六至十队的许多去机粮食的社员,其中包括这几个队的队长和会计。为帮助我解决粮食不够吃的问题,七队会计王守业、八队队长邓国余都曾主动叫我用征购价去他们的队场各称50斤稻子。九队队长杨明富每次挑着两只大笆斗来机米,他多用机好的米充加工费,他用白铁插子窊的米往往超过加工费的一倍。这三个人都已先后离世,但他们的笑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从机米房回三队后,我干过一段时间“看青”。三队有三个庄子,前庄、后庄、甘庄。每年三个庄子东面的庄稼被猪、鸡、鹅、鸭糟蹋了一半。三队的赵序凤二爷老两口待我最好。他们家后有个小竹园,常编些竹篮、竹畚箕去赶集,手头活套点,他们经常喊我去吃饭。去得多了,他们家的大黄狗对我非常亲热,看到我总是上蹿下跳,摇头摆尾。看青时,我一声招呼,它一下子就蹿到我的前面去。不需我吆喝,钻到大田里的鸡、鹅、鸭就被它撵得咯咯咯、嘎嘎嘎、呱呱呱地没命地张开翅膀跑,跑得慢的被大黄咬得羽毛乱飞。有的猪不理睬,被大黄咬住耳朵往外拖得嗷嗷叫。这时猪的主人便在庄头上大声往家唤猪:“呦一嘞嘞嘞……”那年秋天,三个庄子东面的大田喜获丰收。
那里的人常端着饭碗在屋外吃饭,看到路上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都会远远地招呼:“来吃饭噢!”声音非常亲切,无虚情假意。我不止一次地见过曾有受灾从安徽过来的乞讨男女到双坝,他们每到一家,当地农民都不会让他们空手离去,或窊点米或窊点小麦灌进他们背上的口袋里。
别看三队穷,但三队人对我们知青从不吝啬。我们知青仨几乎吃遍三队各户,有的人家被吃过多次。我们每次去吃饭,他们都会笑着说“不要拘礼”“作假自忍饿噢”,并用大碗给我们装饭,饭都堆出了碗口,像个小富士山。桌上,他们还用筷子在菜碗上划拉着连催我们吃菜。
……
插队农村的6年是我人生中一段重要的历练,让我懂得了农业、农村和农民,学会了一些农活,丰富了我的人格和精神,使我多了一份正直、淳朴和坚韧,对回城之后我的工作和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离开双坝多年,梦中曾几回穿越过去,那里的一沟一渠、一草一木还是那么清晰和亲切。现在的双坝村已物换人新,今非昔比,但那个年代的农村经历给我留下的不仅仅是记忆,而是一种人文精神和乡村文化的传承,是对新时代的感恩和图新。
如今的双坝村村部
洪泽湖水流经双坝村旁的邵武闸(以烈士李绍武命名)
双坝村稻田
2024.9.2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