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王鼻子与善德泉的故事
房思春
听说胡家桥村有一处泉水,就在村东,自建村以来,就是村人饮用的水源。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生产队时期,村里还依托泉水,建起了胡家桥酱油酿造厂,生产的酱油质量很好,深受周围群众欢迎,销量还不小,成为胡家桥村的重要经济支柱产业。改革开放后,酱油厂被合并到黄庄人民公社。
这个泉子,距离柿子峪村不足千米,可是柿子峪村的泉水早已经城里有名,乡里有号,已成为济南名泉,并且依托泉水,打造成了旅游景点,可是胡家桥村的泉水,却藏在深闺人不知。偶然的机会,让我有幸欣赏到了泉水的风采。
年轻的张书记想依托泉水,发展乡村经济,就亲自接我和老尚上去看一看,想做一下宣传。车到了村东,停在路边,书记从车后备箱里拿出两双水鞋给我们换上。
已经多少年不穿了,这可是从前出门必备。从前村里街道都是土路,一下雨,满街泥泞,雨后出门上街,须穿水鞋。可能有水鞋的又有几家?雨后能穿着水鞋上街,也是家境好的一种炫耀。现在,乡村街道,包括田间道路,都已经硬化成水泥路,无论下雨下雪,都不必担心不好走,水鞋也早已从人们的生活中告退消失。
我们沿着一条小路向阎王鼻子山行进。小路左侧是一条高高的石堰,堰下是一条深沟,里面栽满了槐树、杨树,正当枝叶茂盛时候。透过细密的枝叶,可以看到树荫下是明晃晃的水。这是刚刚雨过,上面泉水流下来,被公路阻隔,在此汇聚,里面还杂了许多垃圾,漂浮在水面上。
往里走了30多米的样子,就没有道路,只有水路了。越往里面走,地势越高,清清的溪水,到处都是,旁边的柴草底下,亦有水汩汩流出。我们穿着水鞋,逆行在浅水里,看着脚下哗哗流淌的水,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老家是一座四合院,大门前面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浅沟。沟不长,也就五六十米的样子,东面是一座弧形的山岭,每逢下雨,山岭上的雨水,就汇集到这条浅沟里,从大门前南折,注入黄庄河。说白了,大小且不论,这条水沟确是黄庄河的一条支流。
沟里面是多年淤积成的一块沙质小块平地,我的爷爷为了防止水土流失,就栽种上棉槐、白蜡。春天生发,夏天就在雨水的浇灌下,长出细长葳蕤的的枝条,到了深秋,爷爷就用镰刀收割了,准备编筐编篓用。沟里面一下子清亮起来,留下的是一攒一攒的木茬子,支棱着一个斜面,锋利如刀,所以我们是不敢进去玩耍的。
沟两边是一些荆棘等植物,间或有杏树、栗子树、臭椿树,还有两株柿子树。沟里还有两棵梨树,也都是有年头了,不是很高,但是枝头繁茂,每年都结不少的梨子。
就是这条浅沟,却是我童年时候最喜欢的地方。
且不说夏天满树的杏子,秋天满树的梨子,也不比说深秋满树的红柿子。单单就是春天的杏花梨花桃花,就足以使人身心俱醉、流连忘返。
那五六棵大杏树,心有灵犀一点通,那杏花,说开就开了,枝繁花茂。一棵树就是一个大花球,那香味细腻柔软,随风飘荡。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蜜蜂、蝴蝶,忙忙碌碌,从花球里飞进飞出。那样子,兴奋而又满足。也偶尔会见到一身碧绿的大蚕蛾子趴在树干上。个头虽大,似乎飞不动,所以,常常做了我们的战利品,捉回家,用线绳拴住它翅膀,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被玩死了。
杏花开过以后,梨花上线。不动不惊的雪白。缠着衣角的梨花香,随风流淌的香,于是乎,一沟的清香。
夏季到了,一场雨过,沟里流水潺潺。这时节,几乎天天摽在沟里玩水。黄庄河里也有水,但是父母担心不安全不让去。就在大门前的水沟里消磨时间。
然而这一切,都消失在了回眸之间。
1976年,黄庄河改道,神崮山东面的二十多户村民搬迁到东岭。运东西先修路,生产大队就沿大门前的沟南边修了一条便路。本来就不宽的沟,埋填了一多半。沟南的杏树、柿子树、枣树、榆树,惨遭屠戮。再后来沟北的地块,划了宅基地,村民在建房时,又把沟北的杏树、桃树、臭椿树砍伐了,沟也填平了。从此,少年的记忆、少年的美好时光,也被填埋进了时光里。
时光已经无法追回,记忆经时光的洗礼,却越来越清晰。人总是在经历中长大,在无奈中老去。那座修建于民国二十六年的四合院,也已人去院空,房屋倒塌,尽显岁月沧桑之无情。
现在的孩子,也远离自由世界,在被动中长大。不得不让人汗颜,这都是聪明人类作茧自缚啊。不知道有没有人会和我有同感。
再往前走,石壁下一个水潭展现在眼前。
水自石壁上缝隙流出,由于才过了几场雨,泉水还旺。泉眼碗口粗细,犹如喷珠泄玉,注入下面潭中。潭约20平方米见方,深约2米许。潭水清澈如碧玉,冰凉刺骨。泉水周围树木遮天蔽日,植被丰富,清幽素净,人在潭水边,顿感凉意扑面,好像进入清凉世界。潭的左右两边,石砌池墙扔在,石墙上长满了青苔,尽显着岁月悠长。
随行的书记讲,如果是刚下过雨,泉水激射,喷花溅玉,可以持续数日,来时路上会水深没膝,常时水量略小。泉背后的山崖上曾有古树数棵,文革期间人为砍伐。还有就是,近些年,村民们为浇灌山上果树,在泉的上方打了许多深水井,严重影响了泉水水量。
说话间,我们看到在泉水的上方,有好几根树干架起的红绿电线,出没在绿树从中。一根电线,就连接着一个地下深水泵。毫无道理,而又理直气壮的人们,在世一辈子,就是无尽的索取。人之私欲,犹如无底之沟壑,如何能够填得满。
清澈的潭水中,有青蛙在游弋,看到我们的入侵,都急急忙忙潜入深水处。泉水出潭,一路浅吟低唱,注入村南月牙潭。
回村委的路上,支部委员张友祥给我们讲起了阎王鼻子和善德泉的故事:
相传在古时候,有一对法力无边的千年狐仙,云游天下,这天来到了历山。站在山上向山下望去,但见西面山脚下,一水如带,滚滚西去,山上泉水叮咚,一棵银杏树遮天蔽日,庙宇里面香烟缭绕。知道这是舜皇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不禁感叹历山真是块宝地。
再往南看去,山坡上有一片茂盛的树林,树木遮天蔽日,树林上空若隐若现的流动着雾气,一片朦胧犹如仙境。在树林中还有一处泉水,水自崖壁石缝中泄入石潭,在阳光的反射下,潭面犹如一面镜子,熠熠闪光,潭水清澈如碧玉,甘甜可口。狐仙心下暗喜:这真是一块仙灵宝地,如在此安心修练必将得见仙缘早成正果。
于是狐仙夫妻在此安居下来。在树林东侧有一小山,山上树木茂密,经常有野鸡出没,就取名雉鸡山。他们一边修练功法,一边在山中遍寻仙药灵草。潜心钻研治病良方,为历山周边乡民百姓解除病痛、广积善德。从死边缘救回了不少人的性命,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
可这件事被黑白无常汇报给了地府阎王:“根据生死簿记录,周围村庄有应死之人,我俩前去押解之时,却见当事人阳气旺盛,令我二人无法靠近,只好禀告大王。”阎王掐指一算,原来是狐仙治病救人、起死回生。如果长期这样下去,那岂不是坏了生死轮回的定律。于是阎王决定亲自到阳间走一趟。
且说这天晚上,狐仙夫妇正在茅舍中打坐修行,只听历山主峰西侧有人传音给他说道:“狐仙夫妇,前来历山顶峰西侧,面见本王。”
狐仙夫妇一听,知道传音之人不是凡人,便立即前往相见。到了山峰顶处一看,原来是阎王,便躬身施礼:“参见阎王大人,不知有何事召唤小仙。”
阎王说:“你治病救人也算善举,可你把应死之人也救回阳世,破坏了轮回定律,实不应该。”
狐仙回道:“大王,我所救治之人,都是积下功德之人,虽生死薄上期限已到,却因他们日常行善积德,上天延长了他的寿命,我只是听从了上天的意旨而已。”
阎王听后说道:“这样吧!我上山之时在路上遇见一樵夫失脚掉到山涧,如今已是气息奄奄,我刚查过生死薄,他该当今日枉死。如你能把他救活,我自罚割掉鼻子弃之此山,如你救不活他,你夫妻二人随我去地府吧!”
狐仙夫妇齐声说道:“遵命,就听您大王的。”就把随身携带的灵药灌入樵夫口中。不一会儿,樵夫就活了过来,谢罢狐仙归家去了。
阎王看后长叹一声说:“罢了,是上天支使你的。”
说完抽出随身佩刀,挥刀把自己的鼻子割了下来,随手扔在山峰上。鼻子落地后变成了鼻子形状的巨大山石,而阎王的脸上却又生出来一个鼻子。从而,历山西南面的这座山峰,被称为阎王鼻子。
狐仙夫仙连忙躬身施礼道:“大王不要懊恼,这樵夫是一个大孝子,为人行善积德,获得上天眷顾延长其寿命,我夫妇二人也只是替天行道而已。”
阎王说道:“就让我这个鼻子化成的山石,立在这山峰上警示后人,只有积德行善,才是延年益寿之根本也。”说完就打道回府了。
而那狐仙夫妇日后,也因行善积德,修成正果后飞升天界。当地百姓为记念狐仙夫妇的功德,就把此泉叫做“善德泉”。因此泉在旧村东边,有村人习惯上称做东泉。
善德泉的故事,滋润着人们的心田,涵养了淳朴的民风。行善积德,成为胡家桥村民遵循的村规家风,教化了一代又一代的胡家桥村民。小小的山村里,张氏家族走出了张孝德将军。他1946年参军,1958年调入国防科工委工作,1983年,他被任命为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并被授予少将军衔。他一生刚正不阿,一身正气,对党和国家忠心耿耿,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用生命为民族注入了不屈之魂,为祖国航天事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张德利书记也是张氏家族的一员。他说:“我的二老爷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万贯家财,却给我们留下了艰苦奋斗,大公无私的精神。现在我在这个岗位上,深感责任重大,虽然现在还比较艰难,但是,先人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永在,我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胡家桥村的明天定会越来越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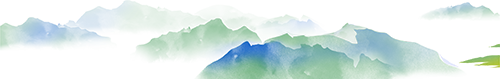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