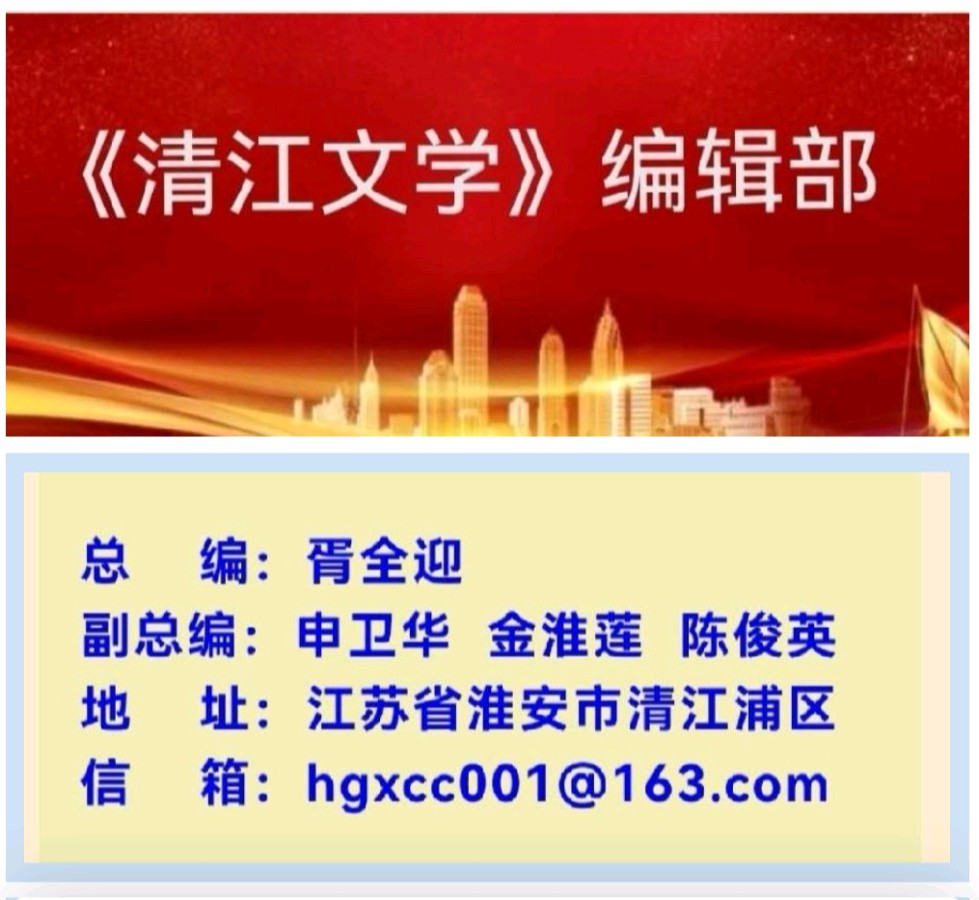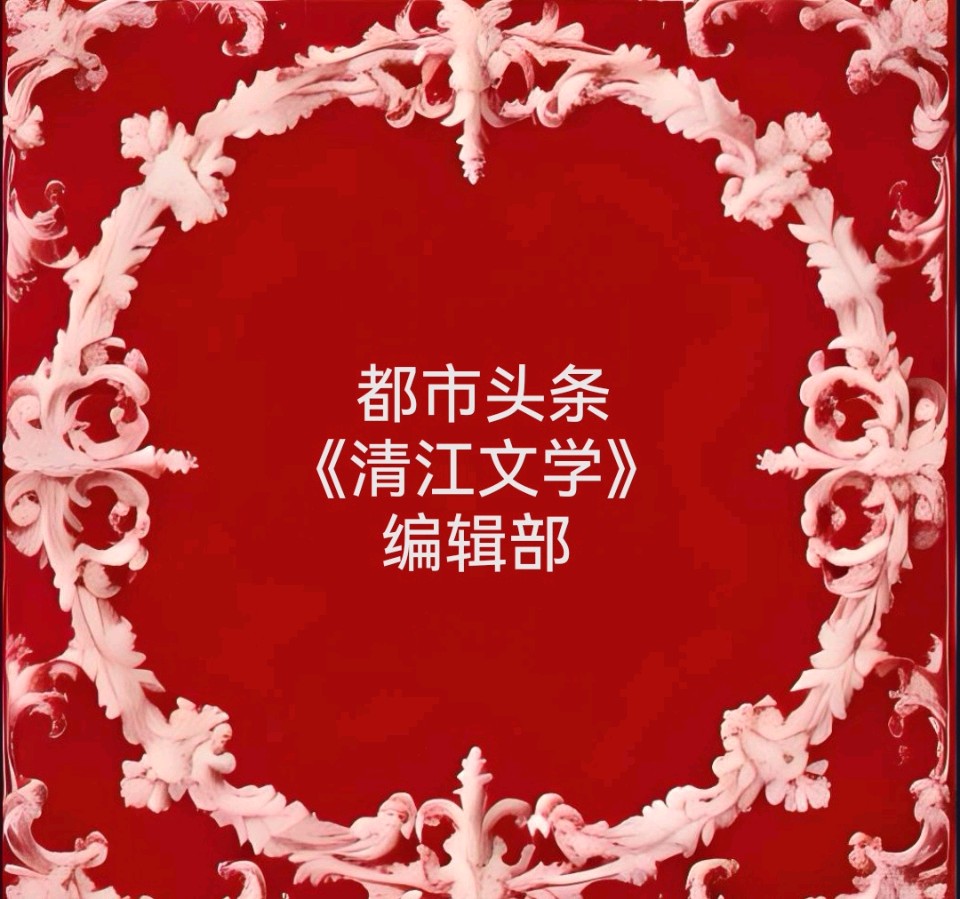王营城隍庙
这个童年时候没有什么好玩的,长年在家前屋后及附近玩,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啥样。
最盼的是过年过节。因为有节日,家中都要买些肉和其他好吃的菜等,尤其是在清明节。
我家南面有一大圩堤,下面有两个大石墩子,矗上一人抱不过来的大木桩,高约三、四丈,上面还有四方形盒子的框子。这是王营城隍庙的一座大戏台旁的两根大旗杆,庙的标志。旗杆上的木框框,不是摆设,是很多乌鸦的窝巢。每到季节性的傍晚,成百上千的乌鸦从你头顶上飞过,气势相当惊人。只要有一只低飞,那“呼”地一声,也着实惊人。此景永远不在了。
说起旗杆,上面有个葫芦形的顶子,是用锡做的。曾有三五块锡因为天热而有锡水水滴落。旗杆旁建四四方方的一大戏台,是为庙谢神用。戏台正北方,是城隍庙正门,两扇朱红漆的大门,常年紧闭,不是节日是不开放的。
那时,小孩无大人带都不敢进入。尤其是在清明节,各家长严格看好自家的孩子,不但不许乱跑乱动,更不许乱说,以怕触撞城隍。据说,王营是都城隍,其他城隍归其管辖。所以,在清明大节日,不但信徒众多,而且小商小贩也视为做生意的大好时机。
在清明前,就有各种敬神事项频繁推出。如城隍出大驾(就是用八人大轿将泥身神像,抬出巡视一下)。从王营到西坝,凡必经之路,家家都设有香案。锣鼓声、大号声和唢呐声,响彻四方,震耳欲聋。贫富人家一个样,都率家中老小,跪地迎送,非常庄重肃穆。供香案上,除香烛、清水,富裕点的人家,还供些茶食。不外是糕、果、糖芝麻饼之类。
我有两次,随母亲跪拜迎送的呢。我家大门是朝东,南北路是大道呢。大人早就讲了,不许说杂话,也不能乱看。
可我好奇,当大驾来到时,偷眼向南望去。先是锣鼓铜镲开道,后面跟着现在电视剧里皇上巡视一般的队伍,拖根随尾都是一色红色着装。在八人大轿中,端坐着一位城隍爷,还有大红绣花盖伞。撑伞人紧盯着大轿。后面鬼庙会,要从右边走,边走边耍,声声作响咯啷啷…一色红衣红头巾,跟着两差人服饰押解一头长白发的,铁锁牵着恐怖吓人。紧跟信众,蜂湧而至,看此场景,实在令人不安心。
在欢庆的人群中,踩高跷子的、玩花船 的、人抬阁的、赶驴的、推花车的等等各式杂耍跟着前行。另外零零星星的人,跟着在后,就不多了。剩下的人,烧香还愿、走亲访友、赶庙会,各个场点随处可见。测字算命、打卦、黄雀抽签、卖小吃的多是卖炒米糖。小孩玩具有木刀、木枪、木碗。最玩的是手推的小风车。满街是人。尤其是我家门前到庙大门,摊子接摊子,各不相同。卖花的,不是鲜花,是绒花娟花。妇女赶来庙会,不但看热闹,还买用品用具,如剪子、刀等。
在平常是看不到庙会的,此时才能饱眼福。我最爱看的是耍猴的。铜锣一敲,耍猴的一吆喝,立马围上一大圈观众。原来庙西空地上,有打拳卖艺的,有二鬼打架的,有玩曲拐驴子(木偶戏)的,都是一簇簇,围得挤不进人。这些场点,不时地暴发出掌声喝彩声。人们都喜爱这个庙会。
庙门虽然不远。从远看,能看到二个大铁香炉。靠大殿的是宝塔式的。偏南一米外的长宽约一米,有耳把。火光熊熊香火烧得烟有时呛人。焚香的人,没有不磕头的。我只能在外向里看。因为家里大人一再交待:小孩不许进入庙内。
我小时候,跑得最远的地方是到南圩堤。东面是孙家烧饼店,黑牛老家。北面是马王庙、杨家砖井。西到粮食街,最远的是四美酱园。这些地方,还都是跟着妈妈走。
庙会热闹,哥哥都是搀着我,我也不敢撒手。
庙会一般持续三、四天,低潮是当天出驾到西坝巡视后。傍晚时仍安放在神座上。
还想起有放洋片的,唱着叫着,实际上就是一些画片,用放大镜在面前的小孔观看,能有30—40张的样子,给我带来快乐,现在想起来都很好笑。。
小时候家人不让孩子外出,编出许多吓唬孩子的话。如老拐子,还有鬼怪、老叽嘠子…等。因此,我从小就在头脑中套上了无形的枷锁与束缚。
总记得,我小时候有一顶小红帽,毡子的,像巴拿马帽子一样,春天、秋天和冬天都戴着。
周家铁匠铺
我尤其爱看近邻周铁匠家打铁,一站就是很长时间。打铁一般都是二、三人。首先要有拉风箱的。
砖砌的都是用油泥(粘土)的。有个烟囱,用的都是煤炭。风箱一拉,“气…达…气…达”地声响,那炉中的火,就慢慢地旺了起来,彤红彤红的。周大爷就拿起铁箝子,一手拿小锤,,把火红的铁件夹到一个铁墩子上。他小锤一敲打,徒弟们就抡起大锤,“叮咚叮咚”地锤打那个物件。原来粗的物件,先成扁形,又为长形…。就这样,经过多次锤打,成为刀,或是锄头。
他们打铁,不穿褂子,赤着膊,汗流浃背的。
我还喜欢看刀的焠火。铁件是红红是,朝水盆里一放,你可听到“嗞嗞”的声响,同时,散发出铁所特有的气味。
周大妈就喜欢我,直到我四、五十岁的时候,见到我还亲切地喊我小名。我说的这些事,只是说明那时人与人的近邻关系非常亲密。
凡是打铁的,都称铁匠铺。做什么工,就叫什么匠。如瓦匠、木匠、银匠、漆匠。凡是做手艺的,都具备一定的技术,所以都美名为“匠”。
河边抬水
记得深刻的是随母亲和姐姐到河边抬水。一根扁担,用绳子,拴住大圆桶,。圆桶有个把子,系根绳,套在扁担上。前面走的是小孩,后边是长辈或哥哥姐姐。因为日间无水,总在晚饭后。第一次跟到黄河边,在依稀的色下,从家门向南,有一道堤,爬上堤再下堤,有三层楼高。斜坡向下走,有一住户叫魏百元,又有一沙城(人名),才见到星星点点的小塘。找到一个大一些的、深一些的水塘(没有一人深),拿出舀水的工具(葫芦被锯成成两瓣,叫瓢),一瓢一瓢地撇起水来。撇了一下,要等一下,再撇一下。就这样,一桶一桶将盛满水桶。如此费了不少力与时间。水抬到家后,还要移、挪,拎起来倒在水缸里。
这水浑浊,有泥等杂质,要用明矾投入少许再用擀面杖搅拌,慢慢的实现清浊分离谢。浑浊的沉在缸底下,其上才是可饮用的水。
家家都有一个瓦罐子,在烧好饭后,将盛了水的瓦罐放在锅腔下面,用烧过火的燃料为瓦罐加温。洗脸时,用的是粗布,或一种叫高丽巾。先是当家洗,然后挨个来,从小到大的,妈妈总是在最后用这个水洗脸,再淘淘毛巾。我到三十岁时,家中用水,还是这个样子。
这样的生活,可能成为我永久的记忆。希望后人知晓一点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
外公与我们陈家
有趣的记忆是我外公(都称婆爹),在悦来开一小杂货店。有时到我们家来,都是骑着毛驴来的。驴脖子上都套一大串铜铃铛,驴行走时都是“哐当哐当”地响 。只要听到驴铃声响,姐妹几个都会跑出来迎接。但有时失望,不是外公,只得怏怏回房里去。
我们陈门也是一大户人家,我的祖母姓陈,曾祖父只此一女,也可以说是娇生惯养。而且家道也不错,因为家中在盐河大渡口(西坝)有渡船,还有些田地。曾祖老马号人(现同兴队),兄弟五人。可能是老二,招在陈家,改姓陈。育有两子一女。父亲是老二,有大伯、小姑。我戴的红帽子,就是小姑从江南常熟带来的。
大伯家有堂兄两人,小姑嫁给西坝解家。大堂兄四十未到就因病去世。育有两位大侄,大的振国,因糖尿病眼瞎几年。二侄,二十年前,因车祸已早往西土。二堂兄耀友落户蒋坝,亲子振华,在淮。振彪在蒋坝。
据母亲讲,她是补房。父原配杜氏,也是大户人家。因服大烟土逝世。两家因此闹得满城风雨。
祖母慈眉善目。传说,小时有婶和乳母养育,中年有丫鬟、老妈,从没做过针线活,更不要说下厨房了。从我记事起,一日三餐,都是端到房内。两房轮流瞻养。每日晚上,母亲都要带我和姐妹几个到祖母面前坐一会,叫走才回自屋休息,日日如此,从未间断。
祖屋有瓦房三间。厨房四间,是草苫的。前大门一排五房,租给张姓多年。后来知道大房典给人家。我们先是住跨屋(即厢房)大的五大间的南两间。在大门外有一个依屋搭建的凉棚,不漏雨水,东南侧均通风。我出生时,祖父早已离世。
门蓬的柱子,是留给有马有驴的客人来拴牲口用的。我只记得伯父一辈子爱玩蟋蟀。因为西坝大渡口有船,雇有船工。每到秋收时,到农村挨家挨户收些粮食、花生、山芋等,地里种的都有。尽义务的是在过渡船上不收钱。但南来北往做生意的买卖人,都要付渡船钱。所以,大伯家生活比我们家好。因为我父亲是一辈子的估衣店员。这个店,是在清江小水门内观音寺巷义成估衣店。从学徒时就在这家店的。工资,那时叫“薪俸”,每月能拿几元。母亲在家,除了家务,那时此地织布才开始兴起,手摇月子(工具名称,如同现在筒子)微薄收入贴补家用。
我有两个姐姐,从小就帮着劳作。
说起来,我已是百岁老人了。我现在仍可以看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写点文字、弹弹琴、下下棋。每天还要喝点老酒。
这幸福的晚年生活是怎么来的?,一是党的阳光照耀,二是子孙孝道,三是我的心态好。
啰啰嗦嗦,想起来一点就说一点。以后有了新回忆,再聊吧!
陈耀荣,1925年出生,原淮阴织布厂中层干部退休。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