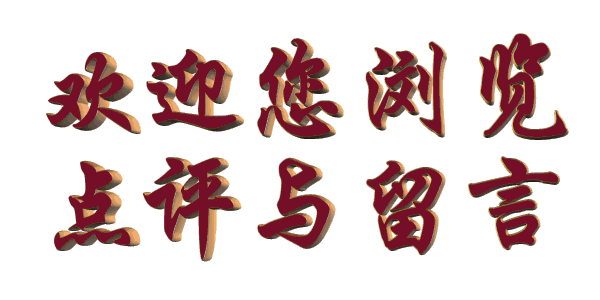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小说《泥土的芳香》第一部
作者:恩清
雷场长答:“吃公家的,不行;可是吃我的,行,咱自个掏钱。”
卢父憨憨一笑。
饭菜备齐了,雷场长同食堂管理员道别后招呼大伙入坐。他面南背北,与卢父相对;卢伟面东背西,与雷家的姑娘相对。她高跟鞋,喇叭裤,头发爆炸,一副歌手张蔷的模样。卢伟认为这不是漂亮,而是时髦。
卢伟问候她,“姐姐,你好,认识你,我很高兴。”
姑娘回复他,“老乡,你好,认识你,我也很高兴。”
什么?老乡!什么意思?笑我是一个农民吗?卢伟心中一阵酸痛,脸上火辣辣的,他低下了头,不敢正眼瞧她。
雷父一声招呼,卢父一声回应,大伙动起了筷子。
一杯酒下肚。
卢父问:“这女子叫啥?多大?排行老几?”
雷父答:“叫文娟,文化的文,口月娟的娟。十五岁,比你家小子大两个月,排行老大。她呀,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扮,就是不知道学习。这次中考没考上,分到场里的青年连了。干什么呢?修路,修场部到省城的大道。”
卢父说:“这么小,你就让她干重活?为什么不帮她找一份好一点的工作呢?你这老子是怎么当的?你这领导又是怎么当的?”
“大哥呀,可不敢胡说。”雷父答:“她不好好学习,由她;她不好好劳动,由不得她,领导干部的子女咋的?领导干部的子女就是要带头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卢父知道惹事了,吓得有些哆嗦,他不敢吱声了。
又一杯酒下肚。
雷父举着筷子指着卢伟问:“大哥,你这小子如何?”
卢父答:“学习成绩还行,中考第三名,可就是思想有问题,他瞧不起农民。”
“这不是孩子的事情,是大人的问题。”雷父道:“过去,为了土地,咱们前赴后继,先是赶走了洋人,后是打倒了地主,一心一意地跟着党走。可是有了土地,属于个人时,还行;属于集体时,怎么就不行呢?属于个人时,人人热爱土地,勤劳致富;属于集体时,人人讨厌土地,偷奸耍滑,这说明‘公’与‘私’不是简单的谁消灭谁的问题,而是一对辩证的矛盾体,小平同志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
卢父问:“你说的我不明白,也不想动脑子揣摩,你就告诉我,‘承包到户’好,还是不好?”
雷父反问:“你说呢?”
卢父答:“说好吗,是能够填饱肚子,可走的是资本主义的道路;说不好吗,是不能够填饱肚子,可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道路。”
雷父道:“不对,土地是国家的,可以国营,也可以私营,只要能够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就是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卢父问:“你说的,我好像明白,又好像不太明白。干脆,你告诉我吧,‘承包到户’我是参加,还是不参加?”
雷父肯定地说:“参加,一定要参加。”
卢父坚定地说:“那好,我就参加,积极地参加,承包村子里的土地,自己先富起来,然后再领着乡亲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雷父举起杯子,大声喝道:“好,为自己先富起来然后领着乡亲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干杯!”
又一杯酒下肚。
卢父道:“兄弟呀,你家是南方人,喜欢吃大米,再说你家的两个小子也长大了,正是吃饭的时候,我带了四十公斤大米,送你,请你收下。”
雷父道:“大哥呀,你家是北方人,喜欢吃白面,再说你家的两个小子也长大了,也是吃饭的时候,我拿出六十公斤白面,换你,请你收下。”
卢父道:“我说了,送你。”
雷父道:“我说了,换你。”
卢父道:“那就一公斤大米换一公斤白面。”
雷父道:“什么?老规矩,一公斤大米换一公斤半白面,否则不能成交。”
卢父道:“那好,这次我听你的。为了不跟我们争地,你们跑到沙漠边种地;为了不跟我们争水,你们不种水稻,让我们种,还让我们用大米多换你们的白面,我们这些地方的老乡呀,惭愧呀,愧对你们这些兵团的战士们呀。”
雷父道:“大家都穷,只能换,不能送,送不起呀,谁送谁挨饿呀。等着吧,等到今后大家都富裕了,我们就能够你送我和我送你了。”
本届高中为两年制,招八个班,四选一,第二年起分科,两个文科班,六个理科班,在“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里,这样的选择并不奇怪。卢伟选择了理科,功课繁忙和压力沉重是他生活中的全部内容。初中时,他讨厌农民,对农工还有那么一点好感,而高中时,他就连这一点好感也荡然无存了。他厌恶农民,讨厌农工,原因是他们手中拥有土地,所以,他讨厌土地,而他摆脱土地的唯一途径就是考上大学,以便将来有机会做一名没有土地且令人羡慕的城里人。
1983年7月,卢伟十七岁,在县一中高中毕业并参加了高考。
离校时,他把行李放在自行车的后架上,把零碎放入了脸盆塞进了网兜挂在自行车的前把上,他要做离别时的畅游。
先是城区,一排排绿色的树木,一栋栋破旧的院落,少量的楼房,除了医院、影院、学校和公园外,还夹杂着一些工厂。看,面粉厂,十几万人靠它;榨油厂,十几万人想它;铁锅厂,十几万人用它;铁锁厂,十几万人要它,向外扩展,就不是十几万,而是几十万,几百万的问题,所以小城的日子还算不错。卢伟很羡慕在工厂做工的农家子弟,除月工资外,每月还能掂着一包茶叶、一袋白糖和几条肥皂回家以及冬天里的一车煤炭,光宗耀祖,令人眼馋,加上每天下午都能享用的职工浴室,每个周末都能光顾的职工影院。这地方,他只去过一回,是哥哥带他去的,洗了一回澡,很神奇,触动了他的神经,他听到了隔壁浴女的欢笑声……还看了一场电影,《生死恋》,那女的,长相好,声音甜……后是郊区,远处是山,近处是田,麦田里,一层层的麦浪,在麦浪地包裹下,农民显得是那样的渺小,一个一个的黑点而已……
他骑车奔向自家的麦田,远远就看见站在田里的几个人,个矮背驼的是父亲,42岁,可头发和胡须已经开始发白;体瘦脸黄的是母亲,40岁,可额头和眼角已经出现了皱纹;卢伟的心中一阵酸痛。哥哥让他感到骄傲,身高体壮,可除了脸,其它地方找不到父母的影子,22岁,大自己五岁,在榨油厂做卡车司机。他确信父亲没有那个本事,猜想一定是文娟的父亲帮了大忙,以至于哥哥能够在“以厂为家”的口号下而变得公私不明的工厂里拉上几车便宜的油渣做肥料,避免了父母天不亮就赶在乡亲们之前抢占旱厕,实现在一片臭烘烘的土地上唯有他家的土地还散发着一股浓浓的菜籽油的芳香。姐姐让他感到自豪,面目清秀,身材苗条,可除了瘦,其它地方与父母亲也无太大的关系,20岁,大自己三岁,在新疆农业大学读本科,已四年,还差一年。这里既没有父亲的本事,也没有雷叔的帮助,全靠自己的努力,其结果震惊了整个水磨村。
看到了他,家人先是惊奇,后是喜悦。父亲点头,母亲微笑,哥哥披着蓝色的工作衣走过来帮他把车子架稳,姐姐穿了一身蓝色的牛仔装急切地询问着他高考的结果。
姐姐问:“考的如何?”
卢伟答:“感觉良好。”
姐姐道:“那就好。”
卢伟道:“即使考上了,可是能去吗?哥哥走了,我也走了,家里还剩下了谁?谁能帮爸爸妈妈下地干活?”
姐姐答:“我!”
“你?”卢伟感到惊奇,他问:“姐,你在开玩笑吗?”
“我不跟你开玩笑。”姐姐答:“瞧,哥哥五大三粗的,爸妈都舍不得让他下地干活,被弄到工厂里光宗耀祖去了,更何况你,卢家未来的大学生。”
卢伟不语,他看一眼父亲,又看一眼母亲。
父亲建议道:“既然一家人到齐了,那就在地头上开个家庭会议吧。”
母亲点头道:“对,把家里的事,理一理,顺一顺。”
父亲道:“先说老小卢伟的事情,这没什么可说的,全家就是砸锅卖铁也要供他上大学,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脸的问题。”
大家表示赞同。
卢伟不语。
父亲道:“再说老大卢宏的事,我认为他谈的那个对象呀,好呀。父母同我们一样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同卢宏一样也是工厂的工人,不就是壮实了点吗,可是壮实了点好呀,能干呀。”
姐姐问:“哥,你喜不喜欢那个胖乎乎的姑娘?”
哥哥答:“她喜欢我。”
姐姐问:“我是问你,你喜不喜欢她?”
哥哥低头道:“我不知道。”
姐姐问:“那你喜不喜欢像我这样苗条的姑娘?”
哥哥低头道:“我不知道。”
姐姐急了,问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父亲问:“苗条能当饭吃吗?”
母亲道:“壮一些好,能干。”
姐姐道:“唉,还真是可悲,好了,我没意见了。”
父亲又道:“再说老二卢娴的事情,她的那个对象呀,父母是农大的教授,同我们不是一路人。虽说他同卢娴一样,也是农大的学生,可是瘦了吧唧的,还戴副眼镜,这,这能过日子吗?他还给咱们家制定了什么发展计划,这靠谱吗?”
“靠不靠谱,不能用嘴巴说话,要用事实说话。”姐姐掏出一张纸,一边看一边说:“咱们家小麦50亩,亩产300—500公斤,平均400公斤,300公斤白面,每公斤0.4元,每月120元,每年1440元;父母每月40公斤,每年480公斤,每年消费192元,每年还剩下1248元。虽说蔬菜能够自给,鸡鸭鹅、牛羊猪和鸡蛋、牛奶能自产,可种子、化肥、农药、水……要钱;雇工,要钱。爸妈明智,没让哥哥当农民,当了工人,每月86.5元的工资,每年1048元的收入,比种地强;再说找了一个工厂里的儿媳妇,不说壮实,也不说能干,就是每月86.5元的工资,每年1048元的收入,也比种地强。所以,小弟呀,不用担心,安安心心地读你的书,咱们家不会爆发经济危机。”
父母点头。
姐姐问:“可是谁来种地呢?”
父母不明白。
“爸妈算得精,女儿不能白给,招个上门女婿。王维嘉不行,个头小,体质弱,还戴副眼镜,干不了重活;猪八戒行,虽然能吃,可是能干,不就是丑了一点吗?”
父母疑惑。
姐姐说:“可我不找猪八戒,我找王维嘉,他父母是农大的教授,他是农大的研究生,研究西瓜,什么‘红优二号’、‘P2’和‘金鹿’,你们见过吗?没有;你们听说过吗?没有。这些西瓜,在北疆甘甜,在华北和中原可口,所以呀,王维嘉父母的知识值钱,王维嘉的西瓜值钱。王维嘉说:阜康的土地好,粘性适当,沙性适中,适合培育他们的西瓜种子,亩产在60至80公斤,平均在70公斤,每公斤能卖100元,每亩就是7000元,10亩就是70000元,50亩就是350000元,哇,天文数字!所以呀,我找王维嘉,做王家的儿媳妇,不仅在省城研究西瓜,做科学家,而且在阜康县种植西瓜,做农民。卢家的儿子们,愿到哪玩就到哪玩,卢家的姑娘来种地。爸妈,可以坐着小轿车买米,买菜;坐着飞机,观光,旅游;还可以出国去,看看日本的小鬼子,望望英国的老毛子,问一下他们过去为啥老是欺负咱?所以‘四眼’比‘八戒’强,不仅能够让咱们家致富,而且还能够让咱们村致富。”
爸爸妈妈听傻了,哥哥弟弟像是在听天书……
卢伟考取了南方工学院,与南方文学院只有一墙之隔,同属南方大学。
第一天,他就沉寂在知识的海洋中。以分子为起点,分子的重组是化学的,而宏观是物理的,微观也是物理的,这两个世界是何等的相似,以至于宇宙和核能都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是闪亮的一点,也是最可怕的一刹那。他坚信,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同时也是发展和变化的。他明白,牛顿的第一定律,揭示的是物体的内因;牛顿的第二定律,揭示的是物体的外因;牛顿的第三定律,揭示了物体内因与外因的关系。他很清楚在时间的坐标系中位置变化显示着速度,速度的变化显示着加速度,从而引出了微积分……
下午下课的时候,卢伟兴奋不已,爬上了楼顶,想吸一口新鲜的空气,看一眼美丽的城市,可是他却被眼前的景象给震住了。对面,同样高度,文学院的楼顶上,有一位姑娘,白裙,长发,一张迷人的面孔,一段迷人的身躯,很清晰,很靓丽,说不出来的那种美,特别是在离别时,她的一个甩头,一个转身,啊,长发飘逸……
卢伟心醉了,抵抗不住诱惑,每天下午都来。有时,能看见那张脸,那个甩头,那个转身;有时,看不见,他只好在脑子里重现那一张脸,那一个甩头,那一个转身……
一次,在同年级的一场篮球赛中,在篮球馆的座位上,卢伟看见了那个女孩。虽然只一墙之隔,可她却不远万里从文学院赶到了工学院,身边还带着一个女伴。卢伟的内心被点燃了,他跳起来截住篮球,冲到对门,轻身跃起。在空中,他右手先是高高地举着篮球,随后放下,篮球经腰间没入后背,又从后背冲出左肩,他左手接过篮球,轻轻地放入篮筐,双脚重重地落在地上……哇塞,帅呆了!哗啦啦……一阵惊奇,一阵欢呼,她和她的女伴也在拍手,卢伟心花怒放。
“喂,肖阳——肖阳——”一个女声,她回过头去,她的女伴也回过头去,她俩一起向那个女孩招手,一起离身向那个女孩奔去,一起与那个女孩消失在了人群中……卢伟恨那个女孩,是她叫走了她;同时,他也爱那个女孩,是她告诉了他恋人的名字:肖阳,啊,美,一个同本人一样美的名字。
“肖阳……肖阳……”卢伟挂在了嘴边,记在了心里。
通过打听,卢伟掌握了她的全部信息。肖阳,女,汉族,山东烟台人,1966年5月生,南方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系83级学生,母亲小学教员,父亲中学校长,书香门第。所以,当卢伟再次来到楼顶,再次看到那一张脸,那一个甩头,那一个转身时,卢伟感觉他离她更近了。
不能再等了,将近四年,卢伟与她虽然有过无数温馨相会,却有着假期中难以忍受的七次分离,第八次也许是永久的分离。卢伟不甘心,于是写信于她:“肖阳同学,你好!虽近在咫尺,但一墙之隔却有万里之遥。汝美不胜收,余不能拔,不甘,愿越墙与之相会?”
一星期后,卢伟收到了她的回信:“汝不为张生,余不为崔莺莺,翻墙头!虽为君子所想?却不为淑女所愿?星期日上午十二时遣红娘与汝于城东广场大庭广众之下相见。”
红娘?什么意思?还用得上红娘?卢伟顾不上细想,早早地就来到城东广场。雨后的天气凉爽,卢伟心急如焚,焦躁不安,在广场上不停地转圈。她来了,终于来了,白裙,长发,像瀑布那样垂下。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她微笑地对卢伟说:“虽然这是我们第一次正式相见,可是在楼顶上我们可是老相识了。”
“是的,”卢伟激动不已,“我们几乎天天相见。”
她说:“书,你读得不错。”
卢伟一阵狂喜,心想,她关注着自己。
她说:“球,你打得不错。”
卢伟一阵陶醉,心想,她欣赏着自己。
她问:“你认识肖阳?”
明知故问,卢伟心想,可表面上点点头,接着有些得意忘形。
她又问:“你默默地恋了她四年?”
多此一举,卢伟心想,可表面上点点头,接着有些忘乎所以。
“可是她说了,她不接受你。”她解释道:“她有男朋友了,在山东烟台,是一位警察,一位小小的警察。”
听到这,卢伟心中一阵酸痛,泪水夺眶而出。
“肖……阳……同学,我尊重你和你的选择……”
她说:“我会转告她的。”
卢伟说:“不用转告,只要你愿意就行。”
她疑惑,“什么意思?”
卢伟把话挑明,“你不就是肖阳吗?”
“我?肖阳?哈哈哈,哈哈哈……”过了好一会,她停下来,否定道:“不,你弄错了,我不是肖阳。”
卢伟疑惑地问道:“你不是肖阳,那你是?”
她答:“我叫程虹,工程的程,彩虹的虹,肖阳的同班同学,是她叫我来的。”
啊,还真是红娘!卢伟先是一阵糊涂,后是一阵惊喜,好像黑暗中找到了光明,他说:“错了,错了……我喜欢的是你。”
她感到吃惊。
卢伟感到尴尬。
“真快,”她说:“变得可真快。”
“什么?”卢伟不明白,他问:“你说什么?”
“我说,”她气急了,大声喊道:“我说你变得可真快!”
“真的,”卢伟急了,低声下气地说道:“真的,我喜欢的是你。”
“我见过无耻的,可是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无耻的。”她气愤至极,“四年了,我原以为你是一条好汉,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无赖,一个流氓。好了,再见!不,我们永不相见!”
卢伟呆住了,呆呆地站在原地,望着她远去,望着她消失在了人群中……
啊,四年,整整的四年,虽然有着漫长的量变过程,可是质变却仅仅进行了几秒钟,而且不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卢伟恨自己,不是没有掌握好这个变化,而是压根他就不知道会有这个变化。
1987年8月10日至14日,整整五天,卢伟垂头丧气,乘火车从江南回到了乌鲁木齐,又乘班车从乌鲁木齐市回到了阜康县,回到了水磨村,他倒在床上呼呼大睡。
父母来了,他不理会。
哥嫂来了,他也不理会。
姐姐和姐夫来了,他同样不理会。
姐夫借故出去,姐姐坐到他的身边,面对着他的脊背,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他不回答。
姐姐不仅敏感而且尖锐,她说:“每个假期,你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我就知道你恋爱了,可是今天,见你失魂落魄的样子,我又知道,你失恋了。”
姐姐点到了卢伟的要害,他翻过身,吃惊地望着姐姐。
“不幸被我言中了吧。”姐姐问:“你打算怎么办?”
他摇摇头。
“就此消沉下去吗?”姐姐问:“你不打算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的人生吗?”
他仍摇头。
“那就忘掉过去,展望未来吧。”姐姐说:“不过,在此之前你应该先了解一下家里的变化。”
他疑惑地问道:“家里?变化?家里有什么变化?”
姐姐高兴地答道:“翻天覆地的变化。”
他不知声,抬头望着姐姐。
姐姐说:“你连家里的变化都不想知道,可见你的心从未在家里停留过。”
“那就告诉我吧,”他一点也不着急,“我们家里的变化。”
姐姐答:“如今,爸妈承包的土地越来越多,我和你姐夫除了研究理论,就是回家种地。哥嫂也辞去了工作,回家种地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回家种地……”
“打住,”他打断了姐姐,“我可不回家种地,种地光荣吗?”
姐姐答:“光荣,前途似锦。你不知道,在你上大学的这四年里,咱家种了四年的西瓜种子。第一年,10亩,亩产70公斤,合同价每公斤100元,产值7万元,利润3.5万元,咱家是全村的第一个万元户。第二年,50亩,亩产72公斤,合同价每公斤105元,产值37.8万元,利润18.9万元。第三年,100亩,亩产75公斤,合同价每公斤110元,产值82.5万元,利润41.2万元。第四年,也就是今年,200亩,亩产80公斤,合同价每公斤115元,产值184万元,利润92万元。第五年呀,也就是明年,400亩,亩产按80公斤,合同价按每公斤115元,产值368万元,利润184万元,咱家是全村的第一个百万富翁。”
“这么多钱?”他忘记了痛苦,起身坐到床边,有些吃惊,问道:“姐,这是真的吗?”
“真的,”姐姐笑了,答道:“姐不骗你。”
他说:“万元户?百万富翁?这些,我好像在报纸、广播和电视里听过。”
姐姐道:“不是报纸,也不是广播,更不是电视,而是阜康的水磨村,在爷爷开垦过的土地上。”
他问:“你要收回爷爷的土地吗?”
姐姐答:“做梦!党不答应,国家不答应,人民也不答应。”
他问:“为什么?”
姐姐答:“为什么?为什么?你脑子有病?想复辟资本主义?旧社会,是爷爷的土地;可新社会,是国家的土地,是人民的土地,咱家只有承包的权利。现在,党的富民政策好,让大家承包土地,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再领着大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他问:“是领着全村的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吗?”
姐姐答:“对。”
他问:“靠西瓜种子吗?”
姐姐答:“不全是,还有石油、煤炭、天然气、有色金属、大米、小麦、棉花、甜菜、猪、马、牛、羊、马鹿、蟠桃……王母娘娘和王母娘娘的天池旅游业,靠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方针。”
他说:“好,非常好!可是,无论你说得再多,说得再好,我也不回来种地,做农民。我要进城,进城,做城里人,做一个让全村人都羡慕的城里人!”
姐姐前后矛盾,她说:“我不是主张你回到农村,而是觉得你离不开农村,离不开土地。还记得那个算命先生吗?他说,离开了土地,你将一事无成。”
“胡说八道,他就是一个骗子!”卢伟说:“我决定了,走自己的路。”

作者简介:
恩清,土木作家。新疆与兵团作家协会会员、乌鲁木齐市作家协会理事、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作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