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周邦文简介:安徽合肥人,大学本科学历,在职研究生肄业。现年69岁,1972年冬入伍,历任航空兵某师歼击机机械师,全军夏北浩式机械师,师机务处参谋,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参谋,1982年初转业到广州市公安局,后随建制转入广东省某保密单位,历任科长、处长,全国内部发行某杂志副总编辑,省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副秘书长。退休后创立东莞市瑞邦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公司作为中国对外服务工作行业协会理事,先后为近千家外企提供综合服务,为东莞地区的外企发展、和谐用工作出了积极贡献,诚信、专业受到中外企业的广泛好评。多年来,在工作之余,系统学习了汉语言文学专业,并在实践中领会精髓,感悟人生,体察社会,勤奋笔耕,陆续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报告文学近百万字。其中散文《弯弯的小河静静的流》获省一等奖,一批报告文学作品获某杂志全国评比一等奖。1998年10月被吸收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1999年1月被吸收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周邦文在文学创作中注重有感而发,不事雕凿,尽力使用细腻的笔触,质朴的语言,自然传递真情挚感,让人读起来容易产生共鸣,自然有一种亲和力。
周邦文虽已年近七十,却时时关注着国家的前途命运,特别是每每看到军队建设、国防力量取得新的进步,他都会像孩子一样欣喜如狂。他常说,曾为军人,生命中军魂长存,爱国报国,不改初心。

迷途知返
作者:周邦文
人,也只有通过欢喜和苦痛,才学会什么应追求和什么应避免 ——歌德。
一
1990年1月15日中午12点35分。
一架波音 737 国际客机平稳地降落在G市白云机场。发动机如释重负般的发出一阵轰鸣,推动着庞大沉重的机体滑向停机坪。
这是一架国际班机。机上走下的大多是外国人,他们似乎忘却了旅途的疲惫,为终于踏上东方这块神秘的黄土地而兴奋不已,谈笑风生。
但是,其中一位四十岁上下的中国男士,却好像心事重重。他眼里闪现出几许追悔、几许惭愧,还有几许盼见亲人的急切和柔情。
他从另一个国家回来,永远都不会忘记刚刚结束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饱含着他的酸甜苦辣。
二
他叫尤启仁(化名),才38岁,原来是一家家用电器厂的副厂长。
他才38岁,属于比较成熟且年富力强的那一个年龄层次。他正处在人生的黄金时节,生活的航船张满了风帆。
在同龄人中,他是一个幸运者,生活给了他太多的厚爱。
1974年,当大批当年被送到海南岛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学生哥学生妹为摆脱社会错位造成的窘迫环境而通关节托人情寻找回城之路的时候,尤启仁被推荐为G市轻工学校的工农兵学员。他决心把握住这个机会,把这作为个人奋斗的阶梯。
1977年夏,尤启仁以优异成绩领取了中专毕业证书。凭着这张毕业证书,尤启仁轻而易举地跳出了“农门”。正当大批工农兵大学生为安排工作挠头的时候,一家经济效益很不错的国营化工厂向他敞开了大门。工厂虽不大,但它有一个在当时很让人羡慕的“国营”招牌。尤启仁如鱼得水,有声有色的当上了该厂的业务员,拉开了个人奋斗的序幕。
四载寒暑,尤启仁业务上进步很快,多次出色的完成了厂里交给的任务,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好评。为此,他连续两年被评为G市轻工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他并没有飘飘然,也没有喜形于色,只是忍不住会在茶余饭后自鸣得意地对朋友说,这不过是他初露头角罢了,用不着大惊小怪,等着瞧吧,好戏还在后头。
他要朋友们等着瞧的,不是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而是所谓个人奋斗的升级。
尤启仁的认知世界里有一个误区,那就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社会环境像水源,像土壤,鱼虾无法在红潮里成活,庄稼难在盐碱地里生长。人和社会互相依存,互相成就,互为对象,互为因果。有时候偶然只是偶然,机缘不是必然。假如你把机缘、偶然当成当然、必然并且昏昏然,倒霉早晚将成必然。这就是成熟的稻穗总是低着头的道理。尤启仁的心理已经处于“亚健康”状态,急需调整。
时值80年代的第二个春天,改革开放的春风吹绿神州大地,迎来万紫千红,大批外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在G市和珠江三角洲一带。G市充分运用改革开放的政策和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经济建设在和煦的春风中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而尤启仁所在的那家小化工厂,却因为经营不善反倒显得有些不景气。他决定趁此机会跳出去,寻找一个更高层次的个人奋斗的起点。
1982年冬,尤启仁又如愿以偿,“活动”到一家外商投资、设备先进、待遇优厚的家用电器厂。离开化工厂的那天,党支部书记何铭找尤启仁谈了一次话。
何书记语重心长地说:“小尤同志,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要跳槽我不拦你,希望你能不忘初衷。”眼见得尤启仁不甚明了的样子,何书记继续点明:“初衷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真实存在于每个人心中的一盏灯。这盏灯是明是暗,决定了一个人的属性和前程。希望你在追逐事业的同时,保持追求真善美的热情,担起报效国家的责任,发扬服务社会的精神。”
“不算什么谈话,权当朋友的临别赠言吧。我们共勉。”何书记一手拉住尤启仁的手,一手拍着尤启仁的肩膀,似乎还有很多话要说,但是欲言又止。这位德高望重的基层党支部书记阅人无数,他是在担心着什么。
尤启仁到了家电厂工作一如既往的勤奋,凭着中专文化基础,技术上手也很快。尤启仁心里憋着一股劲,平时很少说话,别人一下子看不透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没有人事是非,大家都能待见,很快便出人头地被作为培养对象送到工学院进修电子专业。这无疑是让尤启仁的事业进入了快车道。
那时候的民营企业虽然一般都有国企的背景,但人事任免已经放开了诸多禁锢。重视人才,重视文凭,不再按资排辈,有能力、有文凭的赶上了好时候,很多人被破格任用。
1988年2月,对尤启仁来说,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被破格提拔为副厂长,并搬进了一套两房一厅的住房。这在当时住房紧张的G市实在是羡煞旁人。
当尤启仁西装革履端坐在整洁、明亮、宽敞的副厂长办公室审批文件,会见客商的时候,着实让他有些踌躇满志。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凭自己的才干得来的,顺理成章。他相信“个人价值”说,他觉得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实现自我价值,生活才有意义。至于眼前的这一切,都不过是新的阶梯。对于他来说,所谓“成功”必须不断更新“标的”。
家电厂生意非常红火,拉货的车辆在厂门口排起了长龙,购货商们通过各种渠道托关系找门路希望能够优先批货。当然,这些人除了托有关系,还会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有的干脆“塞红包”。以前在化工厂没有见过这些,尤启仁有点眼花缭乱。尤启仁知道,这些人既然找上门来,拿不到货不会轻易离开,产品卖给谁不是卖?不如顺水推舟,既得实惠,又买人情。一来二去反倒成了常态。
夜深人静的时候,尤启仁想想就暗自得意。他觉得当知青那会吃的苦总算有了回报。这些都是他应得的。他发展的太过顺利,加上认知上的缺陷,摆不正个人和社会、群体的关系。他觉得一切进步都是因为自己卓越的能力。这种过分的自信使得他只相信自己,不相信政策,不相信组织,甚至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使得他听不进不同意见,日积月累地和领导也产生了隔阂,在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的时侯怨气日盛。
有人检举他有经济问题,组织上进行例行审查,他说这是整人;
报评经济师职称没能通过,他抱怨国内不重视人才;
申请出国留学,条件所限,拿不到签证,他认为是领导不近人情……
一切的一切,让他感到压抑,认为是别人阻碍了他的前程,西方的所谓自由对他的吸引力越来越强烈。小小家电厂的水太浅了,他下决心要到国外去施展才华,那里才是他尤启仁的天堂。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不惧铤而走险。
机会终于来了。
1989年10月上旬,尤启仁趁着和同事到香港洽谈生意的机会,施展手腕,拿到了赴澳大利亚的旅游签证。
他带着无限的希冀,抛弃了生养他的祖国,登上了一架国泰航空班机,踏上了迷途。
三
澳大利亚悉尼市。
神情沮丧的尤启仁漫无目标地在大街上踌踌徘徊。一想到来到悉尼的遭遇就有些扫兴。
到达悉尼市的第二天,定居在这里的远房堂哥便驾车带他游览了悉尼市容。堂哥告诉他,作为澳大利亚全国经济、文化、交通、旅游中心和第一大港口,悉尼这些年发展得很快。看看今天的悉尼,谁能相信他曾是英国殖民者当年流放罪犯的蛮荒之地呢?悉尼的发展有华侨的一份汗水,一份功劳。华侨们为悉尼的繁荣而高兴,更希望祖国繁荣富强。华侨的根在中国,祖国强大远方的游子腰杆才能挺得直。
堂哥动情地说,尤启仁心不在焉地听。堂哥以过来人的口吻告诫尤启仁,在家日日好,出门时时难,单身一人漂泊在异国他乡更是难上加难,单枪匹马闯进西方的花花世界,不要抱太大的希望,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堂哥还告诉他,据可靠人士了解,根据澳大利亚法律,像尤启仁这样的条件,不能获得在澳定居权。
尤启仁一直心不在焉地听着,他觉得堂哥这是瞧不起人,是危言耸听。但是堂哥的最后一句话却像一瓢凉水兜头淋了下来,让他觉得心头一阵阵发凉。
他蒙头大睡了几天,苦苦思索了几天。他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打起精神再去第三国碰碰运气。
四
十多天后,他辗转来到了加拿大首都温哥华。
在机场办理人境手续时,他向移民局官员提出要求申请在加拿大永久居住。当值的移民局官员是位年轻的金发女郎。闪动着一双湖水般清澈的大眼睛。认真的审视了一阵眼前的这位中国人,目光中明显流露出好感。她轻启朱唇,友好的向尤启仁提问了几句话,并让他填写了一份申请表,又转身和另一位官员嘀咕了一阵,然后笑容可掬的让尤启仁过一个月来听取佳音。
虽然没能马上答应,总算有了希望,尤启仁还是满心欢喜。尤启仁也知道,申请在加国定居的人,一般至少要等半年,有的要等一年才有回音,而他只要等一个月已经是烧高香了。但是转念一想,他还是情不自禁地叹了一口气,辗转来到加国已是孤注一掷,如果一个月后申请被否决将会是一个怎样的结局?
在极度焦虑中熬过了一个月,终于等来了移民中心的通知:经审查,他可以申请在加国永久居住。
满面愁云一扫而光,雄心壮志重占心头。
但是雄心壮志既不能遮风避雨,也不能果腹充饥。从国内带出来的钱所剩无几,囊中羞涩,只好把宏图大志暂放一边,先找房住,找工作,找饭吃。
残酷的现实再次给了尤启仁当头一棒。偌大一个首都城市,加国西部最大的工业、商业、金融、科技和文化中心,竟然找不到一份糊口的工作。没有办法,这位堂堂的副厂长,不得不拿起笔来用英文写下了有生以来第一份救济申请书。
在国内,他只在本厂职工的困难补助报告上签过“同意”两个大字,却从来也没想到过自己有朝一日也要申请救济,而且是在异国他乡,如此卑微地双手把救济申请书递给一位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
这实在是一个无情的讽刺。
这件事多少对尤启仁的自尊心产生了刺激。出国干一番事业,难道就要从申请救济开始吗?
他不甘心这样下去,他要找到工作,开始真正的国外奋斗。
尤启仁打算做一个体面的文员。他根据报刊广告一家家上门去应聘。可是所有去过的企业几乎都以同样的理由予以婉拒:没有过硬的文凭,没有相关从业经验,也没有熟人推荐。
这番经历让尤启仁感到从未有过的煎熬。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他的再三恳求下,一个加油站的老板勉强答应收留他。但是老板声明,每天要干足11个小时的活,只照8个小时支付工钱。
没有选择的余地,尤启仁只好认了。
加油站的工作比他想象的还要累。整天抹车、加油忙个不停,稍有懈怠就会招来老板的责骂,还只能陪着笑脸。一天十多个钟头干下来,直累得尤启仁腰酸背痛。
开头几天还勉强撑得住,越往后越吃不消。下不光是累,更要命的是缺少朋友,缺乏亲情,工作之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加油站十来个雇员,大部分酗酒吸毒,跟他们无法交流情感。最难熬的是夜晚,每当他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那间嘈杂的小旅店,就有一阵强烈的孤独感和着混浊的空气直侵人他的肺腑。他躺在那张硬板架子床上,辗转反侧,难以人眠。他越来越感觉到,个人奋斗的诱惑力实在没有办法和思乡的情绪相抗衡。
尤启仁格外想念妻子小媛。她是那样的温柔善良。想当年他和她一道插队落户,风雨共患难,两颗心总是紧紧地贴在一起。婚后为了他的事业,妻子先后两次放弃了到高等学府进修的机会,一心只想维护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小家。工作之余,妻子独揽了全部家务,独自把一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没让他操过一点心。可惜呀,他尤启仁完全视而不见,把这些当作理所当然。
多么好的女人,如今他尤启仁竟不辞而别,狠心离她而去,这对她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每念至此,他的心一阵阵绞痛。
思念亲人,思念朋友,也思念一直关心着他的各级领导。特别是那位老厂长,为了支持、协助他搞一项技术革新,老厂长忍住胃痛,连续一个多月吃住在车间里。那项技术革新得以成功,为尤启仁在家电厂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而老厂长却累倒在车床边。后来厂里分宿舍,那套两房一厅的住房本应分给老厂长,可是老厂长说舍不得离开旧居,舍不得离开几十年的老邻居,硬是让给了尤启仁。为的是能让他有一个更好的环境,为家电厂多作贡献。如今老厂长们会是何等失望,这不是典型的忘恩负义吗?他还想到了何书记的临别赠言,阅人无数的何书记似乎有着洞察人心的先见之明。
此时此刻的尤启仁格外觉到家人的关爱和领导的帮助是何等的真诚,何等的珍贵。这时候哪怕是听到他们的骂声也会感到亲切。
他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划着一叶小舟,在波特汹涌的大海上飘摇浮沉,内心充满了恐惧……
一天傍晚,尤启仁没精打采的从加油站回到小旅店,还没来得及换下满身油垢的工装,一个西装革履的陌生男人悄然来到他的面前。看样子来者也是个中国人,黄皮肤黑头发,中等个头,四十五、六岁年纪,一口不很流利的普通话。
来人自称姓刘,是来自台湾的客商,一贯乐善好施,对大陆同胞更是如此。他说他注意到了尤启仁的处境窘迫,很愿意帮助他摆脱困境。
来人看到了尤启仁目光中的疑惑,连忙解释:“尤先生不要误会,我看你并非平庸之辈,将来必成大器,希望能和您结成患难之交。”
尤启仁静听对方侃侃而谈,没有搭话。出走以来酸甜苦辣他都尝试过了,在这个认钱不认人的世界,在他穷困潦倒的时候,居然有人主动找上门来要给予帮助?这时的尤启仁变得清醒起来,他透过来人的眼神似乎感受到了什么,这感觉使他不禁打了个寒战。他暗暗警告自己,不能一错再错。他毅然告诉来人,多谢好意,不用费心。说完决然做了个请便的手势。
送走这位不速之客,尤启仁深深感到一阵悲哀,他有一种被嘲弄被羞辱的感觉。
他开始意识到这次出走的盲目与荒唐。他想到了回国,想到了回家。可是转念一想,不能不有所担心:像他这样抛弃祖国的人,祖国还会接纳他吗?单位还会使用他吗?党纪国法会宽宥他吗?
他陷人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极度迷惘,极度悲伤……
五
然而,祖国母亲始终向自己的儿女敞开了温暖的怀抱,她不忍心自己的子孙沦落为无家可归的天涯孤魂,哪怕是不肖子孙。
尤启仁所在单位的领导一直在设法和他取得联系。
一个凝结着无限爱心的越洋电话终于打到了张某所住的小旅店。
党委书记的声音既亲切又威严:“尤启仁同志,迷途应该知返,我们欢迎你回来!”书记稍微停顿一下,声音有些沙哑,“老厂长患胃癌不治离世,弥留之际仍在牵挂着你,希望你能回来……”
尤启仁对着话筒放声大哭起来……
尤启仁放弃了办理在加拿大永久居住手续的机会,他回来了。
经历了几个月的漂泊流浪,他深深体会到做一个异国他乡的下等公民滋味不好受。他要回过头来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
周邦文
该文原载于1992年《隐蔽战线》第二期,篇名《歧路》,在《隐蔽战线》创刊十周年优秀作品评选中荣获优秀作品二等奖。《广州法制报》1992年9月18日第34期转载,改篇名为《迷途知返》。2023年12月修订于东莞,延用《广州法制报》篇名。
 发布人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发布人尹玉峰系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

都市头条 北京头条 天津头条
上海头条 重庆头条 雄安头条
深圳头条 广州头条 东莞头条
佛山头条 湛江头条 茂名头条
惠州头条 江门头条 沈阳头条
抚顺头条 大连头条 锦州头条
鞍山头条 本溪头条 辽阳头条
海城头条 盘锦头条 福州头条
厦门头条 圃田头条 三明头条
泉州头条 漳州头条 南平头条
龙岩头条 成都头条 绵阳头条
杭州头条 宁波头条 温州头条
廊坊头条 嘉兴头条 台州头条
金华头条 丽水头条 舟山头条
济南头条 青岛头条 枣庄头条
合肥头条 长沙头条 株州头条
湘潭头条 岳阳头条 衡阳头条
邵阳头条 常德头条 益阳头条
娄底头条 永州头条 武汉头条
南昌头条 九江头条 赣州头条
吉安头条 上饶头条 萍乡头条
新余头条 鹰潭头条 宜春头条
抚州头条 南宁头条 昆明头条
太原头条 大同头条 长治头条
阳泉头条 晋中头条 晋城头条
成都头条 雅安头条 乐山头条
资阳头条 绵阳头条 南充头条
临汾头条 运城头条 吕梁头条
朔州头条 呼市头条 包头头条
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发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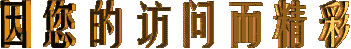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