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后子美文精选016
一眼望不到边
到大西北走一趟,是我多年的夙愿。
时光的脚步迈入到2023年8月,这一夙愿变成了现实。当亲吻了那里的大山大川大湖大草原,手中的笔像澎湃的心一样波涛起伏;一旦动笔,头脑里的图画纷至沓来,千言万语,飞流直下,就刹不住车了。
(一)
走出兰州中川机场,我有些发懵。这哪里是盛夏,简直是寒冬。这寒冬不是因为冷,而是满目的荒凉,漫山遍野几乎看不到一点绿色,看不到一棵树,草不但稀疏更是枯黄的。汽车在路上跑着,偶尔有一棵棵杨树闪过,就像夹着尾巴的狗,落魄瑟缩。树木几乎没有横向的枝条,典型的营养不良。这哪是杨树?分明是非洲大沙漠里的剑兰。
看到这些,我想到了黄土高原,想到了降雨量。是啊,这里的山川,这里的土地不是不想绿,不是不想葱茏,而是极少的降雨扼住了它们的咽喉。少雨,干旱,荒凉……转念又想,假如没有这干旱,就没有莫高窟壁画,就没有麦积山佛雕,就没有炳灵寺造像……就没有文化的大气象,事物都是两面的。万事万物的平衡,维护了自然与人文的统一,正是这统一,才使得人类文明连绵不绝地向前发展,才有了今天的繁盛。
兰州城是一条窄窄的腰带,在一条长长的山谷里展开,长达三十多公里,宽不过一公里。有限的空间制约了城市的扩展,路窄街瘦,再加上秃山荒岭的映衬,显得越发陈旧,陈旧得仿佛走进了中原或北方一个刚刚经历过搬迁的县城。但当你一头扎进去,却发现车多、人多,高楼大厦不时在眼前晃动,一派繁荣景象。矗立于黄河边的黄河楼,高大、雄伟,通身的铜棕色透着历史的气息,塔楼式的结构,现代式楼层风格,马上就会让你意识到这是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元素高度凝练的产物。楼西侧长廊“甘肃艺术博物馆”的题款,不但书法潇洒,且金黄的色调也古朴大气,与这建筑是珠联璧合的绝配。天空中始终飘荡着细微的尘埃,若有若无,应是沙土所至,再加上汽车不停地碾压搅和,让你又不得不抱怨那少得可怜的降雨,若有雨,尘土肯定就会消停。好在有一条大河穿城而过,河的两岸是铺展开来的绿,显得尤为珍贵。兰州是黄河唯一穿城而过的省会,正因为有这条大河,才有了这座城,世世代代的人们在此繁衍生息。河流哺育了世界上所有的文明,从尼罗河到恒河到亚马逊河到密西西比河……当然包括我们的长江、黄河。有水才有生命,有生命才会勃发文明。黄河流经九省,到甘肃是她的第三站。当然她没有站,也不敢站,日夜不息地奔腾着,九曲十六弯,一路向东,滋养着万物,滋养着百姓。有着黄河第一桥之称的中山桥就横卧在大河上,也是兰州游览必到之处。河里的快艇与羊皮筏子顺流携行,远古与现代碰撞,但后者终究争不过前者,在游人的欢声笑语中,快艇拉着一个个羊皮筏子逆流而上,拉去上游,循环往复。黄河水在这里比中下游清澈得多,温顺得多,是以一条益河的形象出现的。再说这桥,几经修缮,依然挺立,风吹到蓝色的桥体上发出呜呜的声响,正诉说着世事沧桑。站在桥上,目送黄河波浪滚滚,远去的身影,大有一眼远不到边的感慨。
到宾馆放下行李,已是中午时分,赶紧找地方填肚止饿。好在女儿女婿早已做足功课,直奔一家叫“再回首”的小吃店而去。还未到店门口,就发现冗长的队伍像一条长龙,已绕过一条街巷。等,还是不等?女婿说:等,来兰州就是吃特色。好在队伍递进得非常快,女儿、女婿排队,我跟妻子带着小外孙找座位,就餐者都是快节奏,且可混用一张餐桌。等女儿女婿把食物端来,我们也寻到了半张餐桌,有站的有坐的,狼吞虎咽起来。吃过一阵,细品细观,肉馅饼、高担酿皮、土豆泥馅饼、麻辣三样、灰豆粥……小吃,色香味俱佳,尤其是那肉馅饼,色泽金黄,外酥内嫩,肉香扑鼻,怪不得食客如云。一边吃着美食,一边环店四顾,在醒目的广告栏里,“再回首”三个苍劲率性、灵动自然的黑色大字赫然于墙面之上,深深吸引着我。字的下方有店的溯源说明,是1993年创办。我拍一拍脑袋细想,姜育恒《再回首》火爆正是那时。诗意,美食,文化,各种唯美的元素在这里集结,给人留下挥之不去的印象。我跟家人说,若把这店引到济南肯定大火,物美价廉,吃饭就不再作难,且将成为实实在在的享受。这店名,这书法,处处散发的文化气息,让我思绪万千。之前有些奇怪,大名鼎鼎的刊物《读者》为何在大西北?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午饭后,溜达着回宾馆。当行至一转弯处,一座仿古精美的门楼赫然矗立,上面挂着省政府的牌子,突然有想进去的冲动。我的一个发小应该就在里边,多年前他曾写信给我,说已从下面调至甘肃省政府工作,后来听其家人说,已官至厅级。官位高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小结下的情谊已深入骨髓。读小学时,这伙计经常天不亮,帮其父拉车去十几里外的集镇卖菜。有一天清晨,乏困的他实在坚持不住,就躺到地排车下睡觉,睡着睡着,突然感觉脸上又湿又热,睁眼一看,啊,原来是一条大狗正伸着长长的舌头舔他的脸,吓得他一咕噜爬起来,跑到父亲的怀里大哭。后来琢磨是睡觉口水惹得祸。再后来,母亲走了,父亲再婚,看够后母白眼、受够后母亲虐待的他,仿佛只有发奋努力一条路。恢复高考第二年,他考取到兰州大学,落户他乡,我也考学去了省城,彼此联系越来越少。
说出我的想法,妻子不冷不热地说:你去找同学,我们带着孩子去博物馆。思来想去,还是以家庭团结为重,也就放弃了去省政府的念头,再说这么多年失联,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找到。
甘肃省博物馆的馆藏丰富,从著名的马踏飞燕到红陶人面像,从卖萌三人组合到天祝铜牦牛……林林总总,满满三层楼,让人目不暇接。回宾馆的路上,我再次观察着兰州的市容市貌,除了人多路窄外,还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古老建筑与现代建筑是拥抱在一起的,没有任何间隙,相互争夺着地盘,给人的感觉是过了今天不说明天。在一条宽阔的马路中央,正建着一座大型寺庙,把一条好好的马路切割得七零八落。心里想,难道说就不能做做民族工作,给未来留下点和谐的空间吗?走着,走着,在一条窄窄的街巷里,突然发现一个牌子,是一个匾额——市府锅炉房,绿底红字,已有经年。看到这五个字,我好像明白了这座城市以上现象存在的真正原因。门口站着一穿蓝色工装的中年人,从上翘的眼角,还能看出他昔日的职业荣耀。
傍晚时分,一看表是7:30分,这边的太阳还老高。今天是周三,我努力往东方望着。此时,凝聚自己心血的读书会已开始近一个小时。多想有分身之术,一半在济南一半在兰州,学习旅游两不误啊。偶尔离开读书会,感觉心里空空落落,就像一个与自己朝夕相处十几年的孩子,突然寄宿别人家里,不在放心不放心,总有种说不出的滋味,是牵挂?是惦念?是情愫?好在旅程简短,很快就回去了,愿同学们学习交流顺利,回家平安。
晚上躺在宾馆松软的床上,习惯性地又看手机,害怕有漏下的信息。突然一条新闻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是中央纪委网站发布的新闻:甘肃省副省长宋某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啊!我立刻蒙了,是真的吗?是发小!又反复看了几遍,确认无误后,心中若有所失——看来今天省政府就是不该去的,去了不知会多么尴尬。
(二)
第二天,天热了起来,这热丝毫不亚于济南的热,如入蒸笼,浑身上下蒸腾地难受。幸亏女婿事先作了攻略,是去刘家峡水库游览,避暑,看水,看佛。早晨7:30到甘肃省博物馆对面集合,必须早起早到,以保证按规定的时间出发。与早起配套的,就是吃兰州拉面了,一条河、一本书、一碗面是兰州的三个亮点。一条河看了,一本书(《读者》)很熟悉,可这一碗面必须在当地体验。当提前到达集合点,来到路南的一面馆,吃上那热腾腾的、上面飘着几片牛肉的拉面时,感觉的确与在别处吃到的不一样。哪里不一样,说不清道不明,劲道、爽滑、汤鲜,味正,很是可口。或许是西北面粉的缘故,或许是水的原因,或许是制作技术不同,或许是其他因由,反正就是种说不出的滋味,有一种充分满足味蕾的愉悦。平时早晨饭少的小外孙,呼呼地吃着拉面,转眼多半碗进肚,比他姥姥吃得还多。
吃饱喝足,开始向刘家峡景区挺进。吃饱喝足的小外孙一路不停地问这问哪,好奇地仿佛到了另一个星球。经过一个小时的颠簸,看到无数座荒山秃岭,面对这毫无生机的世界,大巴车上大人都昏昏欲睡,孩子更是无精打采。可当看到那镶嵌在山坳间里的一泓碧波时,孩子的精神头又回来了,大声喊叫起来。这片水域有多大?可以说大得惊人,从水库大坝坐上快艇以80迈的速度一直往西,需行驶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炳灵寺石窟景区。快艇司机强调一定要穿好救生衣,然后说,水库用了十三年才建成,主要是用于西部的灌溉和发电。手机一查,这是黄河与其他水体第一次交汇之地,第二次与其他水体交汇处就是入海口了——在山东东营。本次交汇是黄河与洮河的交汇,交汇处水面泾渭分明,当然是黄河浑洮河清,但随着快艇的西去,水变得越来越清,这是洮河占了上风的缘故。当看到岸边那些放养的牛马时,让人误以为是在漓江之上呢。快艇跑啊跑,当跑到感觉有了水流,水域变窄、速度降下时,炳灵寺石窟到了。到了,请你不要急于下船,回头一望,是一片黄色的石林,高耸着,状如万笏朝天;仔细看,它们就像黄土高原上那挺拔的汉子,伟岸雄健;各种千姿百态的造型任你思绪驰骋,令人惊叹世界之奇妙,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过姊妹石像已完全不用想象,两块巨石高高地挺立、相拥着,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像一对姐妹,看到巨石上方伸延出来的部分,让人马上想到那是她们飘动的头巾,在召唤着远方的客人。
炳灵寺石窟造像群是沿着一条山谷而展开的,越往里造像越精美,最高的佛像几乎与山同高,微笑着,俯视着世间万物。一尊尊大大小小的佛像,或含笑或凝视或沉思,仿佛正在追思着一段段历史烟云、春秋过往和他们的身世来历。是的,在漫长的时光里,佛教自从印度传入中国,可以说是伴随着造像而逐渐深入的。从西藏到新疆,从甘肃敦煌到麦积山到炳灵寺,到大同的龙门到洛阳的云岗到江南各地,表情更复杂,鼻子更低平,中国元素渐多,烟火气更浓郁。宗教只有越来越世俗化,大众才能接受,才能传播开来,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山谷东面的那尊卧佛,是修水库时迁移到此处的,还专门修建了殿堂和院落加以保护,但因湿度太大,色彩大都脱落了。望着她慈祥安睡的样子,我跟女婿说:“古时候,有了这些具象的佛,百姓就容易教化,就普遍接受一种宿命,统治者就容易统治,所以大量的民脂民膏就干了这个。”“干这个还能保存下来点文化符号,干别的早就随着战火灰飞烟灭了。”女婿争辩道。我没再说什么,说又有何用?中国的历史无非就是一部人亡政息、不断否定前任、恶性循环的历史,任何建筑又怎能摆脱战火的泯灭?望着炳灵寺石窟那一尊尊佛像,仿佛又看到了以魏晋为代表的五胡乱华,那灭绝人寰的场景,又看到了那一帮从蒙古高原上,风驰电掣狂飙南下的武夫,占领中原后那一个个愚民的谋略。对统治者而言,开启民智是万万不可的。即使以汉治汉,也必须把思想统一到佛教上来,统一到高低贵贱的宿命上来,让百姓安分守己、牢牢地捆绑在土地上,接受他们的蹂躏和剥削——不忍再看了,再看是对愚昧的认可,是对心灵的折磨。
回到刘家峡水库大坝,花15元乘出租车来到山顶俯瞰,另一番景象出现了:水面如镜,像一块巨大无边的蓝水晶镶嵌在山坳间,蔚为壮观;细看,更像一幅油画,与茶褐色的山体相映相衬。灿烂的阳光下,在目极之处展示着一幅山水图,一艘艘客舱在水面上涌动着,划开的水线,是画笔的游走。观景平台上,有戴白色小帽的回民小贩,以售卖西瓜、冰糕、冷饮为主,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不停地叫嚷着:“美景,美景,冷饮,冷饮,一样都不能少。”他扫码板有两块,人多时扫冰柜上面的大牌,人少时扫胸前的小牌子。细问究竟,小贩嘿嘿一笑说:“扫大牌是老婆的,扫小牌进自己腰包。没办法,现在谁不怕老婆,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全国都一样。”没再说什么,眼前的那泓碧水已经替我说了,已经对世事沧桑做出回答。远处是美景,近处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天上人间,一雅一俗,乃成世界。
(三)
从兰州到西宁,一小时的高铁就到。
出了火车站,举目四望,周遭山上苍翠可人,倏地生动起来,马路上的树叶水洗般的鲜亮。阳光依然灿烂,但是暑热顿消,浑身清爽,恍若内地深秋提早移至此处。街道很是整洁,所有的建筑物上几乎见不到一个空调青春痘,一个个“夏都”的广告牌,不时从灯杆广告牌上闪现。天上的白云悠闲地飘着,妻子、女儿感觉头有点胀疼,应该是高原反应吧,吃过狗浇尿(饼)后,她们身体舒服了许多。小外孙依然是连窜带蹦地跑着,没有丝毫异样。女婿把租的车开来,有种反客为主的感觉,汽车在街上刷刷行驶,好似又回到了自己熟悉的城市。晚上吃的什锦火锅,肉、蛋、菜、豆腐、粉丝满满一锅,总算敞开肚子吃了顿饱饭。入住的宾馆处在市中心,好在房间是沿街的背面,也算安静。走进房间,凉风吹来,丝毫感觉不到燥热。洗过澡入睡,发现床上是厚厚的棉被,打电话给服务台,要求换毛巾被,回答说,这里夜里说冷就冷,劝我打开空调睡觉。我说,来高原就是享受清凉的,再开空调算怎么回事?无奈之下,突然有了主意,把被子的棉胆抽出,只盖被单,岂不乐哉。告诉女儿女婿此法,不冷不热,皆睡得安然。
养足了精神,我们开始向高原深处挺进。
出了西宁城,汽车沿高速路、国道、省道交织的路网狂奔,地广人稀车少,根本不用担心车的交头接耳,刹车几乎成了多余,右脚只剩下踩油门,这才叫过瘾。更过瘾是天地的辽阔,是没有任何障碍、没有任何建筑物的辽阔,远处是连绵起伏而平缓的山峦,是湛蓝天空上飘动的白云,近处是一群群、一拨拨牛羊。低矮的藏牦牛厚重敦实,活像一只只黑色的木箱,在草地上慢悠悠地移动。大地也好,山峦也罢,都穿着绿色的绒衣,牛、羊、马都悠闲地散布在草地上,几乎看不到放牧人的影子。这是横跨一千多公里的祁连山脉。徜徉在无边无际的天地间,看到漫山遍野的牛羊,我突然想到了王洛宾,想到了德德玛,想到了腾格尔,想到了刀郎和云朵……“草原就像绿色的海,毡包就像白莲花”“骏马好似彩云朵,牛羊好似珍珠撒……”辽阔的大自然是很容易打开人的心胸的。即使你没有任何艺术细胞、不懂音乐,在这样的环境下也会忘掉自我,忘掉尘世间所有的功名利禄,忘掉儿女情长,内心得以净化,想歌唱,想诵诗。想着,跑着,当感觉偶有堵车时,并非车多,而是牛羊的队伍正在通过公路,大小车辆不得不放慢步伐,等待草原主人的通过。
敬畏生灵,敬畏高原。高寒缺氧、生活单调,优胜劣汰,能在此生存下来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值得钦佩。
不知过了多久,汽车跑累了,我们在一个叫聚阳沟的地方停下,此处山水相连,森林茂密,满山遍野的松树冲着游人直笑。水声震耳,循声而去,是从一山洞里流出的瀑布,水花四溅,恰似天上落下的串串珍珠。再往前走,在一开阔地带竖有蓝色牌子,上面写有“景区内烧烤支锅费100元,未支付者不得烧烤。”看到这像草原、像森林一样率性的语言,能不令人莞尔?
登卓尔山的时候,妻子又感觉气短,她决定带着小外孙在山下休息。这期间,外孙认识了一位藏族小朋友。他名叫程立(音),长长的脸,大手大脚,头发微卷,正在照看他的弟弟。离开后,外孙谈起他的朋友,是满脸的欢喜。这份瞬间的友谊,或许将成为孩子终生的美好记忆。
太阳已西斜,当地的朋友来了,来接我们参加晚上的篝火晚会。他们带来了氧气桶和药片,打消了高原反应的顾虑。汽车又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当天色渐渐暗下来,在一座大山的前面停下来,喝过奶茶、青稞酒,众人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地上,篝火点起,开始跟着当地牧民载歌载舞,由怯怯生生,到逐渐投入,到得意忘形。哈哈,根本分不清唱的什么,跳的什么,只是感觉达到了一种忘我的境地,感觉与草原与大地与山峦与夜色融为一体。习惯早睡的小外孙也没了困意,蹦着,跳着,唱着,手舞足蹈,好不高兴。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再看那深邃明净的天幕上,繁星闪烁,半个月亮爬了上来,正冲着我们笑呐。
晚上,到达祁连县城前,朋友交待:“现在是旅游旺季,这个地方是靠七八九三月养活全年,东西特别贵,小心点。”已是很累,无心上街,早早的睡了。
第二天,我们去青海湖。有着高原蓝宝石之称的她,以其壮美和辽阔闻名于世,地球仪上都有她的位置,但是知道“西域生态调节器”名号的人并不多。湖水浩渺,一眼望不到边,她就像一块硕大无边的蓝色玻璃铺展在大地上,与印象中的“湖”天差地远,所以就有了西海的美誉。汽车加大油门沿湖边往前跑着,用了半天,才走了半程,看到她一半的容颜。路边的油菜花还在盛开,是黄色的花海。蓝色的海与黄色的海交相互映,中间是绸带般的路,那份大开大合、诗意的美随你肆意地想。怪不得,有的奇葩诗人把环湖公路写成绳索。嗬,请问,哪里的绳索、怎样的绳索能捆绑住这样的庞然大物?沿公路跑着,望着这一望无际的水域,路边不时出现德令哈的路标,诗人海子的德令哈。这样的天、这样的地、这样的花、这样的湖水,怎么会没有诗情?可惜海子只写了德令哈,如果他当年移点笔墨过来,写写这大湖这花海多好啊,或许就不会自杀。好在刀郎写了,写出了《西海情歌》“等不到西海天际蔚蓝,无言着苍茫的高原……”是的,在博大的自然面前,语言是多么苍白,一个人的生命是多么渺小,时光是多么短暂。有时候写还不如不写。为了生态的恢复,青海湖已实施了有效保护。湖边是去不了了,只能走到离湖相对近的地方停下车,碧波翻滚,一群鸟儿款款向我们走来,然后又轻轻地飞去停下,翘首摆尾,一幅满不在乎的样子。
(四)
刚刚离开青海湖,就收到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短信:“欢迎您来到祖国聚宝盆·神奇柴达木,揽万山之祖昆仑,赏天空之镜盐湖、望瀚海奇观雅丹、游壮美神奇海西。”按照导航的指引,翻越了海拔3800的山脉,又奔波近三个小时就到达了有天空之镜之称的茶卡盐湖了。此地,游人如织,硕大的旅客服务中心周围全是车。购票、等待、坐车,再上小火车,才到达盐湖。湖水是白的,一拨拨换了胶靴的人走进湖里,人在水上飘着,哈,这是盐水比重大产生的奇迹。在明亮的阳光下,天地间白茫茫的一片。远处是灰蒙蒙的山,那斑驳的白点是积雪。这里是昆仑山脉了,依然一眼望不到边。因急于赶回西宁,我们不得不打消进湖的念头,只是匆匆地为小外孙捡了些大大的盐粒作为纪念。
临出景区,忽然发现礼堂的门口挂着茶卡盐湖诗歌节的会标,也就想起了诗友,他刚到这里参加过诗歌节,并写了诗歌,还是用他的诗歌表达我们的心声吧——“满天满地的盐/与我的骨头一样颜色/无论遭遇再黑的夜也泛白光/我眼中的泪水/与这片湖水一个味道/无论世上多么干旱/也未枯竭/一望无际的盐/冷峻、孤傲,不爱说话/泪,与良知生死相许/靠它给灵魂消炎/来到这里,我是要问一问/多少人的泪水结晶出了这么多盐/这么多盐能让/多少酸甜苦辣的生活有滋有味”
(写于2023年8月)

李炳锋先生简介
李炳锋,笔名:金后子, 1962年3月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顾问,山东诗人书画院副院长。济南周三读书会创始人。
著有《日月清音》《一年的光景》《大地的苍茫》《回望天涯》等八部散文集和《在天地间奔跑》《挤掉生活的水分》诗集。2014年散文《红旗渠畔的沉思》获首届齐鲁散文奖;2018年散文集《大地的苍茫》获第八届冰心散文奖。散文诗歌散见各类报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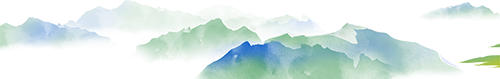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