逮蝈蝈
张庆林

快乐的童年像雨后的彩虹,缤纷绚丽。曾经做过的许多有趣的事,就像一颗颗明亮的小星星,在童年的天空中闪烁。
我的童年,是生活在祖国解放前后的那个年代。我们夏津县,虽然于抗日战争胜利后就解放了,但是全国大部分地区尚未解放,伟大的解放战争才刚刚开始,因此,从我记事起,便经历了火一样的不平凡的年代。
在一穷二白,贫穷落后的,解放了的老区里,满怀激情的村民们,在那张写满了激情与奋斗的白纸上,书写着开創新时代的美好画巻。
那个年代的农民,生活在靠天吃飯的岁月里。常常发生的自然災害,让靠天吃飯的庄户人,青黄不接,上顿不接下顿。 我们这些在那个时代,长大的孩子们,也就像他们的父辈一样,桃李不言,下自成溪,在一年四季的自然变化中,在人与天奋斗的现实中,从小小的脑袋里,就生发出许多采摘乡野趣事的故事。
那年月,我及我的小伙伴们,能够吃上焦黄喷香的玉米大饼子,喝上一碗粘调香甜的小米粥,就成了我们天天盼望的大事情。为着这一天的到来,我们会一天天睁大着眼晴,盼着风调雨顺的好年景;盼着遍地金黄,粮棉大丰收的秋天,以满足我们,放开嘴巴,大口大口地吃下,大自然赏赐给我们吃飽飯的强烈欲望,哪怕是不多的时日。
那个年代,我们虽然过得异常艰难,但是,在贫穷的岁月里,长成的孩子们,就像是受苦受累的父辈一样,早早地就步入了现实而又猎奇的童年生活。
我们跟随着父母,去自家的地里割豆子,也就跟着好事的父亲,学会了逮蝈蝈。金色的秋天,当遍地的毛绒绒约黄豆棵,豆叶柒黄了的时候,豆叶间一丛丛鼓鼓的毛豆角,便像珍珠玛瑙似地围在了豆棵上。而躲藏在枝叶间的蝈蝈,便亮开翅膀,可劲地吱吱叫起来。于是逮蝈蝈,便成了我们最感兴趣的事情。逮蝈蝈可要小心哟,蝈蝈的牙齿可锋利了,悄有不慎,就会被咬的指头流血。但是,逮蝈蝈是童年小伙伴们最上心的事,于是,就学着父亲,壮着胆子去捉。捉着公蝈蝈,便放进自己用高粱杆皮编成的小笼子里,带回家,挂到院子里的凉条上,只要想着每天往笼子里放上南瓜、絲瓜花页,和一点点苹果或梨,蝈蝈便吃得飽飽的,迎着天高云淡的太阳,便唱个没完没了,直叫得午飯后,想睡一会的大人们烦烦的。
高兴了的蝈蝈,晒秋的天越热,叫得越好听,就像一首秋收的歌。到了冬季,天冷了,就把它装进用小葫芦做成的小窩里,放到烧热的炕头上,照常喂养着,只是叫得少了。若是喂好了,它便跟着我们过年。
逮着的母啯蝈,它可要倒霉了。小伙伴们便打了牙祭,解馋瘾了。烧蝈蝈吃,是我们童年最想干的事。把逮着的蝈蝈,穿在细细的树枝上,拣点干树枝、干草叶子,把蝈蝈放在火上烤熟。焦黄的蝈蝈吃起来,甭提多香啦,就像吃满黄的大闸蟹一样,母蝈蝈的卵特香。还有,在黄豆地的地头地边上,烤青玉米;挖个土窨子,烤地瓜;掰一把黑壳青粒的高粱穗子,在火上燎一燎,一个个小小的高梁粒,立即爆开来,顿时,一穗穗的高粱穗上,布满了的白白的一颗颗小星星。这时,我们一边听着地里的蝈蝈唱歌,一边嘴里嚼着喷喷香的烧烤,甭提那个高兴劲了,个个吃得妙趣撗生,余味无穷。
我们生活的 那个年代,虽然年纪小,个子矮,但是,懂事早。因为我们是在风吹日晒的庄稼地里,拔草拣柴,跟着大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长大的,是在生活困难的锅碗瓢盆中长大的。所以,我们也就在父母长辈们,辛勤耕作、大汗流淌的影响和薰陶下;在父母长辈们,省吃俭用,粗粮细作,变着法的过穷日子的影响下,在小小的脑袋瓜子里,就装满了体凉父母,孝敬父母,多多帮助父母做农活,做家务活的孝心。因此,我们在不读书的礼拜天、节假日,或者,放麦假、秋假和寒假的日子里,从来不会赶集上店,闲着没事逛大街。而是把这些上学外的时间,看得很重要,会像排课程表那样,把小孩子们能做的活儿,排得满满的。拔草放羊,是放学后必须要做的事。把晒干的柴草抱到锅灶前,给大人做飯做好准备,也是每天要做的事。如果是礼拜天,或者是节假曰,那就要完成拔一垛草,或拣一垛柴的大任务。做好这件事,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干起来就要一个假期,又脏又累。但是,在成群结队的小伙伴们,干活的曰子里,也就充满了童年的乐趣。
由于我们家住在陈公堤上面的村子里,所以我们拔草、拣柴,则要去堤下的野草荒地里。那里是泛着白碱的蓬松地,长满了很多很多的柴草。长得高高大大的青蒿子,五股三叉的碱蓬棵子,还有各种各样的青草野菜,就是不长庄嫁。生活在这里的祖先们,就在这里种上了一排排,突起的望不到边的红荆棵子,到了雨季后的夏秋季节,一棵棵绿碌的红荆条上,开满了浓浓密密的粉红色小花,小花上溢出了,满满的一层厚厚的白色花粉,飘飘落落,香气袭人,引诱着走南闯北的养蜂人。嗡嗡乱飞的小蜜蜂,可喜欢红荆花了,酿造的红荆花蜜,粘稠晶亮,吃在嘴里,甜得齁人。还有那些草丛里,一群群乱飞乱跳的,绿色、灰色、褐色、黑褐色的大大小小的蚂咋,是我们在拨草拣柴的休息间,必须要捉的一件事情。我们逮住这些大蚂蚱,把它们用长长的一根拫谷谷友草杆,穿成一串一串的,带回家,做一顿美美的菜肴。把逮来的这些蚂蚱,放在火上烧一烧,或者用油炒一炒,黄黄的,又香又酥,好吃极了,越嚼越香。
在我的童年里,有许多的童年趣事,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就渐浙的健忘了。而唯独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我国遭迂三年持大自然災害时的一些童年故事,至今记忆犹新,挥抹不去,也许,那些刻印在骨子里的亲身经历,己同血肉融为一体,渐渐长大。
我们,为了应对那个粮食不足的年代,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会想出许许多多的办法,和我们的父母一道,同心协力,救災抗災,度过那段艰苦的岁月。我清清楚楚地记着,收割小麦的炎热季节里,我们小小的年纪,冒着酷暑的炎热,去生产队的麦地里,拣拾社员们收割小麦后,落在地里的一根根麦穗。天高云淡的秋天里,我和我的弟弟妹妹,会到生产队的黄豆地里,去拣拾爆在地里的一粒粒黄豆。生产队的地瓜熟了收后,我和弟妹们,会用铁铣,用锅铲子去揽落在地里的地瓜。那个年代,让我们懂得了,没有什么能够比吃飽肚子更重要。也没有什么比餓肚子更难受。我们懂得了粮食的金贵,也懂得了没有什么比爱惜节约粮食更重要。
记得有一次,我小小年纪,就跟着父亲去十里外的地里去揽地瓜,揽花生。
在一遍遍用铣翻过的,被人揽过的地里,每当我揽到一块地瓜,或揽到到一粒花生的时候,我心里简直乐开了花。每当父亲扒开一粒花生,把花生米递给我吃的时候,我看看微微有些驼背,白白的头发,脸上爬满皱纹的,五十多岁的老父亲,总是把父亲剝好的花生米,首先放到他的嘴里,或者,趁父亲不注意,偷偷地放在兜袋里,带回家,留给母亲吃。父亲发现了我的这一小秘密,看着矮矮个子的我,总是笑得流着眼泪着说:"儿子,你长大了”。
简介
作者张庆林,山东夏津人,山东散文学会会员,德州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山师聊城分院中文系,曾服役部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在《中国火炬》《人大代表报》《今日文艺报》。《山东工人报》《辽宁日报》《山东教育》《德州日报》《德州晚报》《盘锦日报》《棉花地》:《济南头条》《半盏平台》《两可诗社》等纸刊微刊多家媒体平台发表作品多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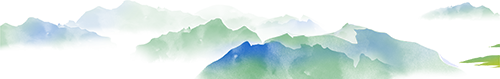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