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难忘在柞水生活的日子
文/陈英良
时光匆匆流逝,离开柞水县红岩寺快三十年了,那段在红岩寺法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在睡梦中时常梦起。因为那儿山美水美人更美,难忘与那儿的人民朝朝暮暮的生活情景,难忘与那儿的同事们生活战斗的经历。
1990年7月份从学校毕业,那年我21岁,青春年少,告别父母,离别亲人,来到了“祖国山河可爱镇安柞水除外”的柞水县,被分配到穷乡僻壤的红岩寺法庭工作。初来乍到,脚踏生地,眼观生人,一个孤零零的外乡人,一切都是那样陌生。第一次离开故土,思乡的情绪油然而生,独处时不知道哭了多少次。蓦然回首,最怀念我在柞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红岩寺,我把她比喻成“窗前含情的少女,月下沐浴的姑娘”。柞水东部一颗璀璨的明珠,它是富人心中的天堂,穷人心中的凄凉。地处柞水县东部的秦岭腹部,六县必经之地,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森林覆盖率90﹪以上,穿越青岗槽越文公岭与蓝田葛牌古镇相望,小金钱河从红岩寺街旁流过。红二十五军曾经在红岩戏楼成立五星县苏维埃政府。红岩寺法庭当时管辖着万青、九间房、红岩寺、黄土砭、张家坪、穆家庄、瓦房口七个乡,南北120里,东西80里,三万六千老区人民。“一山末了一山迎,十里没有半亩平,九山半水半分田”是它地形真实的写照。九十年代的红岩寺人民生活还是比较困难,当地有一句俗话“万青九间房洋芋糍粑是主粮,要吃改样饭,洋芋打糍粑,苞谷漏凉鱼”。

古朴典雅的红岩寺戏楼

古色古香的红岩寺街道
法庭位于风景优美的老母山下,和派出所同住在一个院子里,前后两排房屋,前排是法庭,后排是派出所,被群山重重环抱。法庭的环境与读书时想象的根本不一样。法庭是一座南北走向坐西向东的四间土木结构瓦房,每间房屋一隔为二,里面住人外面办公。两扇铁大门已是锈迹斑斑,前檐下墙面上白石灰痕迹下依稀还可以看见文革时期留下的毛主席语录: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庭长办公室墙壁悬挂的大国徽就是审判法庭和会议室。睡在床上仰望屋顶,可从几块破碎的瓦片缝隙窥见天空。全庭有四个人,庭长姓赵,审判员姓董,都五十多岁老革命了,姓姚的书记员比我大二岁,我们都不是本地人。生活是孤寂清苦,工作单调乏味,心里不免有些失落。欣慰的是自己是一名头顶国徽肩扛天平的法院书记员。法庭没有自己的食堂,要到政府食堂搭伙,有时工作一忙就忘了吃饭时间,只能到街道饭店下馆子,偶尔也去朋友处蹭饭。

九十年代红岩寺破旧法庭一角
我居住的小屋宁静而又自然,有一种自由、惬意的感觉。电是水力发电,每晚七点多才来,电压经常不稳,灯光忽明忽暗,我就在这灯光昏暗的小窗户前下撰写法律文书,整理卷宗。打开门窗,一阵阵清新淡雅的香味扑鼻而来,顿时让人心旷神怡。夏夜窗前月光下小池塘虫鸣蛙叫令人放松心情。法庭小院有一片菜园,里面种有蒜苗、洋葱,菠菜、豆角、青菜,一片绿色的海洋。漫步在小菜园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泥土的清香,一天工作的疲劳好像也瞬间烟消云散了,如此这般地享受着它带给我舒适。
法庭两个办案组。小姚和庭长一个办案组。我和董审判员一组,老董人实在,很随和,文化不高,农村基层工作经验十分丰富,他原先是万青乡党委副书记,调到法庭五年了。那时办案全凭法官跑腿,全凭法官调查取证,当事人可以不举证。走一线办一串,蹲一点办一片的办案模式。那时案件大多是邻里纠纷,家长里短,小额债务,这些纠纷在有些人看来毫不起眼的“小案”,但群众利益无大小。那时案件几乎都是以调解和撤诉结案,离婚案件往往拖好长时间,三番五次不厌其烦的调解,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轻易下判的。我跟着老董背着案卷,办了一件件难缠的案件,学了很多办案经验。细思之,在红岩寺法庭的那段日子,老董教会了我如何正确把握人生的航向,跟着老董接触形形色色人物,用百姓信服的方式化解矛盾纠纷。老董常说,花园里种不出天山上的雪莲,不经过磨难是难以成熟,人生酸甜苦辣才是幸福。在老董那里学会了化解矛盾纠纷的技巧,学会了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学会了如何使情、理、法三者巧妙结合起来。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从老董身上学会很多办案经验和社会常识,这在我以后的工作中少走很多弯路。
我们那时办案经常出没在野草丛生的山间羊肠小道上,翻过了一座山,越过一道岭。一路上绿树成荫溪水潺潺。有时几十里渺无人烟,人迹罕至,大山深处山清水秀好风光,一不留神一条菜花蛇闪现在你的面前,吓得人魂飞天外。站在高高的山岭上极目远望,远处重峦叠嶂,近处半山腰绿树环抱秀丽的村庄,隐隐约约看见升起的袅袅炊烟,也能看见远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劳作的村民身影,山间泉水汇集成溪流清澈见底,仿佛是进入了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地,欣赏着蓝天白云下大自然的美景,让人心花怒放。那时办案也到红岩寺周边的曹坪、蔡玉窑、柴庄、杏坪、肖台、凤凰镇,偶尔也到丰北河、营盘、石瓮、小岭一带,可以说几乎跑遍整个柞水。那时法官们多半是步行或骑自行车,经常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去办案,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经常出没在村头巷尾,田间地头。下一次乡起码要走八九十里山路,时常不能打道回府,只能住在认识的村民或村干部家中过夜,他们一定会四个碟碟,一坛苞谷酒,高升五魁招呼你。

1992年柞水法院全体干警合影(第二排右五是赵庭长,第三排左四是老董,第三排右一是小姚,第一排右一是作者本人)
不在山区工作不知山区环境险恶,特别是山高谷深,水流湍急的山沟。曾记得有一年夏季的一天,老董,小姚和我骑自行车去八十余里外的瓦房口龙坛寺村现场勘验,工作还算顺利,去时艳阳高照,返回到金井河边时已是下午四时许, 顿时大雨如注,河水猛涨,我们三人相互搀扶着过河,刚接近河对岸时,老董脚底一滑被水冲走,我们拼命呼叫,好像天要塌了,没想到水冲到100多米处被一颗树挡住,我和小姚赶紧过去把老董拉上岸,老董终于从鬼门关回来了,这时我们手抖脚软,饥肠辘辘,狼狈不堪,赶到马台时天色已晚,只能寄宿在马台信用社,惊心动魄的一幕至今仍记忆犹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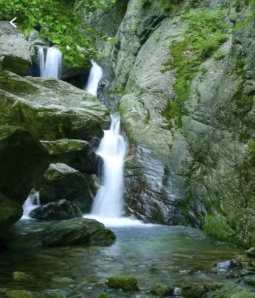

景色秀丽的柞水风光
我清楚的记得1992年秋日一天,我携带三起案件独自骑自行车准备环绕红岩寺一圈,大约一百五十里行程,早上8时在街道吃了一碗肉丝扯面,开始翻越杜家沟岭一路下坡到红岩寺颜家庄,调查取证结束已是正午十二时,又沿着金井河骑行到穆家庄党家塬已是中午二时,苦口婆心调和一对闹矛盾的夫妻,已是下午五点,我又马不停蹄骑行到小河口时,这时天空下起了小雨,折往北上坡骑行五十多里就可以回到法庭,这时我已是人困马乏,精疲力竭。目标是争取按天黑赶到张坪祝家沟送达一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诉讼文书,这时自行车两个轮子搅进去太多的泥泞,几乎已经蹬不动了,又饥又饿,好几次没有把握好速度险些冲到埝下,一路走走停停,最后只好推着走。到沟口时夜幕快要降临了,我把自行车寄放在沟口一农户家,听说进沟四五里路,山间的小路越来越难走,山大沟深林密,四周没一户人家,山沟死一般的寂静,远处传出几声野兽的怪叫,已是伸手不见五指,我淹没在黑咕隆咚的夜色中,心里十分害怕,进退两难时,一着急脚一打滑掉进了水沟,冰凉冰凉,我越思越想越着气,不由得嚎啕大哭起来,我想让我的哭声惊动对面高山上的村民。不一会,我看见了对面山坡上的火把,心里一喜,我有救了。
善良的村民给我烤干了衣服,又给我下了一碗挂面,村民们的热心深深地感动着我,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这次单枪匹马的下乡对于初出茅庐的我的确是不小的挑战。这以后老董言传身教教会我农村生活经验,再也没有经受那样挫折。
在柞水工作的五年里,我历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白驹过隙,往事如烟,山里人的淳朴、善良令我难忘,随着时间的推移愈来愈浓。我的足迹遍布这里的沟沟岔岔梁梁峁峁,我走村串户办案的身影留在了这里的村村落落。记得有一年春季的一天下午,下乡走到万青万灯寺,我辨不清东南西北,又饥饿难忍,好心的大嫂给我端了一碗糍粑,又送我到沟口;记得一年夏天的一天中午,我下乡到红岩寺正沟水口马鞍岭交界处被毒蛇咬伤,好心的大叔给我敷上蛇药,还管我吃住;记得我和小姚在红岩寺卢草沟处理案件时遭遇不明真相的群众围攻,是组长王大哥给我们解围;记得我和老董七上八下黄土砭大沙河处理一起相邻通行纠纷,我们的真诚感动了当事人,纠纷圆满解决,当事人还给我们送来锦旗;记得我和小姚住在张坪石船沟的三天两夜调解了八起债务案件,使得多少年的陈年老账得以兑现;记得我和小姚在红岩寺本地湾处金钱河水里嬉戏的情景;记得在九间房庙沟年迈苍苍的养父母重获养子女的赡养;记得有一年的初冬我和小姚从青岗槽返回法庭途中一路坐的敞篷车,一路尘土飞扬,回到法庭灰头土脸,老董幽默地说,你俩连出土文物一样;记得多少个夜晚我和小姚在我的小屋一起谈古论今,讨论案例,纵情唱歌;记得多少次与同事们在一起纵酒狂欢。记得1995年2月2日早同事们送别时紧握住我的双手,千叮咛万嘱咐,盼我隔年再来游……
记得很多在柞水的往事,闲暇时总在脑海里萦绕。
在洛南生活快三十年了,几回回梦里回柞水,双手搂定老母山。忘不了豪华壮丽、金碧辉煌的红岩戏楼;忘不了红岩中学门前气势雄伟的参天古柏;忘不了古朴且古色古香的的红岩古街;忘不了热闹非凡的三六九红岩寺集镇;忘不了情趣悲哀曲调委婉的红岩孝歌;忘不了热汤酸菜配油泼辣子的九间房洋芋糍粑;忘不了饱经岁月沧桑的凤凰古镇;忘不了光怪陆离的柞水溶洞;忘不了腊味飘香的柞水腊肉;忘不了风味独特的柞水十三花;忘不了肥而不腻瘦而不柴的柞水腊肉锅盔;忘不了柞水唱着歌划拳饮酒的情景;忘不了风光旖旎的牛背梁国家森林公园;忘不了依托秦岭老屋而建的终南山寨;忘不了温柔可爱的柞水妹子嘴巴甜,干活多来吃的少,忘不了……

作者简介:陈英良,男,生于1968年7月7日,本科文化程度,在洛南县人民法院工作。业余时间喜欢练太极,唱秦腔,写一些散文,《我喜欢秦腔》,《基层法官的一天》,巜母亲,我心中的一座灯塔》,《学习太极拳随想》等文章先后在巜商洛日报》《商洛审判》刊登;《如何阻止农民上访后脚步》在《民情与信访》杂志刊登;巜小时候过年的那段岁月》被洛南县图书馆评为特等奖。
发稿编辑:张灏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