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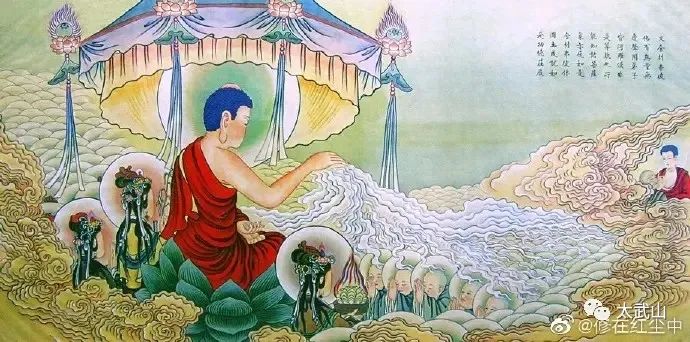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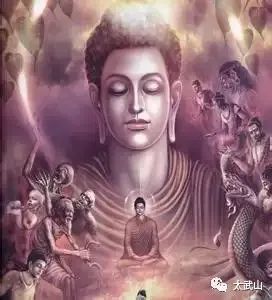
艾艾香草 养我劬劳兮
文/梧闽









《金刚经》第二十品《离色离相分》云:'佛可以具足色相身见不。不也。'所说的'佛',相当于'食物钠'有盐这个色相肉身,用盐做咸菜这个报身,而用吃了'食用钠'很多人很多报身一样。佛祖的色相是一个美男子,有三十二种相,八十种好。就似盐有各种品牌包装,吃'食物钠'长大的有众生人类等。各种吃盐大的人都有一个人的样子,这叫'具足色身'。所以说郭江会老支书的'食物钠'和佛祖的口头禅'于意云何'内容虽然不一样,但是禅意一样的。现在我不禁扪心自問,为什么一样吃盐长大了,有的大富大贵,有的穷困潦倒。有的俗不可耐,有的却观自在成了无忧无虑的活佛,这是值得深思熟虑的。此刻我也不知道'于意云何''。


十年前,己故的漳州文史专家黄超云先生,送我一本《螺壳斋诗文选》,对闽南话漫谈过。其中也特別讲了闽南话的二句土著话:'伊哥豆缠'和'嗄里罗',这是口语汉字译文。'伊哥豆缠'实話意思是'粘贴'或'纠纏'的肢体动作或语言反复这意思。而'嗄里罗'又一种比喻叫'麦牙糖的棰子',一支这样的糠酸莫米鬆的捧子,被粘著了的感觉。'嗄里罗'不是假有文化把'食盐'讲成了'食物钠',让未读到化学课的老支书,小时候莫名其妙,'食物钠'便成了他仿效有文化的老师语气,而成了自己一生开会或交谈的过门话。中国少数民族傣族的古代经典《嗄里罗嗄里坦》,自称是先知写出来的。《嗄里罗嗄里坦》说的道理是要处理好事情,一方面认识必須正确,符合事实;另一方面说处事必须符合政治伦理规范,否则不会成功。书里反复说这一句话:'耳闻还必須眼见,眼见还必須用脑思考,只有思考好了再嘴讲出去。',后来,闽南话中的'糕哆嗦'好像与古代土著口头话'伊哥豆缠'的语意混爻不清相近。那么,'嗄里罗'是傣族古代经典《嗄里罗嗄里坦》的前半段'嗄里罗',作为闽南人的我,容易理解一些,因为闽南人评价一个人说很'罗',是指无知无明又胡搅蛮缠这个意思,应是'嗄里罗'的简约说法。《嗄里罗嗄里坦》之所以是经典,不是为了'嗄里罗'的状況,而是为了'嗄里坦'这一初心目的,'坦'即聪明又正直,坦然自若无所畏惧。这与佛教经典《大光明法》似乎有同样鹄的!









马先生的雨夜'嗄里罗'照片,由睛转雨入夜。虽然我居住在'龙出九江,花开四季'的石码九龙新城,也曾主动布置栽种了石榴、月季、茉莉花、俩雾、人参果、巴西跌、越南铁、盆格子、木瑾花等一批花木,出出入入还是有些季节感或睛雨表!离开农村老家43年、甚至离开乡镇工作也有21年了。住在龙海县城老石码,属于半农村半城市生活,在漳州与厦门之间的小城古镇,似乎就是我的宿命一一当一个不农不兽的养老闲人!


农民的儿子,城镇的女婿在性格上可能还有农民的烙印,却染上了官场的习气或市场的市侩,所以才自喻'不农不兽',做人没有农民的朴实本份叫'不农',做事沒有官僚的凶狠与奸商的狡诈,所以叫'不兽'。记得品牌衣服'七匹狼'广告中李连杰一句话:'男人麻,对自己狠一点!',有创业干事的励志语气,实际上类似教唆别人,不留情面,可踩道德与法律的底线!不然,怎么才叫'狠'角色!


因为城里生活惯了,远离了农村及土地,对于日出日落,好天下雨并不是特別敏感,倒是对发薪日或节假日有露出欢喜心或期望值。出來回去看到的景观,除了高楼水泥路面,就是有空调电脑桌椅的工作室,外面的春夏秋冬季节变化,除了添衣穿戴不同好像无啥变化;城镇里一切的一切,主要是买卖、赚錢与消费,体现在咱身上就是吃喝拉撒了,所以人一旦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就慢慢地成了城镇里的经济动物,不想刮风下雨,只需要春秋两季。对于身边的草木花卉,也沒有那么亲近亲切了,而我在自己住的小区,志愿付出劳动栽花种草,似乎并不是为了锻煉身体,而在于一种救赎与唤醒,不妥忘記自己从哪里来的!


幸好,老家梧桥有一个农耕馆,收集了一大批农耕时代的农机具和农村日常用具,它们已經没有用武之地,而且农三代也随着城市化而少人会操控使用那些犁地的犁、耙田的耙、网鱼的网或打谷的机,仅仅作为一种记住的道具,而'乡愁'也不用愁了,以前农民怕乱风下雨起雷闪电…现在,这算啥?作为跳出农门或者转当居民的梧桥人,狂风暴雨来临之际,完全可以学习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


我的十七岁前是农民区梧桥乡下孩子。生活在丘陵山场那个广阔的天地,虽然没有'大有作为',但是对小时候的花花草草有记忆。朱德委员长《咏兰》诗云:‘幽兰吐秀乔林下,仍自盘根众草旁。纵使无人见欣赏,依然得地自含芳。'农村的众草,印象深的有牛屯草、茅根、紫丁地藤、狗尾草、毛神草、苦草、水浮莲、含菊銀草、稗子等,而更多的是叫不出学名的草,数量漫山遍野,甚至长满房前屋后。它们兀自萌芽展叶,开花结果,荣枯随季。不若那些庄稼水稻、小麦或甘庶有娇气。母亲说过:'我是草籽命,生在九龙江边上宛村,6岁就被送到云洞岩西梧桥社,成了山场的童养媳,命贱点好!'草籽可以下土长根,生生不息!而我也成了草籽的儿子,可惜离乡又离土,恍惚间不知道了何处是故乡!



母親的草籽放在梧桥一块最贫瘠的土地上,嫁給我父親是'地主无地,富农不富'的坏成份家裡,命苦似黄莲一般!



现在好了,有时我从石码回去老家,路过亲人社的洋西村,去《龙江颂歌》主题公园边看看刘亚立同學租地种水稻的场景,顺便在公园的地毡草上赤脚溜達几圈。那看似无边无际的《荷塘月色》前后,象梳子梳理后地毡草地,让我上去就想打个滚,翻筋斗,或者莫名其妙地跑上几个来回,累了就坐在藤椅沙发上,看看西边日幕夕阳落山,瞧瞧东边云霁鹭鸟齐飞翱翔…最为有趣的'梭草'不一定在席梦思床上,而在这里!亲人郑霜高家的狗尾草,就在村庄不远;狗尾草长成的时候,会冒出一截好香的花穗。风过来时,那些花穗会落下草籽随风而去。狗尾草似乎就是芦苇吧,因为它的形状象狗的尾巴,竟然让我忘了它可爱的学名叫'芦苇',当它在春天的季节,就叫'青纱帐',嘿嘿!

瑞午节快到了,石码后街'三芳埕'卖烧肉粽的棕子哥,总是招呼我去白吃美食。不好意思之余,我想破费买点有母亲做过'大碱粽子',并且叮囑他替我购买两种名'草',菖蒲和艾草,菖蒲据說是一种芳香的毒草,放在家门口可以拒蝇虫蚊子,对'四害'有诱杀或驱离作用的草,相对于人类却是有益的。




郑亚水,笔名梧闽,出生于漳州东郊梧桥村,毕业于漳州农机校和厦门大学政治学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先后由漳州市图书馆出版《秋水白云》《西方国际政治研究》、作家出版社出版《白云深处》、海风出版社出版《月泊龙江》等书籍。2001年中国东欧经济研究会授其《企业文化一一现代企业的灵魂》''优秀社科论文一等奖'',并入选《中国改革发展论文集》(北京希望电子出版社);2009年11月,该论文被清华大学收录《n<1知网空间》智库咨文;《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中国文化出版社)副主编。
作品《<兰亭序>拾遗》一文于2010年9月入选《中国散文家代表作集》(作家出版社),并荣获2010年度中国散文学会“中国当代散文奖”;2021年8月,作品《说好的父亲》荣获“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2月,作品《说好的父亲》入编《中国作家书法家代表作全集》并被评为“特等奖”;2022年4月,《过故人庄还有多少龙江颂》荣获第九届相约北京文学艺术大赛“一等奖”;2022年7月,《紫云岩 无住与不迁》荣获2022年最美中国当代诗歌散文大奖“二等奖”;《禅意 太武凡木》荣获全国第八届新年新作征文“一等奖”;《一字圣手江山常在掌中看》入选《高中语文》古诗词必读讲解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