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在读苏忠的诗之前,我有机会读到他已经出版的两本文集,一本是《职场江湖》,一本是《狐行江湖》。两本文集都有名家为之作序,可见他的文字功力和影响非同一般。在《职场江湖》这本大部涉及企业文化的文集中,也有相当多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漂亮,说理透彻且行文幽默成趣,都是极好的美文。就在那里,我惊喜地读到一篇题为《诗眠》的文字,在这篇文章里,他用散文的笔触充分想象地“还原”了李商隐《巴山夜雨》的诗境:
站在那间寒冷的屋舍外,雨帘潺潺,池水徘徊流咽,远远近近的水泡上早已消失了脚步声。屋内,一灯如豆,那个头戴方巾的诗人正若有所思地来回踱步,寂寞长了又短,短了又长,浊重的呼吸与橘黄的烛影层层重叠,周遭游荡着枯草的窃窃私语,屋檐顶上那张千年的蜘蛛网正费力地向着它的影子挨去。
这段文字其实是在用散文的方式解析诗歌,他尽力揣摩诗人创作当时的情景意念,并试图“重现”形成诗歌氛围的主观的和自然的因素。尽管他在做这些努力时可能未曾意识到诗歌创作若干深层的因素,但事实已暗示了他具有这方面的才能。苏忠在上面引用的那篇文章中说,他喜欢“走进”类似“巴山夜雨”那样的诗的境界。这种“走进”的意愿,其实已是诗歌创作的最初萌动。
他不仅在诗中造访了李商隐,还在他的家乡寻访过辛弃疾留在福州的诗的踪迹。为了印证那首《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他曾经从夜雾弥漫的福州城南跑到空荡的城北,从逼窄的东街口绕城一周赶往醉酒摇晃的津泰路。苏忠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平衡方式,我选择读诗来陪伴一生。读诗的时候心是纯净的。”正是因此,我在正式阅读苏忠的诗之前,已对他的诗歌能力具有充分的信心。
苏忠写诗是由于酒,他自己说,某次聚会“酩酊大醉之余,头脑翻江倒海,忽忽生出写诗之念。”他的感觉也许是对的,诗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醉语”。苏忠给自己的诗歌创作划分了许多阶段,我以为不必那么细分,只要是醉眼蒙眬,把现实的影子幻化和重新组合,可能就会出现充分想象的好诗。我从苏忠的叙述中得知,在那场“酒醉”的“启蒙”之前,他好像是并不写诗的,只是由于酒意的来袭,才有了“信笔涂鸦” 的念头:一种书写的愿望“随空行跳格深潜入心”。就是说,他从此拥有了散文之外的另一种表达的方式和手段。
这种新的拥有使苏忠对于城市的感受和书写,得到一种别开生面的展开与提升。他对于城市的见解不再停留在一般性的描写和再现的层次,而是感到了一种“后城市”的“禅意”——他是借助诗歌的方式把他的体认作了超越。过去的那些职场的现实感受,在他的笔下也化为了一系列空灵的甚至怪诞的意象。他恣意地渲染城市生活那些繁华的场景:夜总会和购物广场的林林总总,脚步匆匆的上班族,那些淹没在车流人流中的弱势而无力的人群。诗人的笔触所到之处充盈着关爱与悲悯,那里的骄奢与华靡,那里的隐忍与不公,无不得到尽致的披露与展示。
他用诗歌的方式继续进行他对于城市和职场的生存状态的描述。《幽州台之寻》最鲜明地表达了这种在城市寻找无着的落寞心境:前后左右充斥着的,不是清风明月,也不见古坛残碑,而只是:股票楼市物价玫瑰接吻巧克力与一夜情,唯独永远地失去了他要寻找的幽州台。无论是在幻中,是在路上,或是在闲余,或是在局里,他总着力于表现人们处身的尴尬与困境。人们一面在享受着都市文明的赐予,一面又挣脱不了远逝了的田园风光的怀想与诱惑:
就闭上眼睛
听窗外嫩芽抽枝 ,鸟声啁啾 ,木叶盘旋
任远处赶来的风将头发一根一根舔揉
就闭上眼睛
让电脑里的新闻游流, 邮件停泊, 文件稍息
且随心情走东窜西 ,意念一茬一茬冒泡
诗人总是听到一个声音在与一个声音对话,天空布满鹅卵石,没有一只夜莺在歌唱,这正是诗人心情酸痛的时候。在他做这一切时,并不满足于细节的刻画,而是充分利用现代诗歌的跳跃与抽象,把他的关怀与批判精神融入到那些纷繁杂沓的意象中。他用都市流行的词语:桑拿、派对、精油香薰、钢管舞、铝合金框广告牌、蜘蛛人、阳台护栏——组成冗长的不间断的句子,诸如——“打着手机东张西望握手拥抱海泡大堂吧职业干练”“交换名片—见如故谈判竞合咖啡甜点顺带搭讪小姐们”,用来传达他的不安与疑惑。
他表现的不仅是环境与氛围,而且是他的内心感受、置身其中的冷静思考和判断、混合着不无揶揄的讽喻和讽刺。正是这些,显示了苏忠诗歌创作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可以说,他延续了他用散文表达的城市的思考,并且创造性完成了诗歌对于城市的深沉的观察与考量。
从苏忠的自我叙述来看,他诗歌创作的时间并不长,但却是成果显著。他写得很流畅,涉及的内容宽广而驳杂,但对于城市的把握与揭示却是集中而深刻的。苏忠的诗歌现在还未形成独立而稳定的风格,但总体看来是清新自然的。他喜欢用近于白描来记录和缅怀属于自己的历史记忆,“我读他人诗作时,喜欢的亦为精短篇幅。我也相信,许多人也一样喜欢灵性精洁的诗作。”这方面最为引人注意的是精短简约的《疼》——
奶奶抱着我
把我
轻轻放进摇篮
/
我抱起奶奶
将她
轻轻放入棺木
在这首诗中,一个多余的字、甚至一个多余的形容也没有,这就是白描,这就是简洁。而来自心灵深处的锥心之痛,那种永难泯灭的旷世的哀痛,却极大地震撼着读者的心。苏忠说得对,“千古诗坛,群星璀璨,但再有成就的诗人,其诗作再多,能让我们记住的多为短章小制。” 苏忠的诗也多是短小精悍的,其中不乏隽永含蓄脍炙人口之作。但退一步说,即使只有一首《疼》让人记住,也是诗家之大幸!
苏忠有一首《素描》,给我印象极深:落地生根的那一刻,一棵树苗,就立下了向天生长的目标,这个永生的承诺!也许这就是诗人的诗歌和人生的誓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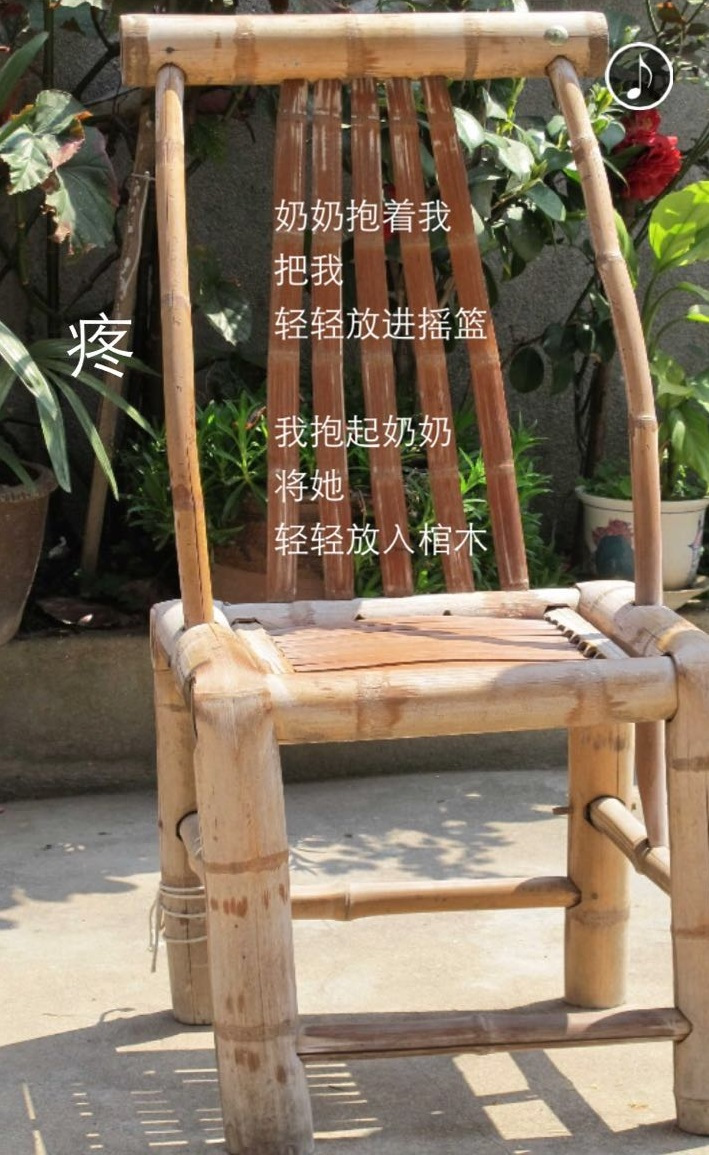
(谢冕,1932年生,著名文艺评论家、诗人、作家,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