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苏小玲:在文化中透视中国
——纪念王学泰先生
 ↑图为:王学泰先生
↑图为:王学泰先生
2018年的1月16日,冬气未散,八宝山弥漫的寒冷是特别的。北京知识界的数百追悼者,与知名学者、被誉为“文化界泰斗”的王学泰先生做最后的告别。吊唁大厅里,除了哀乐、献花和花圈,还播放了一小段先生的生平影像。加之子女悲伤的泣诉、学生深切的回味,一个社会人文的浓浓缩影再次浮现,让逝者坎坷的经历在众人一片脑海与心际间滚动、碾压。了解先生的,一定有那些挥之不去的时代悲凉印痕,或还能感觉眼前的现场如同社会学的一次“临床实验”:在生死之间体会精神煎熬与人类磨难。而我已听到,有数人在感慨万千中潸然泪下!
作为中国文化的思想巨匠,先生这般离去,却为社会留下了某种文化洞见继续残缺的印迹。以我对先生的了解和理解,相关学术机构对他的悼词虽很权威,但依然缺少盖棺定论时应有的真实与力度,似乎也配不起一位学问大家对这个社会孜孜不倦的探索与付出。尤其是,一种知识分子与当代史的复杂文化关系,并未得到应有的检讨和理性地概括。似乎过于官样的评价,妨碍了人们对一个试图解剖国家性格、解读民族文化的学者的深刻解读与足够尊重。同时,也让人不禁联想到一句民间说法:人走茶凉!
我亦深为遗憾。在先生患病其间,曾让他的同事安兴本教授转告我:小苏太忙,就不要前来探望了,等出院后再见面。可没有出院,也不再见面,对我自己的忽略大意随即变成了某种做人缺陷的自责与忏悔!我知道,先生向来不愿麻烦别人,尽管他自己这一生总在经受着无数的麻烦——为思想、为著述,为社会、为他人。先生也以读书人的本分,深刻解释着他个人进步同历史、文化的内在关联与承继。所以,他非常重视写书评,为体现新旧作者的思考价值,也表达作为读者的“感激之情”。
在《坎坷半生唯嗜书》的“后记”中,先生如是说:“许多知识人操觚撰文成书有着许多艰辛,我们从中获得了知识或思想,但却缄默不语,仿佛自己所说所写都与他人的劳动无关,我以为这是不可取的。”这种发现并非远见而属于常识道德,也是人生虔诚与文明敬畏,甚至还是一种代人悔过的现代意识。作为一位饱经风霜的大知识分子,他对不断发生的社会普遍现象,或肯定或否定,终归有自己的观念衡量。
2010年春,经由朋友、中国社科院安兴本教授(文化学者,钱锺书先生的弟子)隆重介绍,我有幸与学泰先生认识。那时,我正在筹办《影响力中国》网,需要更多知识界的各路思想精英们加盟支持。而先生对“影响力”规划也颇有兴趣,听我详尽的网站定义与对象阐释后便颇为认可,于是承应将以有限精力参与其间。次年,他便同出版家沈昌文、法学家曹思源等德高望重的先生们,以及文化学术、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各界近百名人士一道出席“影响力中国”的上线酒会,并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他认为:当下中国社会缺乏的正是一种能兼收并蓄的思想,而“影响力”网站应该大有作为,影响社会新观念、新思维、新文化的建构!
那以后,我会不时与先生通电话,或上门打搅,求教各种疑难杂症的困惑。令人高兴的是,每一次讨教都会有满意的结果。而且,先生总是不厌其烦,每每通话至少一个钟头以上,而面对面交谈就更是没完没了。但凡真正有大学问的人,都会善待真诚的求知者。先生有大胸怀,除了诲人不倦,也常接纳晚辈的肤浅。丰富、厚重与谦和、大度,这些纯粹学者的优质品相在他身上、文中实在是随处可见。
应该说,先生对改革开放为促进中国社会的某种转变是积极肯定的,还认为“这次转型的深刻大大超越了以往”。而对个体的发展也是寄予了某种期待。作为其中之一,他曾说我是个“思想的行动者”。这自然是一种勉励,大概看到了我在不停歇地折腾。而那些与知识界相关的、流产或启动的文化诸事,也同时和他关注的社会问题复杂地交织着。包括“知识分子”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与作为,如何界定意识形态下“人民”与“公民”的真实概念与身份。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文化人应该都成为面向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社会的自觉变革者,而不留恋着旧时代,彻底摆脱旧体制的各种束缚。
先生在国内外具有显赫的学术声誉。其博学强识、研究精深且著作等身,亦被业内人士视为“另一个钱锺书”。而对我这位才疏学浅、见识微薄之人,正是可予恶补的对象。这个年代,许多人也许都遇到了“鬼打墙”的状态。我们的迷路与丧失,是同别人说不清的一种混乱与纠结。但先生博古通今,明了历史正常的神经所以发生阻断的深刻缘由。从《诗经》到《资治通鉴》,从《论语》到《二十四史》,文史哲、儒释道,先生几乎无所不及也无所不究。而研究大文化,当然始终离不开一个共通的背景:历史文化侵染下的政治。
先生平时喜欢在家里三俩聊天。某个夏日,安教授约我同去见先生。到达时,如同往常,几杯绿茶已沏在那儿了。我将一本刚出炉的《大秦帝国》送给他作为参考资料,先生便因此谈起了嬴政与董仲舒两相叠加的历史效应,即专制政治和独尊儒术的互为表里与承袭,就是一部一成不变的传统中国史。先生认为,专制者脑子多是一片浆糊。孟子将人说成是“性本善”是一个重大错误!而世界范围内类似“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实践活动,也包括伊斯兰极端宗教在内,其本质上是一种野蛮而背离了人类的文明。
先生认为,“这个国家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好也好不到什么程度。”此外,在他看来,“士大夫阶层也已消失;今天中国已无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只有极少数的异议人士。”正因如此,先生一直拒绝人们称呼他为“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对当下十分期待“知识分子”又实在稀缺的中国,属于难以化解的社会尴尬!
在与学泰先生的交谈中还给我这样的启发:中国社会之所以容易出现民族主义,是因他们更多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缺少反抗的资源(资本),无法平衡自己的生活与心理,容易走极端或被煽动、被利用。在一声吆喝下,被带进革命队伍(混吃混喝)。的确,这也符合先生对游民文化性格的某种定位。按现代表达,他们就是一群权力或利益的依附者,缺少独立的思考与独立的人格。当保命求生成为第一需求时,那种传统的“臣民”意识就会得到自觉强化。同时,缺乏对社会大是大非的判断,人们的精神更是游离于目标的自觉与价值的自为。再从一个角度回望,当漫长的政治史浸染或切割了宗教的神经,饱读诗书的阶层也可能被逼成一群乌合之众。
先生特别提到朱元璋这个从游民到帝王的典型案例,更加确定了历史上“农民起义”及其“农民领袖”,不过是一些游民为了生存本能的驱使,与其所谓“阶级觉悟”、“先进革命意识”并无什么实质上的逻辑关系。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具有天然的反社会的意识倾向。朱元璋并非出身贵族,从游方和尚到士兵军头再至皇帝老子,身份变了,但内在的品性并无根本改变。先生也自然深谙游民社会的习性、弱点,故此,也必然地要“用法令编织成一个网,笼罩着整个社会,他深信这种强硬控制是保持社会稳定的惟一手段。”至于如何建立国家文明与社会良序,则不是他所考虑的根本。
学泰先生著述繁多,其中特别值得一提就是《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在洋洋洒洒的50万字的论述中,他从游民、游民文化、游民组织以及如《三国志》《水浒传》这样的通俗文学并行入手,分析了游民反社会、结帮派、野蛮性与破坏性的特征,充分展示了一幅影响中国发展史的浓稠而灰沉的社会画面。他力图告诉人们:游民意识或游民文化是中国社会无所不在的一股力量。它们也是一种历史文化的血液,至今还流淌在知识人的血管里,调理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的生命成色。而我所能理解到的一点,则是游民文化与阿Q精神之间的高度契合,形成了对现代文明的持续损害与消解。
“发现另一个中国”——正因这部巨著的学术价值,即对民族史的本质认识具有颠覆性的文化揭示,而为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充分肯定!他在此书的长篇序言中,不仅感叹作者其研究工程的艰巨,更是盛赞对游民社会文化挖掘的重大意义:“因为它蕴藏着中国两三千年所谓一治一乱的谜底,而且我生怕它可能还指向中国未来历史走向的谜底。”此外,还有这段意味深长的评论:“辛亥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会党’的力量,这是人所共知的,而会党不过是有组织的游民而已。当代的中国农民革命在其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斗争过程中,是不是也受到了根深蒂固的游民意识的侵蚀与影响呢?”
李慎之先生也为此书的洞若观火而引出对“十年文革”的再反思。他把“专制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激进主义、历史的“游民文化”与“痞子运动”结合起来分析,发现了“文革”的造反与其暴烈行动,可同归于一种“极左”的“活水源头”。他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屡遭挫折,屡走弯路,其间中国社会的顽固守旧是一大原因,而游民意识作为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起了极大的破坏作用。”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清楚自己身上还有多少非现代的东西,又怎么能知道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
是的,能思考的知识分子,都没敢忽略当代人类曾经的精神劫难史。而学泰先生,作为文史大家,对“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反思无一不是透过表层,精辟入里。那些历史回顾,那些社会论断,那些文化预见,更是这个期望转型的时代一笔不可多得的思想财富。所以在他的言谈中,每每都能得到他的直达要害的启迪。这种启迪,关联到的是数个王朝的勾连形态。通过抽丝剥茧的细节描述,又能感受到中国历史从古到今的一种绝望。而这等绝望,也恰恰是先生所揭示的中国“游民社会”的本质归属。
先生自有背负的苦难岁月。1975年,因言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之后三年多的牢狱之灾与屈辱经历,使他对社会与人性的幽暗又多了一层感悟,也体味了“政治上成了敌人,道德必然也是堕落的”非常规思维逻辑。2013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他的《监狱琐记》,将一段浓缩的“号子里”的人生,从文化视角上展露得淋漓尽致。他对“文革”的剖析尤为深入,对造成灾难的根源认识亦很深刻。记得最后一次见面,先生还转赠了一套厚沉的相关“文革”的书籍给我。他知道之前我曾与哲学与社会学家、中国社科院的徐友渔教授共同策划过《我与文革》专题系列,觉得我们比他更为需要这些历史资料。
作为一种个体意志的存在,学泰先生的学者生活独树一帜。他不因遭遇磨难而止于屈辱,也不为学富五车重返殿堂而沾沾自喜。他坚强的信念,为重开的学术天地给出了一道非凡亮光。对绵绵数千年的中华神经脉络了如指掌,有人称他为一部中国文史的“百科全书”。先生治学正经严谨,也鲜明抵制史学界存在的“非历史的态度”,批评对历史人物进行某种“胡编乱造”、“吹捧过度”,“丧失了史学精神”。这样的假观点或伪学问,无疑都将给青年、给读者,也给社会进步带来不堪的文化后果。
这段时间里,一部叫秦的电视连续剧被各方舆论批得近于体无完肤。将秦一统专制结束分封视为伟大的“转型”之举,着实荒谬!先生若在天有灵,眼下这等对“天下苦秦”历史暴政的歌颂,会有如何的鄙视与忐忑?他曾写道:“现在大家都习惯说‘皇帝也是人!’这成了原谅皇帝凶神恶煞一面的借口。其‘人’有好坏啊,不过普通人影响不大,而皇帝则不得了。”他以清朝的乾隆为例:“制造了那么多的文字狱,连神经不太正常的人都不放过,连年过八旬的老人也毫不留情。”先生对专制帝王的所做作为,充满了深刻的警惕与审视。
作为所谓最高智库的研究员,尤其是深谙历史奥秘又学问声望极高的学者,并非一般人能望其项背。如此感觉,学泰先生似乎该为“朝廷”所倚重。但他却云淡风清,并无专此昆仑心思。对自己的通天学识,他说不过是“雕虫小技”——这对我真的震撼不小,言教极深!传统中国,也培育了浓郁的“君臣”文化。即便当代也不乏“帝师”或“国师”情结者。只苦于不得要领,时常不免落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似的尴尬。这些年,有不少自视甚高者也浮在面上,众目睽睽;凭着大概率的把握,做定无风险的“谋臣”。
先生读书破万卷,通晓文史,自然明了诸如“谋士”、“门客”、“师爷”种类的之所以然。但他对当代历史人物及其智囊的感观却缺乏欣慰。他似乎更注重于做定性分析,不热衷那种不坚实的虚构或幻想。在他眼里,天上还是那颗星,地下还是那片土,而其中的人类,也依然是循环反复的炎黄子孙。可先生也曾告诉我一个小秘密:某日,他被召至中南海“面圣”。对方请他讲解清人板桥的诗书奥妙,他便以郑燮风骨大肆渲染,且不免也得一刻借古讽今。我问先生有否改革策论呈献一二?他幽默一乐:哪能?
对于中西文化比较问题,先生自然也不缺关注。他相信欧美民主政治对世界近、现代史的品质影响深刻。然而,对中国如何嫁接西方文明,却不抱太大指望,原因是东方有着特有的性格固执。他是非常期待出现一个有“个人权利”、并由一群“有独立主体资格的人们组成”的契约性社会。如今,美国的社会生态似乎有所改变,全球化出现不那么健康的进程加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等这些源于西方的新旧思潮,也似乎再一次被全面捣腾,产生某种不确定的变数。而能否以其中真实、优质的一面融入中国社会,在文化上进行一番匠心独运的现代性恰当建构,大约还是一种不小的奢望。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某种执着与顽强的观念沿袭,也会让我们在老路上徘徊不前。
先生与我还曾专门谈论过中日关系和日本的历史现象。在国际关系上,我们彼此的观点有些接近。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他们经历了成功、失败与再成功的社会转型。其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是西化与现代的,那种类似“脱亚入欧”的自觉、决绝与彻底,在中国就一直没能形成过。日本诚然也有自己的国情,但往往在关键时刻,“改变”——改头换面就成其最突出的“国情”共识!或许,日本的现代史,就少有像先生所指的那种特别能依附的“游民知识分子”?他们成功获得的现代性,或取决于一群解放了天性、认同文明生活的人,形成对实现一个国家“贵族化”的整体追求。
显然,作为文化的深度研究者,先生对中国文学的古今面相也是颇有识别的。因此,除了指点李白、杜甫的古诗风格,他还特别对我谈到过鲁迅以及与“左联”的关系,里面还夹着一个年轻轻甚至天真的冯雪峰。他们以不同的方式都倒下了,以悲凉的色彩形成了一节文学的创伤史。的确,在非常时期,文学家同政治沾边总归是危险的。而鲁迅,则可能是想象着在任何方面,“都能从没有希望的路中踏出一条路来”。或许鲁迅死得恰如其时。要不,一个绝对“右派”的作家与“右派”的学者同坐一牢,也并非什么值得惊诧的新鲜事。
总之,回味与王学泰先生相处的日子,有太多情节值得回味。平时,即便感觉他就似一座学识高山,却又见其虚怀若谷平易近人,而忘了怎样恰当地给出必要的敬畏。相反,则是欠缺应有的景仰之势甚至过于随便与疏漏!尽管如此,我还是能找到某种自我安慰:遇上一位名副其实的文化学大家,却未能产生一丁点的生分。客观是,其背后的一种人格尊重与交往平等,还伴有另一层越过庸常的人性与精神的芬芳。是的,细嚼交往中的细节,没一个不蕴含文化生动的滋味。一个人不具一种对美德的敏感和体验,处于社会人生当中便是件最大的憾事之一。而那类在重要品格上经不住过硬审美的人们,不论他们如何有名望和地位,或所谓“高人”、“权威”,倒也无需为其仰视、折腰,大约也只配那种“敬而远之”!
据说先生在病中,也曾希望能“穿过死亡幽谷”。大概感觉自己有幸越活越通透,可以留在这七上八下、容易令人心神不定的人世间,多为迷糊的人们努力点拨些什么?76岁,对在京城退休的学者并非属于高龄。即便患病,以自身脱离了旧式“游民”身份所享有的医治条件,也可能会有更好的康复结局。可惜,先生还是匆匆离去了!这样的遗憾,感觉是文化的长城被瞬间洞穿成一个偌大缺口。而缘于明摆的差异性,旁观者则也无力修补!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欲理会真实历史,或以史鉴今惠及未来,都不是件随意的事情。
已整三个年头了,不时怀念,偶尔迷惘;因先生,也为苍生。
2021.1.23 北京

作者简介:
苏小玲。作家、评论家,北京改革与发展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原《影响力中国》总编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出版有《悲剧的春天》、《一路问云天》、《生命苦旅》等若干文本。

都市头条 北京头条 天津头条
上海头条 重庆头条 雄安头条
深圳头条 广州头条 东莞头条
佛山头条 湛江头条 茂名头条
惠州头条 江门头条 沈阳头条
抚顺头条 大连头条 锦州头条
鞍山头条 本溪头条 辽阳头条
海城头条 盘锦头条 福州头条
厦门头条 圃田头条 三明头条
泉州头条 漳州头条 南平头条
龙岩头条 成都头条 绵阳头条
杭州头条 宁波头条 温州头条
廊坊头条 嘉兴头条 台州头条
金华头条 丽水头条 舟山头条
济南头条 青岛头条 枣庄头条
合肥头条 长沙头条 株州头条
湘潭头条 岳阳头条 衡阳头条
邵阳头条 常德头条 益阳头条
娄底头条 永州头条 武汉头条
南昌头条 九江头条 赣州头条
吉安头条 上饶头条 萍乡头条
新余头条 鹰潭头条 宜春头条
抚州头条 南宁头条 昆明头条
太原头条 大同头条 长治头条
阳泉头条 晋中头条 晋城头条
成都头条 雅安头条 乐山头条
资阳头条 绵阳头条 南充头条
临汾头条 运城头条 吕梁头条
朔州头条 呼市头条 包头头条
京港澳台世界头条总社发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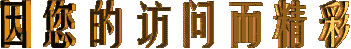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