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海著《黄河传》连载13
《黄河传》
张中海 著

第三章 皇天后土(甘肃)(三)
苦脊甲天下
……一道灿烂的阳光照到舷窗,飞机穿透云层,云雾之下耸立的雪峰像雕塑,又像汹涌的海洋。从乌鲁木齐翻越唐古拉山再往内地,云海忽然逝去,机翼下展现的已是深褐色的土地,太阳像打起万道聚光灯,把河山照亮。这时,冰雪的海洋已变为黄褐色凝固的波浪。随飞行高度下降,只见浑黄波谷中出现一条闪光的飘带,有时纷披如散,有时凝一细线把山一分两半:黄河就这样,把我们从天上带到人间。高原之上,机翼之下,云彩遮着的黄河呈深褐色,阳光直射的地段,河则泛着银光,其大美非语言所能形容。
就像艺术欣赏中的美总是让人忧伤,天上和人间自然是两个天地。远观和近视也不一样,甚至截然相反。
这时,让我们再换一个视角,从河下游的华北平原溯河而上,远离河谷往高原深处走,那印象就只焦、渴,甚至不是黄。山庄零零散散坐落山坡或谷洼,挤成堆的是低矮的房屋。沟谷有河,但多是干的,偶见一星半点的溪流或山泉,在无边的黄土弥漫中,更见纤弱、无助。
对高原刻骨铭心的回族作家张承志如此描绘:“只要你凝视着它,只要你能够不背转身而一直望着它,这片焦黄红褐的裂土秃山就会灼伤你的双目。在恐怖的酷日直射下,眼睛会干涩、皱裂、充血,一种难以形容的旱渴会一直穿透肺腑。”干渴是因为缺水。
水是世间一切生物赖以繁衍生存的基础,还是一切营养能够让人体消化和传输的动力。
庄稼、瓜果、菜蔬,包括人体之所以丰盈,之所以蓬勃,那也全是因为它50%以上的成分都是水,如果把水拧干,那就只剩一把柴火。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以其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古往今来,人们在享受水的恩泽时,还创造出以水为喻的普天下皆准的哲学思想。但在高原深处,水却没有那么浪漫,只有形而下,因为它,也只有它,才能活命。
甘肃定西机关干部回忆自己的公务员经历说,那时,机关干部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就是每当干旱来临,给乡下百姓送水。每当送水车来临,牛、羊、鸟,全都围了过来。
一头老牛把头抵在送水汽车前,宁愿被撞死,也不挪一步。当送水车被迫停下,它朝着远处哞哞呼唤,一头小牛从山沟跑来。原来,它是为了自己的骨肉而不惜以命相抵,就是为了那口水。
2015年6月19日,我前往定西最穷的安定考察当地水土保持,由于国家政策扶持,退耕还林特色农业兴起,安定的土豆已经远销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并且他们还引进加拿大、荷兰品种,生产炸薯条专用薯,包括特色中药材和花卉,农民生活已经较前好了许多。经过打地坝地堰、梯田整修等一系列水土保持措施,农民把坡地还给了山林,不种地也有国家补助的粮食,腾出工夫正好出去打工挣钱,这片贫瘠荒芜了多少辈子的黄土高坡才得以休养生息,才渐渐变绿,山沟地才积累起一汪一汪让人看着湿润、看着心疼的水。
“苦脊甲天下”,缘起清朝左宗棠给光绪皇帝奏章,“陇中苦瘠甲于天下”,后做一地域概念广泛使用。它原指甘肃定西市安定区、陇西县、漳县、岷县以及临夏一部分,后又包括周边会宁、静宁、甘谷、武山和秦安等县。严酷的自然环境使这里的生活像凝固又不断坍塌的千沟万壑一样,时光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这里却还是原来的样子。
自然交替,时代轮回,1949年以后的新国家新制度,无疑给穷人带来了新希望,但老天却好像仍无动于衷。九山一川难见水的定西仍然是十年九旱,1972年连旱三年,百姓看人民公社生产队的地实在是养活不了人了,集体扒火车逃荒;1982年又旱,五、六万农民簇集兰州火车站扒火车。天旱,种一葫芦收一瓢,人可以逃荒,那牛呢?来春还指望黄牛耕地驮粪,而牛也需要吃草喝水。杀了,舍不得,卖掉又不值钱,那真是农民的哈姆雷特式的烦恼。这年12月,国务院召开甘宁两省救灾专题会议,除去发放数额庞大的粮款,还制定了修梯田、集雨栽培、集雨补灌、打窖拦蓄等诸多措施。
关心时事新闻的当代人或许注意到,2007年大年三十夜,时任国家主席、国家总理的年就是在定西安定区青岚山乡大坪村过的。
2013年春节到来之际,新任国家主席也绕过九曲十八弯,先后来到定西市渭源县元古堆村和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族自治县布楞沟村,在一户人家,总书记特意端起一瓢水品尝,并嘱咐把民生工程切实搞好,让老百姓早日喝干净甘甜的洮河水。
领袖为什么逢年过节都往这里跑?因为这里是他最挂心的地方。2020年后全国脱贫,但之前的历史却不应忘记。
在我们固原,有十万大山。
大山夹着平川,平川里长着野牡丹。
在我们固原,女人磕麻子,男人嚼豌豆
……
一碗洋芋面能盛三斤,锅盔似磨盘,
罐罐茶能苦死癞蛤蟆……
在我们固原,几千年就没出过状元写在史书里的是响马,土匪,棒客……
在我们固原,有一条最大的河,泾河,你要是在河里饮驴
下游的甘肃人会站在山梁梁上大喊:
我日你老先人哩,你家的驴喝了,叫我喝怂呢
……
甘肃土著诗人单永珍的诗,《在我们固原》。
水窖与水井,水车与天车
把头插向河里或山泉里一顿痛饮,或用手捧着把水送进嘴里,这曾是我和我乡村伙伴的拿手好戏,当然也是我们先人最先取水的方法,几乎和林间野物如狮、豹、狼及后来的家畜马、牛、羊没有什么两样。以后先人尝试用阔大的树叶、中间有凹面的石片盛水,这些方法对于濒水而居来说,很是轻松,但对于被洪水赶上山腰或土丘之上的先人,就远水不解近渴了。
出土于四五千年前柳湾或马家窑的陶罐,显然是人类史前期最伟大的发明,它不是我们今天视角之下的艺术品或文物,是生活用具,装盛粮食,如粟菽,更重要的是用来盛水。
汲水的女子从河边泉子里盛一陶罐水扛在肩上,赤脚、裸露着胸乳向我们走来,当这一画面被有嫌色情的画家定格于画框,人们显然不满足于欣赏这一古典美,而立马就要临渴掘井了。或早已掘井?
《史记》载:“后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但传统上我们的先人更认同“伯益作井”。就在大禹“尽力乎沟洫”灌溉庄稼的同时,水井,古代文明中富有意味的符号,也在这片厚土上,以揽入白云明月的光亮仰望它头上的皇天了。
周代实行“井田制”有多种解释,而我只取一种,那就是田头或村头,至少必须有一口。
一锹下去见水,那井就毫无必要。一个人凿不了一口井,两个人三个人也难。所以,井的出现也就标志着村庄、部落以及小农小生产条件下集体生产方式出现了。
掘井的前提是有地下水。在没有地下水的干旱地区,人们只能收集地表水。这种储存地表水的“器皿”,人们称为“水窖”。
水窖也称旱井,是甘肃、宁夏西海固地区人们储水以解决人畜用水的设施。雨后或冰雪融化后的洼地水汪,牛羊可饮,人也可以刮来烧水做饭。
宁夏专业人士吴尚贤和张万海调查,宁夏阳山有1920年大地震后修建的水窖,到现在用了90年也还在使用;同心地区高家岭有一眼水窖,至今120年了;而盐池县麻黄山一眼容积为80立方米的水窖,则距今已有200余年历史,目前仍完好无损,正常使用。一般情况,一眼水窖使用年限在20—50年上下。
水窖的传统做法和规格,一般都是上下小,中腰大,状如古瓶,地面距水面一丈五。深藏地下的窖不为观赏用,但它美,美在它的科学道理。
首先,上下小、中间大是两个截头椎体连在一起,具稳固性,既符合力学原理的结构,也是存水最大的一个形体。
其次,水面距地面5米,水深5米,符合只有水深达到6米水才有自清作用的道理。如果水深不足6米,或距地面不足6米,存水时间一长,水质就会腐臭。地表浅水如水塘水汪容易腐坏而深水不腐,就是这个道理。由于水窖具一定深度且有自净作用,其水质是时间越久越好。在刚蓄水时,较为浑浊,需要沉淀一月左右水才能清凛。
一个蓄水量达40立方米左右的水窖,可供五口之家全年用,如一户两窖,就能抗两年无雨,还能养十头大牲口,100只羊。
水窖还能蓄冰雪。每当冬季下雪,男女老少都会出动,连同草根羊粪都统统收进。那时,村民娶妻说媳妇不问粮食囤几个、房屋几间,而是问水窖。有没有水窖,几乎就是财富的标志了。
安定采风还有一个故事,20世纪20年代,一个没有水窖的农家,大旱之年去十里开外的一眼泉取水,等了一天一夜,好歹才挨上号取满了一担水。回家的路上,一个趔趄,前面瓦罐打碎,平衡失去,后面罐子也碎了。跌坐在地的老汉爬起身,解下腰带,干脆把自己吊在了一棵唯一的树上……
现在看,水窖或水窨,就是干旱地区人们在没有地下水的地方借鉴先人掘井的方式给自己修建的一个大水缸,而在河边,特别是黄河边,濒水而居的人们提水用的更多的是水车。
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自来水龙头一拧,就可以让不知从哪里来因而也就不知珍惜的水龙头喷上半天,或习惯了站在离天三尺三的高处,看大马力的电灌站,只要把电闸合上,几百米之下的河水就会如涌泉一样喷上来,自然无法想象先人当拥有最初的一只陶罐或拥有一架水车,让水按自己的意愿汩汩地流进自家田里那种由衷的欣喜。
较早把水车应用于农业生产的是三国时期的魏国扶风人马钧。马钧住在京城洛阳,城里有一片菜园,因地势高无法取水灌溉,马钧研究了以前多种灌溉方法,经多次试验,设计制造了一种可以直接提井水的“ 车”,而且还可以从黄河或黄河支流上提水。可以用人力,也可以用畜力,如牛、马、驴。效率是原先提水工具的百倍之多。
而马钧以前,实际上已经有了辘轳和东汉毕岚造过的“水车”。辘轳的结构是在井口两边竖起两木架,再把轮轴原理制成的辘轳头置于木架之上,辘轳上缠有绳索,利用人力摇动,把水从井里打上来。在人力提水与水车提水之间,辘轳是决定性的一环。
黄河流域大规模使用水车提水以灌溉农田,历史上记载有两次,一次是公元828年的唐大和二年闰三月,《旧唐书·文宗本纪》载:朝廷“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水车从民间发明到沿河仿效,进而形成政府行为,是因他看到了新技术装备对农业生产、国力增强的促进作用。
而这种促进的原始诱因,则是河水。是的,河水。黄河千古,不仅能灌田、生发庄稼,还能催生更加先进的技术、工具。
兰州地区对水车的再一记载是《甘肃新通志》:“续里居时,创翻车,倒挽河流,以灌田,致有巧思。……沿河农民皆仿效焉。”
段续,明嘉靖二年进士,官至云南道御史,宦游南方数省时,就对当地筒车产生极大兴趣,派人绘成图样,保存身边。晚年回乡,致力于水车仿制,嘉靖三十五年也就是1556年春,段续创制的第一台翻车架在了今广武门外的黄河北岸,接着又在今镇原路北口架了三台。“水车园”地名即由此而来。靖远一带农民也由此开始了仿制。
“ 西晋东渡”作为北人向南方大规模迁徙的开始,躲避中原战乱的同时,也带去了黄河流域先进的科技文化,包括水车技术。江南本多才子又多水田,北方的水车一到南方,无疑得到更优化的改进。而回乡士绅段续以南方技术仿制的“翻车”一经出现在黄河岸上,立即形成一种别致的风情。黄河静流,水轮咿呀,又黄又浓的河水从低处扬向高处,又漫进田垅,田间麦谷青葱,远处黄土映照,白云蓝天下,也许只有这偌大的天轮的转动才可以匹配雄浑的河流?所以,兰州人把这种从江南引进过来的水车称“天车”。
不过也有人认为,兰州水车既非从西南引进,也非始于明代,公元907年至960年间的五代时期,“大食”,也就是唐代所指阿拉伯帝国伊本·墨哈墨尔所作的《游记》中,就载有“中国王城”也就是今甘肃张掖古城用水车灌田情况。我认为两种说法都对,只是五代时期张掖的水车形制与引水量可能都小了些,关键还是没有直接架在黄河之上。支流和主流的推动力,究竟还有差别。
与南方龙骨水车不同,兰州水车酷似巨大古式车轮,轮辐直径大的近20米,小的也有10米,可提水达15米至20米高处。轮辐中心是合抱粗的轮轴,轮轴周边装有两排并行的辐条,如自行车辐条,每排辐条尽头装有一块刮板,刮板之间挂有可以活动的长方形水斗。轮子两侧筑有石坝,为了固定架设水车支架,也是为了从水车下面聚引河水。而在水车上面,则横空架有木槽,水流推动刮板,驱水车徐徐转动,水斗则依次舀满河水,缓缓上升,当升到轮子上方正中时,斗口翻转向下将水倾入木槽,由木槽导入水渠,再由水渠流入田间。
天车虽然提水量不大,但是昼夜旋转不停且不费人工,从每年三、四月间河水上涨开始,到冬季水降,一架天车,大的可浇六、七百亩农田,小的也能浇二、三百亩,所以甫一出现,就受黄河两岸百姓欢迎,上至贵德,下至宁夏中卫,都可见天车身影,成为黄河沿岸唯一自动提灌工具。
至1949年,这种天车在兰州发展到361架之多,9万多亩水浇田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对于解决沿河旱地农人的吃粮问题,其作用无疑大如天。1955年农业合作化时期,天车架数下降。以后,天车先是被以煤做燃料的锅驼机抽水替代,以后又是柴油机、汽油机,以后又是电机。从小马力到大马力,从单机抽水到沿河一系列集发电、灌溉的水电水利枢纽建成运用,天车终于退出历史舞台。
黄壤时代和它的董志塬
地质年代结束,海洋退后,广袤无边的盐卤之地成为中华儿女生息繁衍的家园,是因为黄河。黄河搬运造陆不止,是因为有黄土高原。
天造地设。为了成全黄河一个新大陆的梦想,上天在让青藏高原横空出世后,与蒙古高原同时,又赐以黄土高原。
河套贺兰山以东,晋陕峡谷太行山以西,长江与黄河的分水岭秦岭以北,及青藏高原东缘4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耸起成为华夏神州继喜马拉雅之后的又一高度。
正如美国诗人弗罗斯特所叹美国西部比美国更早诞生了百年,而我们的高原呢?像它孕育的黄河,她成为中国国土比属于她的人民更早10万年,百万年,它高原属于黄河,或者说黄河属于它,它属于中华儿女,则更早千万年。
地质学家站在甘肃永靖距岸 80 米之下的河面断层,指着黄河切开的“天书”给我们看—离河面最接近的是河溯流侵蚀刚切割完成的由泥沙形成的河湖沉积层,那是三千万年前还没形成上下一统的黄河在孕育生成时古湖留下的痕迹。再往上是古地层,再往上是马兰黄土,以现代技术测定,那是黄土高原形成之前落在黄河岸上的第一层黄土。距今大约2200万年。
有关黄土高原成因,有风成说、冲积说、洪积说、冰川说等多种解释。
1925年,李仪祉根据德国人李希霍芬著述,对中国黄土形成画出较为清晰的轮廓。
2200万年以前,青藏高原反复抬升以至最终崛起为今天的高度,汾渭古湖上下系列古湖作为最早的黄河胚胎,因喜马拉雅崛起而溯源冲刷,开始上下贯通,逐渐隆起的青藏高原阻挡了印度洋水汽,亚洲内陆从此陷入干旱。气候变干,湖泽消逝,中亚西亚到中国北部成了一个广大的沙漠。
强劲的冬季风在风化后的沙漠卷起沙尘暴,沿青藏高原边缘持续向东推进,在今天甘肃、陕西、山西境内,遇到六盘山、吕梁山、太行山、秦岭阻挡,沙尘颗粒在山脉之侧不断沉降。这样经过几万年、百万年,沙尘落地,植被生长,又被沙尘掩盖,又生新的,又被掩盖,循环不已。距今260万年前,沙尘沉降更加剧烈,不起眼的小小沙粒,居然在地表上堆积出巨厚的黄土,最厚之处可达600米,包括黄河的河漫滩,包括城堡状的丹霞地貌,包括条状交织带地层。地质演变进入了黄壤时代。
业界一般把早、中更新世的沉积称老黄土,也称红色土,晚更新世以及以后的沉积物称黄土或砂质新黄土,也称马兰黄土,覆盖于老黄土之上。
根据黄土呈现的岩性及结构剖面的一致性,分布的连续性,多层重复埋藏以及粒度由西北向东南逐渐变细的方向性等,专家推断形成黄土高原的地质营力应该是:不受地形条件的制约,源于同一区域,具有相同方向的作用,就是以中国北方常见的西北风为主导,将远处的黄土物质搬运而来,源于同一补给区。
这些判断,在中国古籍也能找到例证。《汉书·五行志》记公元前32年的成帝建始元年四月,“壬寅晨,大风从西北起,云气赤黄,四塞天下,终日夜下著地者黄土尘也”。说明黄土是由西北风带来的。
青藏高原是一群弧形山脉构成的高地,其间是大小不等的纵谷与盆地,黄河穿过这些山脊与纵谷,因底岩软硬不同,谷宽常有变化,遇红色岩系,谷盆就扩大成盆地,遇到硬岩,河道就缩窄成峡,如贵德盆地西缘的龙羊峡,盆地以东的松巴峡和李家峡等。黄河由中卫县黑山峡峡口的沙坡头至河口镇,多行于宽广冲积平原中,由黑山峡至青铜峡为卫宁平原,青铜峡至石嘴山为宁夏平原,三盛公以下为后套平原。
从托克托到龙门,黄河在晋、陕交界峡谷中奔流,逐渐斜过吕梁山脉,亦即穿过汾渭地堑西北面的断层崖。此区新生代地层黄土、红黄土及红土的发育,虽不及陕甘黄土高原深厚,但因雨量较大,又为泾、渭、洛、延诸水及清涧河、无定河等枝状水系所割切,成为岭壑纷繁的崎岖地形。以下呈东西向的黄河与走向东北西南的燕山褶皱带相交,河道主要沿着某些断层破碎带以横过,如遇较坚硬岩层,就构成大小不一的峡谷,如三门峡、王家滩、任家堆、八里胡同、小浪底等。
地质时期,黄土高原古地面为黄土所覆盖,并经地壳运动以及气候变化和多次水流侵蚀割切,形成了黄土高原地区塬、梁、峁自然景观。宋沈括《梦溪笔谈》说:“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今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亦雁荡具体而微者,但此土彼石耳。”
铁森对黄土高原地貌的描述则是:“沟壑复曲,有如迷境,崖土矗立,如壁如柱。”
以董志塬为例。董志塬位于庆阳中南部,地处泾水之北,马莲河和蒲河两大河流之间,塬面面积 910 平方公里,约合 9 万公顷。南北最长 110公里,东西最宽50公里。
这是黄土高原形成又被切割后,目前整个黄土高原上最大的塬,是西周“太原”被分割后的残余部分。即便现在董志塬已远不是西周“太原”,即便仅庆阳境内的塬也被切割成孟坝、临泾、平泉、西华池等11个小高原,使它们如手牵足立的一母同胞的兄弟,又像一个极不规则的叶片模样,与千沟万壑的广大高原相比,它的塬面也仍然平坦而宽广,不仅在庆阳黄土残原中排行第一,而且在全国所有黄土高原的残原中,仍然是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土层最厚。这座“ 天下第一塬”,因雨量充沛、日照充足、气候温和,自先周至唐宋至今,“陇东粮仓”之美誉历久不衰。
因为要绕道。要绕过那些沟壑,直线距离十里就可能变成了三十里、五十里了。原先一个时辰抬脚就到,现在驾着方向盘也得跑一小时还多。
如此尴尬,史念海先生就曾遇到。
史念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教授,1972年,他受命查勘西北军事地理。军事地理离不开疆场营寨,取水开泉,运粮道途及古堡关隘研究,如汉时“陇坻之隘,隔阂华戎”的陇关及萧关,由此开始了他持续20年之久的高原田野调查。而让他没想到的是,在完成有关军事地理考察期间,他的兴趣已从军事地理转向《黄土高原历史地理研究》,以煌煌百多万字的《河山集》而成为黄土高原研究的一代大家。当他考察董志塬上最大的城镇时,发现西丰镇这个地方,现在已夹处东西至少5条沟头之间。
曾几何时,大原被分割成小原,原又分割一道道“梁”,“梁”又分割成一座座“坪”或一个个“峁”。浑然一体的一个“太原”终演变成千沟万壑。黄河功在造陆,造陆缘有高原。天生一条大河,天生一个高原,由此才成就黄河子孙得以庇佑的皇天后土啊!

个人简介:张中海,50后,山东临朐人,业余诗作者。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继业。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上世纪80年代有诗集《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5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两种。另有短篇小说《青春墓志铭》《一片光明》、传记文学《一个空战老兵的非凡人生》《黄河传》多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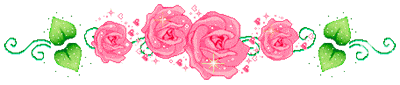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