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这是作家张炜在新作《河湾》中富有哲思的一句话,作品中主人公的蜕变更值得读者深思。《河湾》是作家张炜沉潜5年后的新作,花城出版社以极大的诚意与之合作,出版前后下了不少功夫。作品面世后,在读者中间产生热烈反响,还入选多个榜单。百道网专访《河湾》责编李嘉平,请他讲述作品出版过程,同时挖掘作品背后的深意。
《河湾》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
作者:张炜
出版时间:2022年06月
一年前,经过文学评论家何平的牵线搭桥,花城出版社第一时间了解到作家张炜正在闭关创作一本长篇小说——《河湾》。2021年冬天,花城出版社的编辑们两次前往济南拜访张炜表达出版意愿,热情沟通,使得张炜对花城出版社给予完全的信任和帮助,将沉潜五年的作品交托出版。花城出版社高度重视本书,不仅为《河湾》安排三位责编,从社领导、责编,到营销发行设计部门的同事,花城整个团队都为本书的策划出版付出心血。
2022年6月,《河湾》甫一上市,就在京东长篇当代小说榜、当当小说飙升榜排行第一,入选《光明日报》《新周刊》“腾讯好书”“百道好书榜”等十几个榜单,获得《光明日报》《南方日报》《大众日报》等数十家媒体的宣传和推荐。在女性用户占大多数的小红书,仅一条推送就获得了数十万用户的阅读,相关推送阅读量预计总量超过百万,让本以为小说主要吸引男粉丝的编辑们格外惊喜。大家的努力最终收获了回报,图书库存告罄的速度远远超过了预期。
《河湾》为什么好看?百道网专访《河湾》责编李嘉平,作为除作者本人外对这本小说最了解的人之一,他对《河湾》亮点与深意的解读值得每位读者品味。

《河湾》责编 李嘉平
如果把张炜的写作比做一条长河
《河湾》就是河中回漩迂曲的景观
张炜通过他的笔,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审美拓进,深受中国当代阅读者的尊重和喜爱。他近五十年个人写作史,亦是一部微观的长篇小说艺术发展史。作为一个思想型的作家,张炜的每一部长篇小说都进入到历史纵深,瞰视现实全体,回应并反思时代和人性之变。张炜表示,这几年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段极不平凡的岁月,《河湾》就是他在新时代最新思考的结果。
他在《序》中如是写道:“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自己走入了精神和心灵的一个关口,正面临最重要的一次抉择。”“我记起青年时代读到的一部直率而痛苦的书:关于社会的最小单位,即家庭之书。它记下了时代的椎心之痛,以及人生的至大诱惑。至今难忘那些热烈和冷峻的面容,他们的徘徊与决绝。”“我也在讲一个致命的诱惑的故事。像过去一样,讲述一定伴随了自我拷问,经历一场灵魂的洗礼。如果不是如此,写作将变得轻浮。”“人们常常讲到苦难的家世和良好的教育。可这一切未必等同于良知。”人的一生仅仅对得起自己的经历,也将是至艰至难的一条长路。在即将耗尽的长夜,在黎明前,张炜通过《河湾》和读者做最后的长谈。
而书名为什么叫做《河湾》?张炜没有公开做过明确的解释,但这是所有读者们肯定会思考的问题。学者贺仲明曾在一篇题为《退却中的坚守与超越》的文学评论中指出,从最初的“芦清河系列”开始,对自然景物和动植物的精细描摹已经成为张炜作品最显著的特色之一。此后,张炜作品中的 “自然”内涵更为丰富,他有意识地将 “自然” 与 “野地”、“土地”和 “生命”相联系,赋予其“自由”、“浪漫”、“神性”、“生命力”等精神特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链接于人的根本生存方式。显然,在这里,自然已经升华为一种精神,已经与人类的生命状态、与人和自然的基本关系相沟通。
李嘉平认为,河湾,在小说中是主人公傅亦衔告别生活的终点和重建生活的起点。主人公的好朋友余之锷、苏步慧夫妇在事业成功之后,选择到山林中寻找自我生活、生长的居所,河湾就是他们的收获。然而,在现实面前这个理想没有想象的坚固,傅亦衔看到好友因为失败而消沉后,决心与自己过去的生活告别,接手了朋友的荒败的河湾,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新生活。“这是一个不断重复和累叠的欲望的世界,各种欲望。这是一架大功率的粉碎机,它借助人性的特征,就像遇到了一堆干柴,很容易就把它们打成了粉末。既然是一棵草,我们还是浸到水中,比如河湾那样的地方吧。”张炜在书中这样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河湾”一词的本意是河流沉淀和转向的地方。李嘉平介绍称,北京大学陈晓明教授曾说过《河湾》是张炜的集大成之作,兼有内敛和飘逸的风格,是张炜美学气质的总结;而南京大学张光芒教授则认为《河湾》是转向之作,即张炜从心史到当下,从知识分子到个体心灵立场的写作转向。“这两种说法分别讲出了《河湾》厚积和转向的地方。如果把张炜的写作比做一条长河,《河湾》就是河中回漩迂曲的景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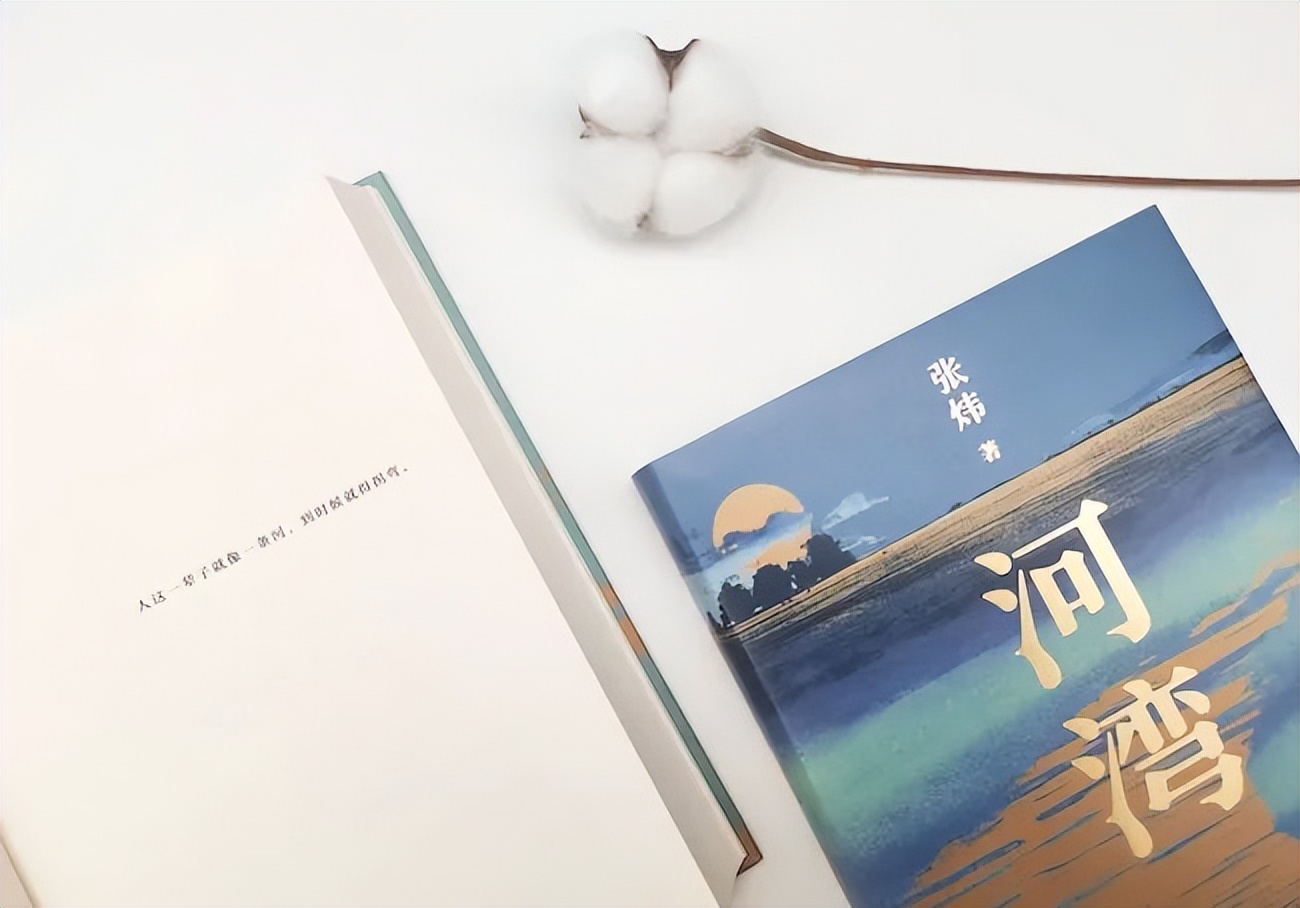
我可能会把《河湾》看作一本“奇书”
因为它既有历史的奥秘,又富含现实的奥秘
张炜在一次活动里谈过创作《河湾》的体会:“我要尽可能真实的记录‘我这一段生命的河流’。每个人的每一段生命的河流都是不同的,不会重复,重复是因为你不愿意动脑,你不诚恳,你想把你讲过的话再讲一遍,应付一次,搪塞一次。”
写作是作家存在于当下的方式。张炜在创作《河湾》期间关掉手机,须发皆长,体重下降了20斤,被朋友笑称是“躲在山洞里写作”。而在他的《河湾》中,主人公“是从流浪之路上走来的一个少年和青年”,一路跋涉,一路追寻。这两个形象启发了李嘉平,“隔绝和外出,对作家来说是不矛盾的,写作就是张炜孤身一人与此刻世界的交谈,是他居于陋室的孤独远行。”他说。
几十年来,作家张炜总是不断以其颇具个人风格的创造带给中国文学以新的惊喜。逃离与回归、漂泊与救赎、现实与浪漫、批判与礼赞,这些丰富驳杂而多维的精神主题,构成了张炜小说的哲学思想深度和诗性抒情风格。从《古船》到《你在高原》到《独药师》,张炜惯于在家族史和社会史的结合点上展开叙事,偏爱追问当代社会的历史由来,可以说,他一直从事着史诗性的写作。史诗意味着所写的人和事发生在写作之前,写作以局外的观照和记录进行着。史诗性在《河湾》当然也有体现,如主人公曲折苦难的家世,以及他本人成年以前在齐鲁大地上的奔走本身就极富寓意,也都促使他为今后的人生奠定了寻找正义的主题。
与史诗相对应的是另一种写作。李嘉平谈到,在编辑《河湾》的过程中,他的一个明显感受是这部作品具有很强的“当下性”。“《哈姆雷特》有句话,‘天地之间有许多事情,是你的睿智所无法想象的’。相比而言,《河湾》中的生活写于当下,写于此刻,这种生活存在着更多的扑朔迷离之处。真实的人也必然会有这样的感受,即我们对生活的真相总是后知后觉,对待眼前发生的事总是手足无措。”
《河湾》中的生活表象,如恋人洛珈的美,“暴发户”德雷令的蛮横,同事圆圆的唐突,手机、网络无处不在的喧嚣,无不对主人公傅亦衔造成震颤;尤其是洛珈,无论是她“凌驾于他人的理解之上”的魅力,还是后来成为“手眼通天的人”,都似乎无法被傅亦衔真正触及或者干预,虽然两人有相似的家世和十几年的隐恋,但仍然是两座彼此陌生的孤岛。李嘉平表示,在读到小说结尾之前,你可以为河湾的失落想出很多理由——一场山洪、一次资金危机、一场车祸、一个城市开发的项目,但河湾最后就毁在了一件不大不小的情事上。“围困《河湾》人物的更多是现实的这些纷纷扰扰。作为读者,我可能会把《河湾》看作一本‘奇书’,因为它既有历史的奥秘,又富含现实的奥秘。”李嘉平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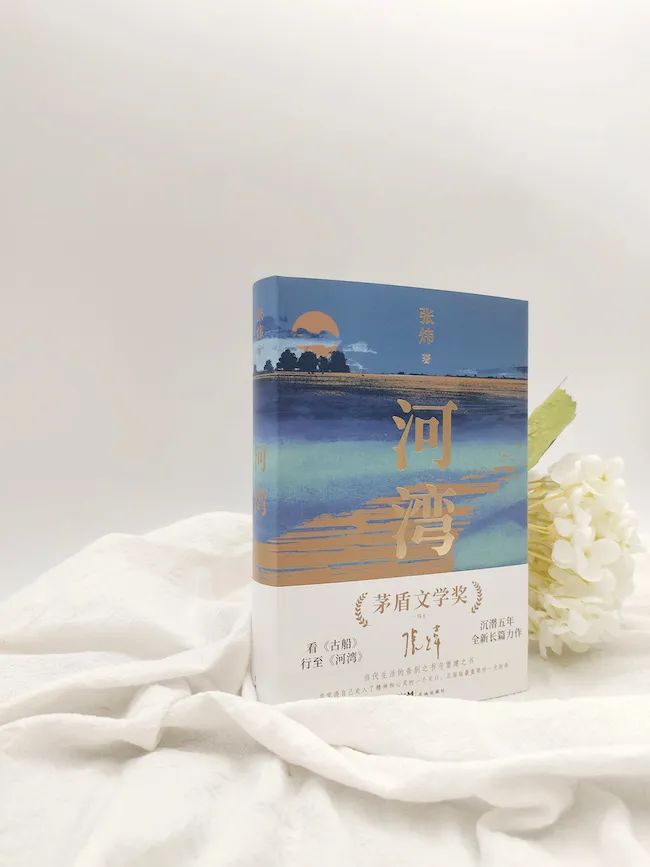
外界的变化不可能因为人的意志而停止
所以“到时候就得拐弯”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指出,《河湾》体现了张炜在艺术探索方面的热情和对中国当代社会变迁、对中国人精神变迁的独特思考,具有丰富的思想和艺术含量。花城出版社社长张懿也表示,张炜多年来始终高扬严肃的人文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情感,思索着时代和人性的变化,他的新作《河湾》让读者感受到作家在创作上不断积淀、不断探索的转向,融会了古典的风骨和现代的精神。
《河湾》中,“精神”一词让大家想到张炜悉心描绘的“高人”和“异人”。他在书中解释称,“他们是难以遇到,也难以被复制和学习的人,能够在时代从众的潮流里,脱离到一边去过自己的生活。高人,最能够摆脱潮流,最能够活出自我,最能够在各种各样的热情、语言、动作、思想以及强烈的诱惑冲击之下,回到自己的角落进行思考和判断。”小说主人公傅亦衔在体面的表层生活下追寻超脱凡俗的“异人”,在目睹好友的挫败和恋人的蜕变后,独自走向河湾重建生活,走向了“异人”。
在李嘉平看来,《河湾》里的“异人”,比如初见时的洛珈,城市中的隐士何典的内心都有着一以贯之的个人追求,但这不妨碍他们生活在世俗中。“这有点像是溪流里冒出的石头,你知道它们在流水中保持静穆需要毅力和定力,不过你也不会认为这些石头要刻意地与河水搏击,高出河水一头。我想使异人成为异人的是专注、独立、宽容等等这些内在的品质。虽然名字叫‘异人’,他们的那些品质反而是最传统,最被人们需要的。”他说。
在张炜独特的由民间、大地和苦难的记忆构筑起来的艺术系统中,读者不仅能从中感受到自然的温情和浪漫、言语的从容舒缓,还常能读出一种激愤和孤傲。不折不挠是张炜小说人物形象性格体系中的一大特征,不过李嘉平提醒我们,如果只有“不折不挠”,那这个人物就是单薄的,他认为,张炜笔下的不折不挠的人往往都是自洽的,你不会感到这个人物“头铁”,他们有自己的命运和生长逻辑,正如史诗中的人物一般。
在《河湾》中,傅亦衔在流浪和书香中度过了青少年时期,成年后生活在机关单位的喧嚣和与洛珈的地下恋情中,追寻着古往今来的“异人”。仔细想想,这个人物的生活虽然发生了变化,内在结构却是相似的:表面平静的机关生活对他而言,是另一种异乡的漂泊,年少时的经历养成了他在喧嚣中“不动如山”,选择用一种隐逸于市的方法继续个人的生长。就像在流浪中的阅读一样,他于喧嚣中经营地下恋情,寻找“异人”也是寻找精神寄托的表现。
李嘉平指出,小说更进一步的地方,是主人公的生活最终难以为继,恋人远去,好友挫败,他在坚石和流水一般的生活中经历种种惊愕和震颤,最终走到了不破不立的终点。他表示,这可能就是现代人的生活,每个人都想要“舒适区”,外界的变化却不可能因为人的意志而停止。
而在新时代,张炜想引导我们思考的大概已经融汇为《河湾》里的那句话,“人这一辈子就像一条河,到时候就得拐弯”。
作者:刘瑞丽
编辑:道之
终审:令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