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县记忆
张中海
和滕县的交集是上世纪80年代初,1983年底,作为民办教师的我,从老家临朐的一乡村联中到滕县七中任代课教师。想那个年头,改革开放大潮风头正健,最早感觉到春江水暖的行者,已开始把探索的触角涉及到曾经铁板一块的人才使用、人才引进等制度的禁区,继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胜利油田之后,滕县也在全国范围内招聘代课教师。而当时的我,也正像春天到来之前的小虫子,因了河冰的开裂抑或远处闷雷所发出的声响蠢蠢欲动,但又没有小虫子的果绝与一无反顾。所谓“昏鸦三匝迷枯树”,先是西域奎屯农七师济南面试缺席,后是油田孤岛东方红中学放弃,再后,滕县也辞了。可是,神差鬼使,辞信刚刚落到也是诗歌评论者的滕县教研室主任王牧天桌上,我人也到了滕县。由此,你就知道了我以后《奥巴马与张中海》一诗说奥巴马“打着左转向灯,又右拐”的两难困境了吧?
人,任何人都常常陷入这个困境。
“不能去七中。”王中斩钉截铁。
怎么不能去呢?我疑惑的看着黄强,不明就里。
“让他写诗。再去教书不把这人瞎了?”王中把头转向黄强:“咱一人10块凑点钱做中海的生活费至多俩月,让他到文化局专职创作。”
这时的我也许才明白,目标代课教师的我,怎么偏偏被黄强领着先进了文化局的门。
哥哥!万万使不的啊哥哥!我当时虽然没有叫出声,但我致明澈白的是:诗友黄强在运输公司,文化部门的专职写作人员不可能容纳两个写诗的。也许看到了我的忧虑,他又强调:“一个一个的办,会给黄强安排好的。”看黄强也连连点头我就更急了,态度坚决:“这就走。一霎也不能再耽搁!”我怕天生意志薄弱的我最后崩溃,抓起包就外走。王中无奈,叫上他局里唯一的北京吉普,把我送到地处东戈公社的滕县七中。再找上他学校的一个熟人给我买上一摞饭票,这才打道回府。
如果不连胜利油田工会文友王忆惠送我去车站时让我坐的小面包,习惯了庄稼地里推独轮车、至多坐过独轮车、驴拉地排,以后又坐过公共车、火车的我,乘坐吉普,就是农村孩子称做“鳖盖”的“卧车”,这一辈子是头一回。
“咱老辈里就是庄户,庄庄户户的就很好,你还想干什么?”这是老爹常教育我的一句话。我嘴上不辩驳,但心里不屑。这个不屑就源起于老爹这个“反面教员”:好歹打过江去没死,好好的军分区司令部的兵不当,上司撵到火车站硬拽也拽不回,就一心建设娘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你土鏒鼹鼠一样拱一辈子我不管,到头来连我也没有出头之日!
当时我咬在牙缝里就亮个字:“转正”,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进入体制。可能一开始不敢这么想,但随着诗写、教书渐渐有了点名堂,这个念头就浮出了水面。从临朐跑到滕县,目的实无其二。我不愁下地下死力气,读初中时就挣2700个工分,但让我下一辈子庄户,打死我也不干。
所以,当滕县黄强、王牧天老师给我这么一个确切的回答时,我就去了。
为什么在新疆、油田、滕县三家中选了滕县,还有一主要因素是滕县有一群诗友文友——尽管除了黄强别的都不认识。
为什么从原先定好的三中又变成了七中,也是因为文友。语文组同行、七中副校长张明泉先生对我说:“硬让我从王牧天那要来了。”但他没想到 ,他要来的是“麻烦”。
转过年来三月的一天,同样是代课教师也同样有着文学癖好同样和我另一小兄弟一年出生的李伟小兄弟拿着一份《新民晚报》指给我看,是我年前发《萌芽》的《泥土的诗》获萌芽创作荣誉奖的消息。
奖就奖呗,奖之于吾正是吾之欲,但不该借此机会给我等长达一个月还多的公费旅游!他就不知道我的饭碗是泥饭碗?春尾夏初,正是庄稼发身量的季节,且我教的是高中,学子们第二年就要高考,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啊。
所以,当以后任滕县教育局长的张显岱校长明确回答不给我假时,我一点也没有吃惊。
业余作者都知道,业余爱好与本职工作从来就是一对矛盾。这,在我原来执教的青崖头联中就遇见过。虽然我诗作在报刊大量见报的1981年,《人民教育》,还刊发了我有关中学作文教学论文,并且《光明日报》还摘要推介,此前,所谓教学经验还在公社、县、地区会上“讲用”过,甚至1984年全昌潍地区的中学语文教学现场会也要选在我联中举办,但实话实说,相比创作,我用在教书上的精力还不到50/100。以至到现在,还常常从恶梦中惊醒:学期即将结束,我一册语文却一课也还没讲!刚刚成为网红的把“鸿鹄”念成“鸿浩”的什么校长还算什么事?我和他一派,我就把“桃花流水鳜鱼肥”的“鳜”教成“撅”……
看着刚寒假开学就从老家公社办公室转来的电报通知,明泉先生声 音柔和温润又洪钟一样余音袅袅:“想去不想去呢?”
“想去”。我回答自然怯怯的。
“那你就先向显岱请假,不行我再和他商量”。
预料之中的“不准假” 。预料之外的则是刚刚拒绝了我的校长,第二天又笑呵呵的招呼我去他屋:“明泉说这是个荣誉,也是个机会……他说他替你上课……40多天,可不是个短时间哈!出去可要好好学习啊哈!”拍拍我的肩,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解决了。
退休之后才开始文学创作,写出并出版一本散文一部长篇小说的明泉校长完成自己一生宿愿,这是后话。由关明泉校长给我的人生榜样,在我为他撰写的序文中已做记述,在此不赘述。正是明泉的挺身而出,一下子让我摆脱困境。听到我能顺利出行的消息,黄强、王中他们这才松了一口气。
上海、安徽、浙江,黄山、九华山、铜陵游山玩水还不到一半,我就外面待不住了。半路回来,是想着教室里那一群第二年就要高考的学子,还是想着文化局长早答应了的“班”?或许兼而有之。上海行前,王中又把我领到了局长商洪度面前。什么也没问,商局就说:“这里已给你安排,回来就到局里上班就是了。”我梦寐以求的文化馆创作辅导员临时工,在我想也不敢想的时候,就降临我头上了。
许是本来就不该无功受禄,上海一行回来,正值1984年开始以学历换干部,只几天功夫,商局变李局,尽管王中已被新任局长指“组自己班底,”他也还是苦口婆心:“原来商局定了的……权当我们白捡了这么个人。”那也不行。不行就是不行。尽管已经不行,王中还是让文化馆专业摄影师,給我大大小小照了一摞照片,伟人像一样摆了滕县大街长长一溜橱窗。让我这个“外省人”,让我这个刚从外省回来的“滕县人”,平生享受了唯一一次衣锦还乡的虚荣——虽然这个锦,还是土布、又比身量大出二指的大襟褂子的“襟”……

图说|1984年的文学故乡,那个美好的年代
左起:张中海、侯贺林、王中
我在滕县只待了一年。我走几年后,千方百计让我在滕县扎根的王中、黄强、海城包括李伟等也相继离开了滕县。但滕县一年于我人生之意义,在以后的日子中,我曾无意中做过比较,如果说临朐仅仅是标准的乡土文化,作为曾经出过“民国第一案”、出过铁道游击队,离水泊梁山又不远、铁路线早通了的古滕国,那就是既富古道热肠,又富商业精神、又富南蛮的现代文化于一身。滕县一年,于我人生之意义不可或缺。以后我在新的供职单位跑经营,顶头上司说我多大的官都敢打交道,这不都是明泉为了给我解决饭碗问题领我去枣庄找他熟人官员,王中领我直接闯进县委书记家的做派?带经营队伍,千方百计让农民工吃上饭,不都是明泉先生既当校长又带两个班语文,又为我挺身而出的翻版?之于帮助别人,真的比王中先生差老大一截子了。包括我在内的滕县黄强、侯贺林、吕宜芳等等多少工农出身的业余作者,谁又没受到他的强力援手?如此说来,王中是何等神通广大的人物?就是一个县文化局创作组组长,股级干部?一级编剧,地主黑五类子弟,乡贤文化倡导者,墨子、孔子文化研究者……如此所谓“成功人物”,要么成为冷酷的个人奋斗者,要么成为人道主义者,滕县王中、明泉先生,显然是后者。
而在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明泉先生老家并不是滕县,这个大学毕业就在滕县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宁阳人,其豪侠与儒雅,没一点比滕县人逊色。文化需要传承,相比上述两位,我作为两位上下代的“中间代”,实在是惭愧。
七中宿舍是秋天刚起的新房,还没上梁前被连阴雨灌过,所以我进去时四面墙壁全是一层冰。手指头肚一抹,那凉、那滑啊!当我把所有从临朐带来的家当:一床被褥、一个草褥子套、一本《汉语大辞典》放下,又在李伟带领下,去邻村场院一个麦穰垛上,把草褥子鼓囊囊填满,那就觉得我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的窝,是暖暖和和了。不是吗?茫茫人生,大千世界,生死可交,冷暖自知。多少年之后我还清楚的记的我去滕县那天的冷,真冷。以后又发现,那一天是冬至,农历的双十一,光棍节,恰恰30年前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骑车和黄强去文化局看素未谋面的王中的路上,车辆行人不多,路也没坑坑洼洼,但不知为什么,我连人带车摔了个狗啃地。跌倒了,肯定又爬起来了,而当我再爬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把我打倒——除了疾病、衰老和死亡……
2017.11.19草于黄河口
2018.6.10改

简介:张中海,1954生于山东临朐,业余诗作者。
落生时挨饿,上学时停课,没毕业就业。1970年代以农为业,诗为余;80年代以教为业,诗仍余;90年代以商为业,余不见。后业终,余存。余孽。
最后一代标本式农民;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民办教师)、第一代新兴资产者(“二道贩子”)。上世纪80年代末有《泥土的诗》、《现代田园诗》、《田园的忧郁》三种;2016年后有《混迹与自白》、《雁哨》五本诗集。另有传记文学《黄河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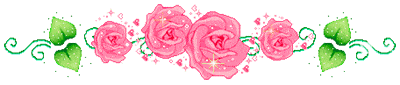
图书出版、文学、论文专著、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