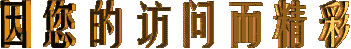王燕生,生于1934年11月4日,故于2011年3月20日,终年77岁。 系当代著名诗人,诗歌编辑家、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临沂人,系卧冰求鲤王祥第四十九代孙。
1950年1月6日入伍,历任军政大学学员、文工队员、俱乐部主任、宣传干事等。1953年立西南军区三等功一次,1958年被评为铁道兵三级先进工作者一次。1964年转业至湖南省药材公司。1978年调入诗刊任作品组副组长、编辑室副主任。1956年10月26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7年被评为副编审,1995年退休。
1952年开始写诗,1956年发表作品。诗歌《太阳的故乡》、组诗《在新建铁路上》1962年分获铁道兵文艺创作二、三等奖;《解放军文艺》发表的《我知道》被人民日报转载时,臧克家著文予以赞扬;1965年11月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8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出版有诗集《路啊,脚下的路》、《走向地平线》、《亲山爱水》、《岁月之树》、《心形船》;诗论集《学诗十二忌》、《与缪斯的会晤》;诗学随笔《上帝的粮食》;新译新释《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小传、作品被收入百余种辞书、专著和选本。有诗被译为英、法、阿拉伯、土耳其文。
王燕生一生为人高风亮节、铁骨铮铮;为文浩气长存、著作等身;为师严谨细致、誉满诗坛。其人品、学问、师德皆为当世之楷模。他善于发现青年作者,热心培养诗歌新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新时期以来中国诗坛的生力军,他与广大作者和诗人也结下了深厚友谊。他被誉为“青春诗会教父”,一生桃李满天下,为中国诗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 ★ ★ ★ ★
在燕生兄长的告别仪式上,我恍惚着,失声痛哭……很多人理解不了这种“失态”,不知道我们血脉里的“铁缘”。
那是1978年,王老师(平时我还是称燕生兄为师,称嫂夫人李老师)正式调到诗刊社工作不久,便急着找“娘家人”,他当过十多年铁道兵,且在铁道兵机关当过文化教员,血液里有“铁元素”……我很快成为他的“娘家小兄弟”,从此来往频繁,甚至连机关放“内部电影”,我也会请他俩口子来看。
1979年4月,王老师第一次享受采风创作假,可自由支配3个半月的时间。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回娘家”,到青藏线和南疆线走访百日,文化部指派我全程陪同他采访。4月底,高原上还有些寒意,他执意要到最高的关角山隧道去看看那里的战士们。
海拔3874米的关角山,藏语意为“登天的梯”。这里高寒缺氧、人烟稀少,年均气温零下0.5℃,极端最低温零下35.8℃。他听完指导员的介绍,眼眶湿润了,说一定要到炊事班去看看。他看见好大的高压锅啊,可蒸出来的馒头还是夹生的。再看炊事班战士的手,指甲或残缺,或翻卷畸形,那施工一线的情形就可想而知了。他要再到洞口去看看,洞内在施工,不能进,他就趴在路基上,听关角山隧道里的声音。他知道有不少战士牺牲在这里,眼泪就哗哗的淌下来了,滴在路基上……
告别铁十师部队后,我们转到铁七师辖区的察尔汗盐湖,戴眼镜的副指导员带着我们参观营区,都是一色的盐壳结构,腐蚀性强,患眼疾的战士多……王老师接过话茬,说:战争年代,我们是用血肉之躯筑长城,敢于赴死杀敌,而在和平年代,铁道兵是在用血肉之躯筑路,能吃苦,不怕死……说到动情处,眼里闪着泪花,陪同的副指导员也摘下眼镜,用袖口擦拭泪痕。王老师就这样深入部队生活,走一路,辅导一路,为基层部队播撒诗的种子。
一百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就是这样走出了“铁”的友谊,诗让我们结成师生兄弟!行文到这里,我还是称“王老师”为燕生兄,这样更亲近。他不仅著述颇丰,还热心扶植青年,发起办“青春诗会”。那年,他邀我参加第一届“青春诗会”,我因诸事繁忙,请不了假,错失了这次良机。因此事,燕生兄多次责备我:你会后悔的!后来,《诗刊》社“青春诗会”成为中国青年诗人最重要的展示平台,被誉为诗坛的“黄埔军校”。若干年后,我果然后悔极了,认为这是我此生最该后悔的一件事!值得欣慰的是,燕生兄的长子晓笛贤侄接续父亲的事业,在庆祝“青春诗会”40周年之际,继续“舞动青春”!
——李武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