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牧歌
每个周末或节假日,我们省会的大街上就有婚庆的车队走过。这时我的脑海里便有一个头扎红丝带,梳着俩发刷的胖美新娘坐在自行车的后面,向我笑着挥手的画面浮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文革后慢长的社会经济状况并不乐观,工资标准也很低,几百元就能办个很不错的婚礼,普通人家的婚庆也不过是在饭店,或家里摆几桌酒席,请请亲明好友。旅行结婚才兴起不久,算是前卫我赶上了。大多家庭的婚车就是自行车,司机则是新郎,还必须亲自骑车驮着身穿鲜艳服饰的新娘,接走了再送回来。服饰变化也不大,穿件红衬衫或红毛衣即可。头饰简单,扎辫子的也就换个红丝带,留短发的沒啥头饰,顶多带个亮色塑料发卡,穿裙装的新娘都很少见。
这个常常浮出我脑海的坐在自行车上笑的象花儿一样的新娘,就是我童年时一起玩大的邻居中三个亲密伙伴之一平平。她小我两岁是我们仨中的小妹,身体最胖也是模样长得最好看的漂亮女生。初中毕业就顶替巳故父亲指标上班了,在离家不远的邮局有了正式工作。在那个工作岗位奇缺,大量知青无法安排工作而上山下乡的年代,是多么的让侧目,也是待嫁姑娘可以骄傲的硬条件之一。她很爱美,为了遮掩自己的粗腰肥腿,常穿类似现在韩板样式的裙子,上短下阔巧妙掩饰了不足。白净的脸上长了一张樱桃小嘴,淡施烟脂,胖也美的养眼,我俩私底下常取笑她是胖美人'杨贵妃'。
她的父母虽是工薪阶层,但在那个物质匮乏,大多家庭錢少多子的年代,独生子女是大家眼中多么羡慕的存在啊!除了她自己,我们都知道她是被收养来的。邻家女生们常常羡慕她有好得吃,好得穿,包括她的胖。我家兄妹两个都够让邻居大妈们羡慕了,一有人说我家干净,马上有人打叉,人家家里几个张嘴的,你家几个?几乎每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六七个的也不少见。我们三姐妹中的老大叫玲玲,大我两岁,家里兄妹五个,她是唯一女生。虽排行老二,基本上是老大,手也巧啥活都得干,经常为弟弟缝补衣裳,织线衣袜子,颇有大姐的风范。我俩家住斜对门,闲暇时我也经常帮她照看她的弟弟们,带着一起出来玩。
她家有一个大通铺,也就是砖垒的土炕。是我们三姐妹经常活动的地点。她高我一个年级,也大我两岁,懂的事多负责讲故事,我负责梳头,每天约好去的时间,带上几种颏色的玻璃丝头绳和小镜子。我会编当时流行样式的各种发辫,胡同里一群女生沒人可比,被大家认可是最好看的。我们之间谁做了新衣服也经常换着穿,胖妹穿不上就和我们换着带围巾帽子,好的无话不说。也不知在什么时候开始对胡同里的男生有了心思,经常在一起悄悄说一些不可告人的小秘密。
一天,老大提议每人自己写一张纸条,写上你最想嫁的男生名字,还必须发个毒誓,不说实话怎么怎么……当我们展开三张纸条,居然写的是胡同里同一个帅哥的名字。一个和老大同年龄,同学校的军属子弟,居委会主任的儿子。这小伙在当时那可就是现在的高富帅啊,他家的政治背景在胡同里红的发紫沒有之二。哇!羞羞,我们三个同时背过身去,一起说了不论谁和他有缘不许嫉妒,互送礼物的话。我承认真的忘不了那个年代那个身穿军装,肩背军挎,左臂佩带红卫兵袖章的俊俏男生,不止一次地到过我的梦中。
随着年龄一天天增长,家长们着急起来,我家第一个幸运地接到那个帅哥家长递出的橄榄枝。而这时的我,反而沒了先前的感觉,用现在话讲就是不来电。怎么拒绝成了难题,碍于人家一片真情,我把他介绍给了我的已在医院工作的闺蜜同学,箅是婉拒了。我仨中的老大,高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去了离市很远一个叫虎家滩的山区。走的那天我和小妹送了她。虽然她笑着和我们道别,我知道她是带着内心的隐痛走的,她是真的爱他,我也知道他是真不爱她。缘分这事永远猜不出结果,真想找个机会问问那个当年的帅锅可否知道,近在咫尺间,有三个曾经为你心动过的女孩。
我们仨中的胖妹整天乐呵呵的有点沒心沒肺,估计早把这事忘记了。第一个把自己嫁了出去,好让我俩羡慕。那个天真纯美的新娘画面就是我俩送她出嫁时的场景。虽然嫁的工友非富非贵,但写在脸上的幸福说明了一切,那年她才二十岁。我真佩服在那个提倡晚婚晚育的年代,她的超前意识和胆量。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胡同也早己拆迁,大家各奔东西,那些年通讯也不发达,几乎沒有了联系。但是那个扎着紅丝带,穿着紅裙子,坐在自行车上笑的美新娘向我挥手的画面却时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宋霞,网名牧歌,河北省石家市退休教师,曾获省级优秀教师荣誉,爱好文学并有多篇作品发表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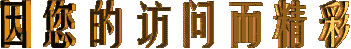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