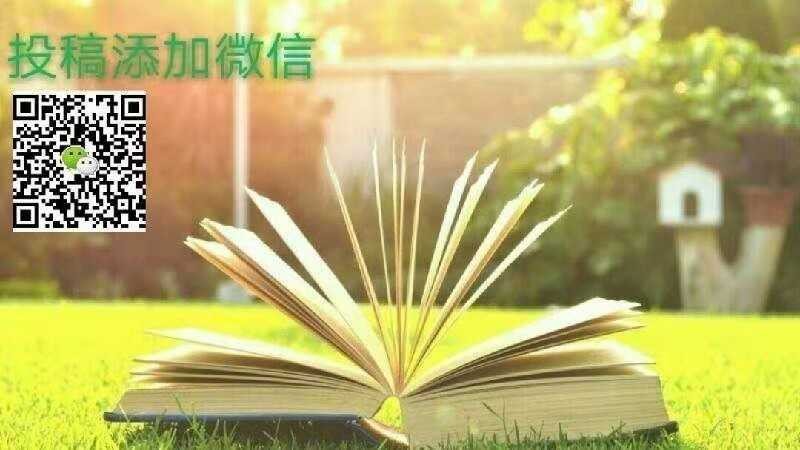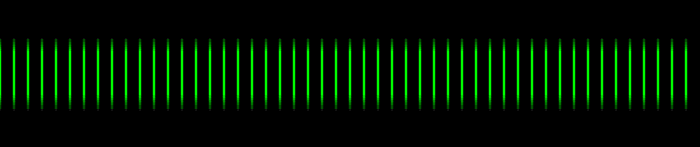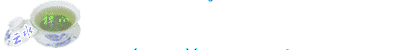作者:柳泽生(辽宁阜新知青驿站)
推荐:白云溪
上工哨声
下乡第一天,我们4个小青年,看这也新、看那也奇,反正是看啥都新奇,忙忙碌碌地很快就到了晚上。
青年点的房子还没盖好,我们就临时住在老包二哥家的东屋。也许是白天太累了,虽然是新环境,第一次睡在农家的土炕上,但是哥几个倒是自来熟,倒头便睡,睡的特别香。
睡梦中,突然被一阵阵嘟嘟声和喊声惊醒。朦胧中那嘟——嘟——嘟——的哨声竟是那样清脆、嘹亮;那“上工啦——上工啦——”的喊声又是那样雄浑、震撼。在一阵阵哨声和高喊声中,我们哥几个不情愿地爬了起来。 屋外,开始传来踢踢踏踏的脚步声和老少爷们相互见面粗声大气的打招呼声。小山村中心,姜品卿家门前有一个高高的老式井台,白队长高大的身躯和那吹哨子和高喊时的姿态,就像一个轮廓分明的剪影,矗立在晨曦微明中。白队长,名叫白洪恩,当时五十多岁,高大魁梧,典型的蒙古族汉子,多年的生产队长,在社员中特别有威望。
沉寂了一夜的小山村,在一阵紧过一阵的哨声中、在一声高过一声的喊声中,开始了一天的新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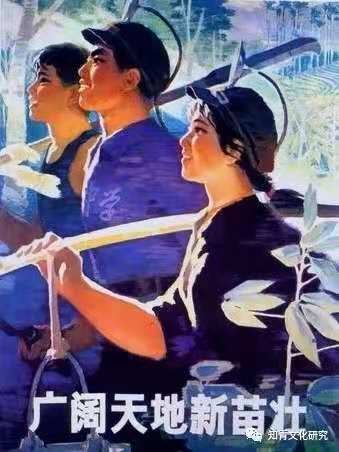
五十年前,这里是萝卜沟村的中心,从西到东是 队长白洪恩家,车老板白洪瑞家,会计姜品卿家。现在这里已经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五十年前,阜新西北部的农村特别困难。像我们这样有三十几户百十口人的生产小队,连一块手表都没有。全生产小队只有两户挺像样的人家有钟,也是那种历经岁月剥蚀,锈迹斑斑,打土豪、分田地时分来的老式座钟。当时农村除了到公社去赶汽车、孩子上学、去参加会议外,几乎没有什么事需要比较准确的时间。当地社员,几乎都有“看天知时”的本事。看看太阳的高度、瞅瞅大山的阴影,基本就能说出个大概的时间。有时,可以精确到3~5分钟之内。时间长了,我们这些下乡青年也都有了这“看天知时”本事。当时,一般生产队上工都是敲钟。所谓“钟”,大多数是一截铁轨,挂在树上;少数用的是祖辈传下来的大铁钟。只有我们下萝卜沟生产小队例外,自从白队长上任后,声传数里的哨声和喊声,就成了这里生活中的一景。说实在的,当时看不看点,知道不知道时间,真的没有什么必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就是这么简单。再加上有了白队长,更是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昔日白队长脚蹬青石,吹响上工哨声的井台,如今已经成为靠边站的“古董”
早上,东方刚见微白,哨声和喊声响起,人们齐齐地聚在村头,等待队长的指派、分工;中午,疲乏劲还没过,哨声、喊声又起,社员们打着哈欠、伸着懒腰,凑到树阴下,然后三五成群地奔向工地;晚上(主要是秋收季节),天已漆黑,哨声、喊声显得更响,月色下,上工的人拖着老长老长的身影。就这样,日复一日,周而复始,就连生与斯长于斯的社员们都有点吃不消,更苦了我们这些新来乍到的小青年。好不容易盼到收工,拖拖拉拉地回到家,哪里还顾得上洗脸、洗脚、刷牙。那真是倒头便睡,甚至连衣服是这样脱掉的都不知道。
就这样,哨声和喊声陪伴我在萝卜沟度过了1000来个日日夜夜。转眼50多年过去了,斯事已矣,斯人已逝。但那哨声,那喊声,却仍在我的耳边,不,仍在我的心中回响。

知青吃得苦中苦
文:白云溪
开过荒,种过粮,
伐过木,盖过房,
上过跳,抢过场,
喂过猪,放过羊。
会见过瞎蜢,蚊子,小咬,
捞起过冰水中的小麦高梁,
抡起过震裂虎口的铁镐,
握过比冰还凉的钢枪!

作者简介:白玉凤,网名:白云, 女, 蒙古族, 大学文化, 高级职称, 中共党员 ,退休后受聘于阜新市博大中医院。辽宁省阜新市作家协会、诗歌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都市头条、阜新日报、大山诗刊及网络平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