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活在母亲的智慧里
侯 林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十六年了,而我却时时觉得,母亲没有走远,他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而我,依然活在她的目光里,活在她的生存智慧里……
母亲照
记得每当快要立秋的季节,母亲便说:“立了秋,一早一晚的就凉快了。”于是,我们兄妹立即会从盛夏的燥热与怠惰之中清醒过来。其实,济南的秋天经常会遭遇“秋老虎”,一时半会儿是凉快不起来的,但是有了母亲灌输的想法,就像是打了兴奋剂一般,你觉得一切都有盼头了。而且,不久你就真的感到,一早一晚是不一样了,真有了“秋之为气”的感动了。
展望未来,给人信心是重要的。
后来,几十年后,到了季节,我也会这样对孩子们说的,因为我是母亲这话的受益者。我感到,高明的话语不一定是眼前的真实,但它是未来的趋势,而且它一定是直指心灵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侯林与父母兄妹照
我很是庆幸自己出生在一个平民知识分子的家庭里。我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小学教师。兄妹五人,还有奶奶,依靠着父母菲薄的工资生活。虽则家境贫寒,但父母却有着可贵的文化视野,他们将孩子的读书上进看作头等大事。我从小听母亲说的最多的话语便是“小车不到尽着推”,“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上学。”因而,我们兄妹五人都十分用功努力,个个在班里学习成绩都名列前茅。
回想我这一生,遭遇挫折磨难甚多。初中毕业便因父亲三青团的历史问题而被列入“不宜录取”的另册,“文/革”中在济南柴油机厂饱受政治歧视与“牛棚酷刑”之磨难,能够熬的出来,大多倚仗一位坚韧而富于远见的母亲,我在厂里遭受批斗,一旦回到那个虽则贫穷但充满温馨与爱的家里,一切的烦恼与痛苦便烟消云散了……
而且,即便在这样的环境里,母亲依然鼓励我们读书上进,她常说:“林儿,要相信,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一天,她在居委会里听说距离我家不远的学院街新搬来一位山东大学的教授赵省之先生,立即鼓励我和哥哥前去拜访。我自此常到赵老师家里,借书、请教,得益匪浅。七十年代末恢复高考制度,我与哥哥能够考中,实在是与父母创造一切方便条件让我们读书,还有母亲的督促与坚韧是分不开的。
母亲始终认为自己的孩子很优秀,谈到自己的孩子,她的脸上总是充满光辉。即便我们当了工人之后,她也认为自己的孩子一定会有前途。而每当孩子取得点滴成绩,如在报刊上发表一篇“豆腐干”文章时,总能看到戴着花镜读报的母亲脸上欣慰的笑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侯林兄妹在大明湖上
我们兄妹五人都十分爱美,喜欢艺术,喜欢穿衣,讲求风度仪表,这显然是母亲的影响与基因。母亲爱好文学,酷嗜读书,能弹琴、懂音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家里触目皆是的是《林海雪原》《三家巷》《苦斗》《野火春风斗古城》等长篇小说,那是母亲的最爱,她还订有《大众电影》等刊物。母亲心灵手巧,一切女工均为上乘。记得五十年代,她自己裁剪作了一件旗袍,引得同校的女教师滋滋艳称,纷纷要求母亲为她们也做上一件,母亲毫不推辞,一时间,学校的美女教师皆着漂亮的旗袍上课,但那时,却是有政治风险的。据母亲的同事樊仁孟老师在一篇散文中回忆道:
“和我一起住校的,有位安老师,他比我大两岁,也是济南师范毕业,知识广博,画的水墨画更是一绝。他画的蜻蜓,翅膀透着光,鲜活得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这都是因为他在师范时,受过齐白石学生的指点。有一次,他给宋老师蚊帐的前脸布上画了花鸟,引得全校老师都称赞,爱美的宋老师更是高兴得合不拢嘴。可好景不长,这事被人当成了“资产阶级作风”,宋老师遭到了批判,安老师也受了冲击。那之后,安老师就再也没动过画笔,直到老了,也没再拾起过。”
宋老师,便是我的母亲。
21世纪初年,兄妹随父亲重返刘庄小学
这酷爱艺术与崇尚审美的不朽价值,是我后半生深刻体味的,它是我人生最大的财富。
我曾在《书此以识岁月云》的散文中说:
审美,是我生命的兴趣与追求之所在。
西哲尼采认为,人生有三种样态或曰模式:道德的、科学的、审美的。而最高的,则是审美的。
最重要的是,审美地活着,其乐无穷。
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最得我心:
人难道不是艺术品吗?我们应该像创造艺术品那样创造我们自身。
我常常想:如果你这一生是审美的,无疑,你会比常人获得更多的快乐与幸福,真的不枉来这世上走了一遭。
亦因此,我最终选择了济南的地域文化研究。因为在我看来,以生花之妙笔,志乡梓之美艳,不断地发现和发掘济南这座城市自古以来的价值与美,用以在今日和以后的岁月里发扬光大之,这是济南研究的宗旨与鹄的。因而这一事业在本质上是审美的。
从事济南的地域文化研究,想不到的、实在令我惬意万分的,是实现了我的两个夙愿:审美与做学问。
这些,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应该肇始于母亲的智慧,她的爱美的智慧。
2022年,济南日报刊登李雪萌文章《侯门三秀,斯文在兹》
我曾经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第一次是文/革中在“文攻武卫”的牛棚里,那棒子呼啸着朝我的头部打来,多亏我躲得快,不然早已脑袋开花了。
后来,一位医生朋友对我说:你也真不简单,得了这样严重的病,还能支撑三年。我说:我觉得自己还有许多事情没有做完,还有许多想写的文章没有写出来,我觉得我要活下去,为了我和我的家庭,我还想辅导只有三、四岁的外孙读书。我会经常拿母亲的话激励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天下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关于身体的,我一生还有两个奇迹,一是眼睛,二是头发,我曾经因为用眼过度,眼睛干涩、红肿,根本睁不开眼睛,西医全部看过,一点儿办法没有,我的舅舅魏鍾先生,便是大名鼎鼎的眼科专家,他说:西医是没有办法了。你去看看中医吧。我于是找到中医宫兰芳先生,她是济南近代中医泰斗吴少怀的弟子,吃了宫大夫半年的中药,眼睛奇迹般的好了。
人生一定不能轻言放弃,只要精神不垮,就不会垮的。而一旦精神垮了,那才是真的无药可医了。这是母亲经常告诫我们的,而我得以继承。每得有知己在,我会谈起我的经历。特别是母亲的谆谆话语,几十年如在眼前。
“你给我一个家”,这是电影《搭错车》的经典唱词。
母亲是家。在我们的心目中,哪里有母亲,哪里就是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父母为支援农村教育,由济南城里的制锦市小学、官扎营小学来到西郊区的刘庄小学。其后我们兄妹一同前往。
那里的冬天真冷哟,地面上的裂缝就有寸把宽呢!我和村里的娃娃一起弹琉璃球,抽陀螺,手上冻得满是裂口,最怕那球掉进裂缝里,任你怎么使劲也抠不出来。那裂缝就在学校门外的场园上,蜿蜿蜒蜒像一条条长龙。
母亲连缀旧布套上棉花做成了一个棉帘,挂在小屋门外,然后在屋里点上一个小小的火炉,小屋内就充满融融的春意了。
面帘隔风,竟有如此大的魔力,还是母爱使然?
1968年秋,我从柴油机厂文攻武卫的牛棚里出来,背一床破被回到家中,母亲惊喜若狂,然后,眼含热泪用手切出薄薄的馒头片,下油锅炸,并趁热附上少许一点儿细盐,吃到口里,好香呀,似乎一生没有的美餐,尽管第二天一早还要到文攻武卫报到然后拎一把扫帚清扫厂里的大街,然而,有这一刻就足够了。从今往后,儿子最喜欢的饭食便是这炸馒头片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侯林兄妹在刘庄小学
母亲天资聪颖。他最懂智慧的力量。他常常会告诫我们:“凡事要多动脑筋,不要门里吊不过扁担来。”
母亲性格刚强,不畏恶人,而又面慈心善。她常说:树活一张皮,人争一口气。以此鼓励孩子们要正直,要追求正义。正所谓圣人之教:“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一生不羡慕金钱与权势,只是热衷文化与学问,显然与父母的家教有关。母亲一生见不得受苦人,县学西庑一条街,来我家讨饭的最多,因为母亲从来不让他们空手而归。有人对母亲说:有些要饭的是假的,他们是专业户。母亲会说:“我们是分不清的。”当年在刘庄小学,她为穷学生缴纳学费,而且,很多穷学生过冬的棉衣,都是母亲送的,使得他们免除冻馁之患。
记得母亲的葬礼时,来了那么多的人。有她的学生和同事,也有与她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们,凡是得知信息的,都来了。那日,天飘着雨,人流着泪,为她送行。那眼泪是真诚的、痛惜的;还有的,是悔恨的……
那时,我才蓦然感到:母亲在这世上播酒下那么多爱的种子,如今破土而出。母亲尽管一生清贫,但她是富有的,她拥有着这么多人对她的深深怀念,这就够了。那时,我才猛然醒悟:一个真正慷慨地在人世间播种下爱的人,其实是最富有的。
侯琪、侯林兄弟在切磋
母亲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还有世间最少有的:勇毅担当。
这些,是我们兄妹都自叹不如的。
1977年,高考恢复,我报名参加,却无端被阻,厂里死不讲理,无论如何不肯出具证明(当时还需要单位证明),眼看报名期限要过了,母亲悲愤填膺,于是毅然赴京上访。我会永远记得,那是1月末的一个寒冷的冬夜,母亲拖着病体,夤夜登程(晚上十点的火车),站了整整一夜,才到达北京的。在北京、在我的恩师张伯海先生(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协助下,母亲见到柴油机厂的上级石油工业部的领导,他们批评了柴油机厂的做法,这才使得我能够顺利参加第二年的高考。
侯林与恩师张伯海先生在一起
我会经常想到,世上多少为人父母者,遇到无端的侮辱乃至陷害时,往往空自下泪,委曲求全,有几人能像母亲一样,愤然而起,千里奔驰,不怕引火烧身,不惧恶人权势,为儿子甘愿赴汤蹈火以告“御状”呀!呜呼,慈母之爱,天下至爱。孩儿今日之些许有成,赖慈母心血浇灌也。寸草之心,乌鸟私情,总愧对三春阳晖,为慈母之恩难报也。
母亲在北京上访时写给侯林的信
我知道:这是我几十年来读书、作学问从来不敢懈怠的根源之所在。还有,是像母亲那样充满爱心地活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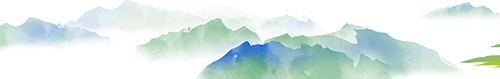



茶水分离 市树市花,扫码聆听超然楼赋
超然杯订购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
丛书号、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