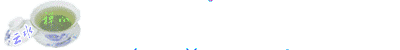那年我们正青春
作者:王锦蓉
那年,是1989年,我们二十岁出头的年纪,正是热血沸腾的时期,我和张云在武汉上大学,小武已毕业、在鄂州一所小学教书。现在记不起是谁的提议,我们三人约好去浠水县巴河镇的望天湖中学,看望高中时的同学小曾老师。
一场艰辛且执着的旅程
早忘记了事先是怎么约的,那年代没有手机没有座机,只有写信,或许就是几封辗转的信,敲定了这场行程。只记得是12月2日星期六,我下午没课,吃了午饭就去小东门长途汽车站,等到张云从市郊的中南政法大学赶过来,我俩一起搭大客车去鄂州。
那时还没有高速公路,大客车一路颠簸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来到了鄂州江边,我们俩盯着窗外不敢眨眼,生怕错过了那根挂着大喇叭的电线杆。小武曾告诉我们,看到那根电线杆就得喊司机停车,下车后走过一小段下坡路,就到了一个简陋的小学校———临江乡小学,我们到达时小武正在跟学生上课,等她四点钟下课,我们才算真正凑齐,又坐公共汽车到鄂州的江边码头,再坐轮渡船过了长江,到达黄州的江边。
这里离我们要去的浠水县巴河镇还有多远,我们并不清楚。向路人打听,有人建议我们坐车去县城转,也有人建议找船从江上去。我们觉得都不靠谱。“我们步行走过去吧,”小武说:“老话说‘先走十里江堤,再走十里荒滩就到了’”。因为我们三人中只有小武曾在巴河上过学,都觉得她的建议可行,她的话在我们听来简单直接,是目前最好的方式,对于路途的远近,我们其实没有概念,殊不知那“十里”只是俗语计量的距离,实际大概率是不止的,可那时哪里顾得上想,夕阳西下时我们三人就直愣愣地踏上了前行的道路。
天慢慢黑了下来。我们仨沿着江堤走了很远,暮色里的江堤静得能听见风卷着江水潮气往衣服领子里钻,月光像凝住了的银霜,铺在脚下的碎石路上。江堤上静悄悄没有路人,只有我们仨默默地走着,谁都没劲说话,只剩腿脚机械地往前行。直到小武突然惊叫:“呀!月亮刚才还在左边,怎么跑右边了?”
这话像颗石子砸进沉寂里,我们面面相觑,疲惫里突然掺进了慌乱。我们赶紧停下脚,茫然四顾,只有天上的星星和遥远的零星灯光,我们一直沿着江堤走并没有换方向啊,应该不会错啊,突然我一拍脑袋:“应该江堤是弯的,才这样子吧。”小武又问“那这江水从哪边往哪边流?”,张云揶揄地说“呵,女生就是随什么话都敢问呵”,言下之意就是我们笨得不辨方向,的确,可月光下的江面波光粼粼,根本看不出江水的流向,倒是那道月光,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时而交叠,时而分开,江堤依旧空旷,只有我们。那声“月亮换了边”的惊叫,反倒成了黑夜里的星火,让三个年轻的身影,在1989年的冬夜,有了温度。
总算走完了江堤,下到土路时很幸运碰到了两个步履匆匆的路人,问清了方向,我们开始走上了荒滩,荒滩在夏天涨水时江水灌进来就成了水泽、这时正值冬天,水退了就是滩涂,可以行走,稀疏的小树和杂草,在昏暗中影影绰绰,月亮也躲躲闪闪起来。
走了不知多久,一条河沟拦在跟前,这下子犯愁了,我们焦急地用目光四处搜寻,看到对岸不远处有一小点弱弱的亮光,我们很饿,但还是鼓起劲大声喊人,好半天才有一个船工答话,又等了好半天,他才慢悠悠地划着小船儿过来了,靠岸让我们上船,看我们笨笨的样子,他又好气又好笑:“哎哟,街上的学生娃啊,连船都不会上!”船是摇晃的、岸是稀泥巴,上个船还真不容易。借着汽灯微弱的光,小武迫不及待地用石子刮她新皮鞋上粘的泥巴,又多又稀,怎么也刮不干净。
上岸了我们继续前行,懵懂中不知又走了多远,“我都没感觉到有腿呢。”小武嘟哝着。确实,步行了几个小时,腿早麻了,却不敢停。走着走着,疲乏的我们迎面看到了好多座黑影子,尖尖的、耸入天际,形状宛如“金字塔”,嗬,那是黄沙堆起来的,我们知道进了浠水地界了,那几年浠水的河沙卖得很火,沙子的质量很棒,呈稀有的八边形,是做高楼房的上好建材,在上海尤其抢手,当年甚至卖出了食盐的价格。这里有窝棚房还有灯光,我们心里轻松下来,但很快又被狗吓到了,那些窝棚房门前的狗不断地冲我们叫嚣,张云颇有担当地告诫“不要跑,不然狗会追着咬的”,攥着拳,我们战战兢兢地走过这一段路。
感觉再走了很久,上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隐隐约约看到一些平房。我们实在太累了,小武说:“走不动了,望天湖中学还要到镇上去,也不知有多远、怎么走。这是江边,我想泵站大约在附近吧,我们去找小曾他爸爸吧”。四周黑漆漆、静悄悄,也没个行人可以问路。当我们疲惫至极地走到一个院落前,看起来像是个单位院子,再探望看到院里屋子隐约有亮光。我们直走进院,见屋里那大方桌上有一盏煤油罩子灯,几个人正围坐着,似乎是在聊天,张云疲惫地叉着腰,虚弱地开口:“请问这里是泵站吗?”桌旁的一人回应:“是的,你们找谁?”张云大约是很欣喜,话音都有点微微发颤:“我们找曾站长。”那人又问:“你们找他有么事?”张云再答:“我们是他儿子的同学......”这时坐在上座正中的人“腾”地一下子站了起来,大声说:“哎呀,哎呀哎呀,你们真到了啊!这么晚啊!”言语中欢喜无比。于是有人快跑去学校通知小曾老师、有人赶紧去厨房煮面条,我们又累又饿,饥寒交迫中已经记不得时间了,冬天的农村,真的是很晚了。
当面条端过来时,张云接过那跟洗脸盆一样大的盆子,,眼睛看着盆里的鱼和面条,裂开嘴开怀大笑:“哈哈哈哈哈”,我们不禁被他逗乐了:他一路都没怎么说话、更没有笑,这会儿见着吃的,倒先乐了,我们也跟着笑,累好像淡了点。
一段短暂且温馨的相聚
笑声还没停,院门就被“砰”地推开,小曾老师风风火火冲进来。张云撂下筷子,上去就给了他肩膀一拳,闹闹哄哄间,才看见后面跟着陈飞舟——也是我们的高中同学,没想到他也在望天湖中学教书,听见动静就跟着来了。
久别重逢的年轻人有着说不完的话,一直到转钟聊到了凌晨,我和小武实在困极了,睡去了。他们三个男同学挤在隔壁的小床上,事后听说都没怎么睡,除了聊天,更多的是商讨第二天的安排。
第二天是周日,我和小武起床后,发现小曾和陈飞舟已经出门去买鱼买菜了。我们跟曾叔叔和泵站的工友告别,往望天湖中学走。正值星期天,学校没学生,我们溜达之后,回来看到了买的鱼——“巴河鱼”,又大又白、水灵灵的很诱人,难怪美誉名声在外。不记得是哪几个人下厨的,我只清楚地记得我们在桌上玩游戏时,我和张云敲着筷子对决“杠子老虎虫子”,他总是输,输了就喝酒,席间很热闹,闹个不停。只是没吃上巴河芝麻湖的九孔藕,那也是出了名的好吃,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遗憾。晚上我们都睡在学校的学生宿舍。
周一就得散了,小武要回鄂州上班的,我们商量好由张云陪她一起走。凌晨四点,小曾送他俩去江边等第一班船,赶上午第一堂课。小曾上午也有课要上,我就等他上完了课,下午我俩再一起去鄂州。我们到达小武的学校时,已是晚饭时候,张云已经先返回武汉了。我们在小武的单人宿舍做晚饭,有红薯煮粥,香气四溢,美味极了,那是我吃过最香的粥、没有之一。
小武教一年级,学校是包班制,语文、数学、体育、音乐全要她教。她说最不擅长音乐课,小曾立刻说“我帮你上”。于是小武调了一节课,小曾教孩子们唱《社会主义好》,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听,孩子们唱得认真,小曾也教得投入,大家唱得热情澎湃,歌声裹着暖意,满教室飘荡。
下午的课结束,我也要回武汉了。小武舍不得,说要送我,小曾也跟着一起。我们搭车到武汉的中南政法大学,去张云的宿舍。一见面,小武一本正经地说“楼下有人找你”,我还很疑惑,只见张云转身就跑下楼去,不多会儿他拎着一袋桔子回来了,满脸不解:“没人找我啊?”小武扬了扬手里正剥的桔子,笑而不答——现在想起来,那袋桔子的甜,好像还在嘴里。
“千里长亭、终有一别”,第二天早上我们跟张云道别后,来到大路边,小武和小曾要搭长途客车回去的。不多时间,汽车喷着淡淡的尾气,缓缓停在我们面前,小武和小曾上车落座后,齐齐地看向车外的我,默默地都没说话,我站在原地,也没说话,只是挥了挥手,客车开动了,车轮碾过路面的石子,发出细碎的声响,我看着车窗里两人的身影渐渐变小,直到消失在视线的尽头。
一份深藏在心底的记忆
风带着清晨的凉意扫过我的脸, 我忽然意识到短暂的相聚结束了,我们又要回到各自的地方。
我慢慢转身走向公共汽车站,公交车摇摇晃晃地穿过城区,窗外的树木和高楼一点点地后退,就像短短的假期里那些热热闹闹的相聚瞬间,正一点点地被拉远。
车到站了,我走在回校的林荫道上,忽然觉得告别不是结束,而是为了下一次更热闹的相聚,这一刻我已经开始期待了。
【作者简介】
王锦蓉,湖北省浠水县人,毕业于湖北经济学院,居武汉。钟情翰墨,笔耕不辍,有多篇文章在报刊杂志和网络媒体发表。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