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家乡农事——
吃牛肉出牛力的耙地人
李召新
锄镰铣镢,犁耙楼耙,这是咱老祖宗传下来的八大农耕工具。耕地、平地、播种、收获,是庄稼人的看家本领。其中耙字,一字两音,一音一具。耙(pa),是一种手持、多齿的小型农具,用于一畦一垄的整平。耙(ba),是一种大型的农用工具。两米多长、一米多宽的长方形的木框上,有数十个长长的铁钉,一头方,一头尖,方头在上,尖头朝下,裸露在木框的两头。它可是用来平整大宗土地必不可少的。一般情况下,两头牛拉一张耙。一个人站在耙上,牵着缰绳,摇着鞭子,吆五喝六,指挥着耕牛往前走,对刚刚犁过的土地进行平整。
耕牛,是农民最可靠的朋友,也是农耕文化中最能吃苦、最能受累的劳动者。虽然它比不上骡马跑得快,也不如小毛驴灵活,可它吃的是青草,出的是苦力。农活中最累的活都是它来干的。耕地,耙地,播种,拉车,样样都行。假如要在牲畜中评选劳动模范,耕牛当之无愧。自从人民公社成立后,国家把耕牛作为生产队的重要生产资料进行重点保护。一个生产队上有几头牛?健康状况如何?在公社经管站的台账上登记得清清楚楚。即便是到了拖拉机时代,像耙地、播种这些农活,大多还是少不了耕牛的付出。生产队里有专职饲养员,日夜守护在牛棚里,不断往牛槽里添草。上世纪六十年代,生活困难。人都没有吃的,何况牛呀?可为了保住耕牛,省里组织协调草源丰富的地方,接受外地的耕牛前来放养。饲养员牵着眼看就要瘦倒的耕牛,步行一百七八十里路,到沾化县去饲养度荒。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牛吃的是野草,饲养员们吃的是野菜。等到麦收时节,人牛平安归来时,人们发现:牛被喂得膘肥体壮,而人却都瘦得皮包骨头了。
说起对牛的感情,有一件事情让我铭记在心。那是1976年的9月底,正值三秋大忙时节。我们第一生产队的大黄牛突然病到了。眼看着就要种麦子了,耕牛却得了重病,全队人忧心忡忡。村里赶紧报告了公社,并请县兽医站的专家前来诊治。专家检查后确诊,是得了一种急性传染病,要求立即把病牛跟没有得病的牛隔离开来。就这样,第二天又发现一头小黄牛也出现了同样病状。大黄牛死了,紧接着小黄牛也不治身亡。一个生产队死了两头牛,这可是塌天大祸呀!全队人都别提多难过了。经过有关部门的批准,牛宰了,皮卖了,肉分了。多少年没吃过牛肉的乡亲们,家家含着泪水煮牛肉。牛没了,可麦子还得种呀。拖拉机耕完地,耙地这活怎么安排?这可愁坏了老队长。男劳力还得运肥、耩地呢。没办法,只能开会动员妇女劳力报名、组成临时突击队了。没想到,十几个青年妇女主动入队。她们心里清楚:今年的麦子种不上,明年就没有白面馍馍吃呀!耙虽然不沉,可耙地时需要有人站在耙上压耙,增加平整土地的功效。否则,就会整了皮整不了瓤,到播种时大坷垃都从地理钻出来。站耙,这可是个最轻快的活儿。然而,没人愿意站。谁好意思眼看着姐妹们汗流浃背地拉着自己走?没办法,大家只好轮流上耙。这时,第二生产队就有人说风凉话了;“你们吃的是牛肉,可出的是牛力呀!”这话不假。整整一个秋上,二百多亩地的小麦,都是妇女们用自己的肩膀、胳膊还有浑身的力气耙的地。她们把绳索缠在手腕上,再搭在肩膀上,弯着腰、艰难地在地里迈着步子,一步一个脚窝,一步一滴汗水。尽管生产队给大家买了垫肩,可谁的肩上没出过血?谁的手腕上没有伤呀?没想到的是,那一年,我们队的小麦不仅没来耽误农时,还夺得了先进单位的红旗。事后老队长总结说:“我们损失了两头牛,却看到了一群牛。就是平时爱溜肩耍滑的人也使出了牛劲儿。”秋后,生产队里搞决算,社员们都说,别忘了,先把买牛的钱留出来!
老辈人说,牛通人性。我觉得,人牛皆有情。写到这里,我想起一个村名的来历。这个村,离我们村有五里路。村里有一家姓王的财主,家里喂了一头牛。自家的农活干完后,他就把牛拴在大门前。告诉乡亲们,谁要用牛,牵去用就是了,不用打招呼,到了饭时只要送回来就行。这家人的善举,感动了乡亲们。人们用完牛,不光按时送回,还会在牛身上搭上一捆青草,以表谢意。这事传到了县里,县太爷为鼓励善举,弘扬正气,随命名该村为王义牛村。
一项农活,一件往事,一段佳话。从这个关于牛的故事中,我也悟出一个道理:牛马比君子。人与人,人与牛,爱是相互的。人对牛好了,牛的身体就健壮,干起活来就有劲儿。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换来的也一定是人间大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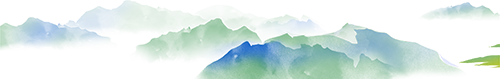




玫瑰手绘折扇、玫瑰国画
订购热线: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