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家乡的柿子树柿子树是我国北方的一种普普通通的果树。在我的家乡洛宁县东北部的河底镇一带随处可见,它高可达二三丈,树围大的可一抱粗。树龄可达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盛果期可达几十年。
我们家乡的柿子树大都生长在瘠薄的山坡上或者是村头地边,这是农民十分珍惜耕地,由于柿子树倘若生长于耕地之中,势必会占据耕地的空间,汲取土壤中的水分与养分,进而对粮食的产量产生影响。
柿子树的适应性特别强,生命力也异常旺盛。它不讲生存条件,就是在瘠薄的山坡上,村头地边上,它也能茁壮成长,干旱旱不死它,狂风刮不倒它,严寒冻不坏它,它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的最深处,顽强地生长。每到秋天,它都会把美味的果实奉献给人们。
柿子树不像苹果树那么娇贵,苹果树只能生长在肥沃的土地上,它对生存条件也要求极高。果农们每年都要给它们浇水施肥、剪枝打杈、打药除虫,少一道工序它都结不出好的果子。而柿子树从来没有人照管过它,它生长在荒山野岭上,却长得郁郁葱葱,茁壮茂盛。
到了春天,桃梨花盛开灿烂时,都会引起人们的喜爱和赞颂,而柿子树却花开初夏,它的花黄白色,小小的,如同一顶皇冠,但却朴实无华,从不引人注目,更不哗众取宠,只有喜爱它的小孩子,才会把它捡起来,用绳子串起来,做成头环,或者是项链,必定会赢得父母的夸赞以及小朋友们的钦羡。
若是说苹果树是果树中的贵族,那么柿子树就是果树中的平民。过了中秋节,柿子逐渐成熟,黄澄澄的柿子,就挂满了枝头。我小时候每到星期天就拿上竹竿,㨤上篮子,约上小伙伴们去拧烘柿吃,那是最快乐的时光。

拧下来的烘柿,摘掉柿蒂,对住柿蒂口,用嘴一吸,把浓密的果浆吸进嘴里,那个甜啊,让人回味无穷,至今想起来,还十分向往那时候摘烘柿的活动。柿子有好多品种,我们家乡就有杵头、铁蛋、水柿、面柿、牛心等十几个品种,各个品种的吃法各异,味道也不同。
譬如牛心柿,最适合吃柿饼。那就是用小刀把柿子皮一圈一圈地旋下来,用绵软的榆树枝条把旋好的柿子吊起来,挂在树枝上或者向阳的墙壁上,经过三个星期左右的晾晒,柿饼就失去大量的水分,然后把柿饼摘下来,放进小口缸里,盖严密封。
捂上一个星期左右,等到晚上有刮西风的时候,拿出来凉,就这样反复凉二三次,再放进缸里盖严密封,柿饼就出醭了,这就是柿饼霜,洁白晶莹,甘甜如蜜,是口舌生疮的良药,每个柿饼就象白面蛋蛋一样,软糯甘甜可口。平常家里来了客人,或者过年待客,拾上一盘,那可是倍有面子的事。
水柿最适合吃漤柿,那就是把柿子放进盆子里或罐子里,倒上四、五十度的热水,密封好两天之后就漤甜去涩了。漤柿脆甜脆甜的,年轻人最爱吃,这是苹果所无法比拟的。
杵头和面柿是最适合吃烘柿的。把柿子摘下后,放在家里十天八天就逐渐烘了,这两种烘柿沙甜沙甜的,尤其是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里,人们去地劳动回来又累又渴,吃几个沙甜如蜜的烘柿,又充饥又解渴,简直就是无比的享受。
还有一种叫铁蛋的柿子,果实非常硬,从树上掉下来也摔不烂。它很不容易烘,可放到春节过后,春暖花开时节它才能烘,当你去地干活回来,又热又渴时吃上几个烘柿,顿觉满口生津疲劳顿消。在灾荒年代,柿子帮人们渡过灾荒,救过不少人的生命,以前粮食不够吃,人们靠柿子来渡荒年。
在那饥荒的年代,我爷爷已经是六七十岁的老人,由于长期吃不饱,缺乏营养,饿成浮肿病,那年冬天夜里,爷爷饿得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吃两个柿子来充饥,爷爷说那年冬天如果没有柿子吃就会被饿死。
柿子成了救命的食物,那些年代里,人们用秕谷糠和烘柿搅拌成团晒干,用石磨磨面,蒸上糠窝窝,在春荒二三月时,人们经常吃这样的糠馍或糠糊糊来渡荒年。
我小时候也经常吃这样的糠窝窝,现在的年轻人会相信吗?过去有的困难家庭生下小孩,奶水不够吃,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奶粉,那时就是有奶粉也无钱买,就用烘柿来喂养小孩子,柿子是小孩赖以生存的食物。

洛宁县志上记载:柿子功可代乳。柿子树朴实无华,它没有桃梨的华丽妖娆,没有杨树的伟岸挺拔,更没有柳树的婀娜多姿。它适应性强,不管是生长在山坡上也好,还是生长在村头地边也好,它都能够茁壮成长。一到秋天都会把丰美的果实贡献给人们,它要求人们的甚少,却给予人们的甚多。当你看到柿子树对人们无私奉献,难道就不想到我们的农民对社会的无私奉献吗?
我家乡的农民,在国家需要时为国家所做的一切,且不说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就是在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国家的政策是农业支援工业,农村支援城市。我们农民每年都把粮食晒干扬净,过筛,把最好的粮食交给国家,支援国家建设,自己却留下次一等的粮食作为口粮,那怕自己再困难也要完成国家下达的征购任务。
一直到二〇〇五年,国家免除农业税,一直交了五十多年的农业税。那时候国家修水利,修公路,搞基础设施建设,农民们带上口粮,背上铺盖卷踊跃参与,奉献自己的义务,不挣国家的一分钱,无怨无悔的为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后,家乡的青壮年农民走出农村,进入城市,矿山,工厂,农民变成了农民工,为国家大建流汗出力。
试问城市里高耸入云的大楼工地,城市里宽广干净的街道上,哪里没有农民工的身影?建筑工地上的脏活累活,哪样不是农民工干的?他们不管是烈日当空,还是凛冽寒风,他们都坚守在工地上,一砖一瓦地建造着城市的明天。
他们有信念,有担当,即使工作再累也不说苦,一点一滴砌出城市的辉煌,为祖国的强大,做出了无私的贡献。我们的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群体,他们要求国家给予的甚少,却给予这个社会的甚多。
著名的经济学家温铁军说:我们的农民从来就不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者,他们是百业的从业者,你看木匠、铁匠、石匠、泥瓦匠,甚至修鞋的,补锅的,以至于现在农村的大型农机驾驶员,不都是农民吗?我赞美柿子树,我更敬仰我们的农民,我为他们唱赞歌,农民是国家的脊梁。
二〇二五年三月于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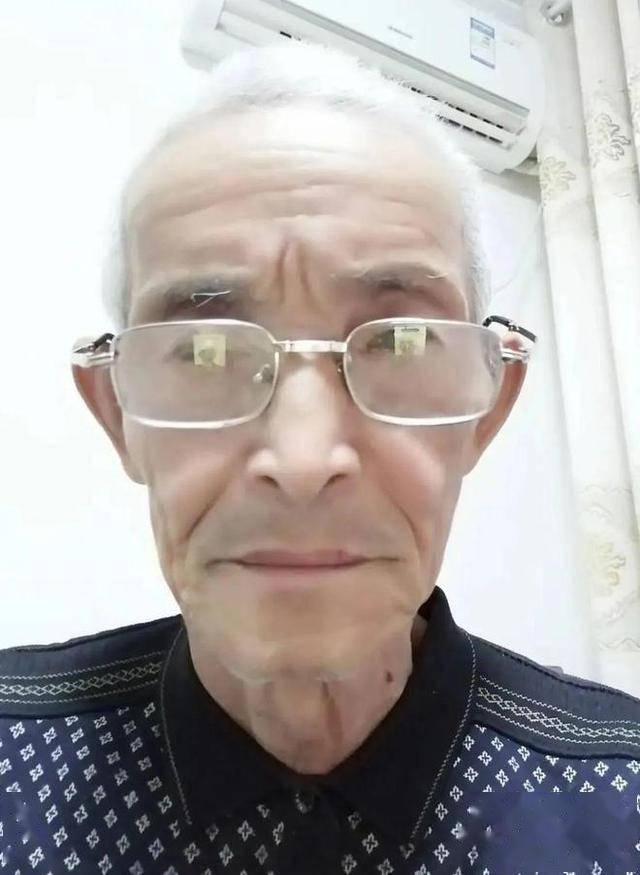
作者简介:张红彦,洛宁县河底镇杨坟村人,生于1947年,高中毕业,一生务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