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内容提要】:主人公“老刘”,一位没有文化的农民。拾过粪贩过豆,当过兵打过工,养过鸡喂过猪,凭着正直善良和一点“小聪明”,与贫穷奋斗,与命运拼搏,换来了幸福的晚年。
文图|崔方春
老刘,今年六十九岁,山西泽州人,是我南方猫冬同一小区同一栋楼的近邻。他方圆脸庞,个头不高,头发浓密,身体稍胖,左手中间三个指头少了一截,混杂的晋城方言和青青的络腮胡子,令人记忆深刻。

一个月前,我俩还不认识。准确地说,是没有具体交流,对不上号。一日,我老伴与几个老姐妹坐在一楼大厅闲聊,见我回来让帮她们照张合影。其中一位姓郝,是老刘的妻子。他妻子和我老伴,成了我认识老刘的牵线人。接触多了,交流多了,我开始认识老刘。
一、没文化
“我没文化”,这句话老刘总挂在嘴边。导致“没文化”的原因很多。他家居太行山南麓晋中盆地,祖祖辈辈以种地为生。这里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陈旧的观念亦束缚着人们的思维,早年多数人家都不怎么把孩子的学习当回事儿。
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他,上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全家九口人。他父亲是位乡村(赤脚)医生,能为本村和周边的群众治疗常见病。在他老家,也算是文化人。但由于人口多,家境贫寒,兄弟姐妹都未能好好读书。
老刘回忆,他自认为不是读书的料儿。上学不愿听老师讲课,不愿做作业,课堂上小动作不断,有时还影响其他同学。当然,成绩是垫底的。读完一年级有些跟不上,被老师留了一级,但没起多大作用。腻腻歪歪读完五年级,他“抽腿”不干了。自己不喜欢上学,不愿意读书,父母也没办法,那就回家种地吧。1968年夏天,十二岁的他回村当上了生产队的“小社员”。
年龄小,个子矮,干不了地里的重活。但家里不能养吃闲饭的,必须想办法去争“工分”。在农村大集体时代,收集粪肥是生产队庄稼用肥的重要来源,拾粪把他派上了用场。
他背粪篮挑箩筐,蹚公路跑货场,走村头串小巷,捡马粪驴粪,拾狗屎牛屎,连路边的羊粪蛋蛋也不放过。攒够一百斤,去生产队兑换十个工分。这其间,他感谢孟匠火车站货场和晋城马车运输队,感谢好些可怜他帮助过他的车把式。有的赶车人让他把箩筐放到马车尾部,免去了他挑担之苦。有的车把式在牲口排便时减速慢行,让他顺利拾进粪筐。令他至今难忘。
老刘常说,自己干活不惜力,嘴巴还甜,脑筋也比较灵活。他帮助货场过磅员运货汽车司机跑腿送单、传递小票,帮助马车板车驭手牵牲口、装卸挡板,甚至搬运货物。力气换来好人缘,周边有不少人喜欢他帮助他。联系穿城而过的卸货司机,捎带村里叔叔婶婶去县城办事,是最受待见的。在他的撺掇联系下,解决了不少人的进城难题。人熟了还有意外之喜。有一次,车站装生铁坨子,泥土里剩了些碎铁渣。经默许,他捡回来三分钱一斤卖给供销社赚了三毛钱。一毛钱买了个窝窝头自己吃,剩下的两毛交给了母亲。当时,算不小的收入呢。
十六岁那年夏天,他成了五人割草组成员之一,负责打青草喂生产队的牲口。打草不但要用力气,还要有门道,懂得如何找草源,如何割得快割得多。别看他人不大,但脑瓜灵光,善于发现和扑捉机会,总能在不经意间跑到别人前头。一过磅,天天都比其他几个人多,兑现的工分也多。
他还透露,自己割草时会 “假公济私”。那些年,家里养了几只兔子,兔子吃的草与牲口草不同。他打牲口草的同时留心兔子草,发现一点割下一点,单独存放。交完牲口草后背回去喂自己家的兔子,父母高兴的不得了。他还经常“搂草打兔子”,顺手把生产队的“瓜瓜”掩草带回家。下锅炒炒,一个南瓜就是一家大小的下饭菜。他说,别看没文化,我可不缺这样的“小心思”。

长到十八岁,他成年了。虽然有些瘦弱,但身高已达一米六五。可惜从那之后没怎么再长高。那年冬天,他为生产队“出民工”,参加某兵工厂建设。几个月后,他成为村里农业学大寨水利队的一员。故名思义,就是修建水利设施。春夏秋三季打井找水、修塘筑坝、挖沟修渠,冬天开山劈岭造“大寨田”,脏活累活危险活他都干过。用他的话说,就是“出老鼻子力了”。
广阔天地把他“累得够呛”,让他看不到“出头的日子”。参军当兵,也许是唯一希望。
二、兵哥哥
沾了“贫下中农”成分的光,又有担任生产队干部叔叔的帮助,1976年3月他应征入伍,被分配到太城警备区六连,成为一名光荣的“兵哥哥”。
在新兵训练期间,六连被整建制划转武警部队,担负起值守太城公安看守所的任务。按说,机会“应该来了”。但他,吃了“没文化的亏”。人家都能看书读报写材料,他却不能完整地念完一篇文章,写出一段简短的文字。
他说,还是“革命大熔炉”教育了他,培养了他。不断的政治学习,周边的耳闻目染,包括上级通读《毛选》的具体要求,他也打算下功夫学文化。可是基础太差,好些“它认得我,我却不认识它”,只能“顺流而下”了。不过,还是收到了成效。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能磕磕绊绊地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和报纸上的一些文章了。他说,到现在还吃那时的“老本儿”。
在部队,他做事认真,诚实待人,不惜力气,不怕吃苦。执勤站岗,内部勤务,炊事做饭,种菜养猪,哪里需要哪里去,叫干啥就干好啥,样样走在别人前面,得到领导的肯定和战友的赞扬。三年服役期满,他被继续留在部队干了两年。1979年 8月,他加入党组织,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被提为副班长至退役。
入伍三年后,部队领导给了他一次探亲的机会,时间十五天。临行前,连长交代:“回去好好找个对象”。他明白,这是机会,因为现役军人找媳妇比较容易。父母也作为重要任务,找了几个媒婆四处撒网。其间,先后见了几个女孩子,但提前准备好的“两块布料”楞楞没送出去。没想到,归队前头天晚上的一句无意之言,却成了他婚恋的开始。
话从另一头说起。当年,公社组织修水利设施,一支民工队住进他们村。有几个女青年住在他哥哥家的侧房里,其中包括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小红。这天,他去看望与哥哥同住一个院子的本族奶奶,巧被在家休息的小红隔窗听到。也许出于好奇,也许出于青春女子的敏感,小红起身从半边门缝里“偷窥”了这个房东的弟弟。虽然只是个侧面,只看了半张脸,但个头和体形还是印象深刻。小红说,她当时就是好奇,绝对没有爱恋的意思。
时间过的好快,第二天就要归队了。那天晚上村里放电影,这可是不多得娱乐活动。作为混熟的姐妹,小红跑去邀请正在吃饭的他妹妹一同看电影。其间,谁也没有说什么。她们走后,他母亲遗憾地说:“这次回来,媳妇没有着落,看样子要等下次了。”“娘,不急。要是有合适的,找个小红这样的就行。”他说的很随意。他娘,心领神会。几天后,第一个媒婆、他的亲婶婶去小红家登门了。
得到的回话是,“不同意”。为避免不必要的嫌疑,小红搬到了另一家居住。尴尬的是,从“窖子”搬进了“窟窿”,这家竟是他的堂叔。从此,媒婆由一个变成了两个。出民工结束,事情进入了高潮。小红回忆说,对他本人,包括长相外表个头和家境基本是满意的,没有多少想法。其实,“我最讨厌的是,两个村子之间有一条很深的大沟,总担心走沟底会遇到坏人甚至危险。一旦嫁过去,总不能不回娘家吧”。但不同意的回辞,并没有拦住媒婆的脚步,反而开始了难以置信的“狂轰滥炸”。

俩媒婆下午进门等小红下地归来,小红避而不见,她们晚上十点都不离开。见面后,非要小红去他家“走走形式”。无奈,小红口头答应,第二天却放了鸽子。几天后,她们再次登门,硬数落软磨咕,“不答应上门,就不走了”。被整的没有办法,小红答应“走一趟”,但前提是“不吃饭不拿定礼”。结果,吞进的鱼钩再无法吐出来,小红一步步跌入了他家和媒婆的“套路”:上门了,就要吃饭—-吃饭了,就得“拿礼”—-拿礼了,就算答应亲事了。
三、难日子
小红从他家回来,把为遮人耳目换了包皮的“两块布料”,没开封地挂在门后,一放就是一年多。其间,与他并无见面和书信往来。1981年初,他接到部队通知,要他准备退役,同时允许回家探亲。这下,小红没了办法,真的“生米煮成了熟饭”。这年三月,他俩结为百年之好。
办完仪式,他带着新婚妻子到了部队,边度蜜月边办理退伍手续,也开始互相了解对方。用亲密的厮守甜蜜的陪伴,结束了没有通信,没有牵手,没有抚摸,没有拥抱的“恋爱生活”。他和妻子异口同声,说他们是真正的先结婚后恋爱。
一个月后,办妥退役手续,部队给了三百块生活补助费。这时,他突然萌生了一个大胆甚至不可思议的想法:带小红去北京开开眼,看看首都,欣赏欣赏祖国大美河山。“那时候,我们农村人山里人能去北京,是不可想象的。”他说。他奔着驻北京郊区、在某连队担任司务长的老乡而去。
他揣着退役费,提着军用帆布包,背一床被子一双鞋,陪小红坐火车搭汽车,转地铁乘公交,颠颠簸簸找到老乡。老乡很热情,很周到。借了部队一间营房,提供米面菜蔬,让他俩自炊自食,即实惠又方便。在营房周边转了一个星期,老乡找车陪他们去市中心,参观了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故宫等名胜。他说,站在天安门广场留影的那一刻,就甭提我俩那高兴劲儿了。真幸福!
途中路过一家商店,看到一种时兴的粗皮行李箱,单价七十元。他一阵兴起,要开开荤,买一个。同行的老乡说,“我也来一个”。他毫不犹豫地掏一百四十元结清了箱款。尔后,碍于情面,出于感恩,老乡不提给钱他也不好意思开口。回到旅社,他俩别提多后悔了,这可是近一半的退伍费呀!他们又上街买了几斤北京糖果、给父母买了点小礼物,乘火车回到了家乡。
晚上,母亲问:“你不是有三百块钱的补助吗,钱呢?”他低头不语,东翻西翻从衣服口袋里,找出仅剩的七十块钱递给母亲。唯唯诺诺检讨自己:“花了,就这么多了。”他说,当时母亲的脸色很难看,样子很生气,就差打耳光了。“父母打算用这笔钱安排的事项,都让我给吹了,搅和了”。
几个月后,按村里的习惯做法,父母提出让他“独立门户”,即分家过日子。分给他三间土屋,几件农具,几个锅碗瓢盆和一袋五十斤白面。由于推迟二十多天分家,这袋面粉已吃去一半之多。“剩下的二十几斤,我们不能都拿走啊,又给父母和弟弟妹妹留了二分之一。我和小红用这十斤面粉,开始了自己的生活”。他很苦涩,很无奈。
转过年,农村开始实行土地承包,生产队的牲口农具也分配到户。很幸运,他分到了二亩地,抓阄抓到了一头毛驴。有头牲口,对拉磨、种地、搬运东西会方便很多,但需要饲料饲草,还得工夫喂养。正在犹豫,后邻一位叔叔好像看透了他的心思:“如有难处,驴子由我养吧,你随用随牵”。“驴子转出去,我也没有撒手不管,秸秆、瓜蔓都作为饲草给叔叔送去。当然,需要的时候,我也会把驴子牵回家”。他解释道。

这年,他办了件大事。他以代缴一千斤小麦公粮为条件,接手了一个本家的十亩薄地。“我们那里是旱地,粮食产量低,小麦更不行。好多人包括父母,都为我捏着一把汗。但我豁出去了,非要试试自己的本事”。那时候,他胆子有点儿大。不过,他是幸运的。经过与小红共同努力,小麦获得不错的收成。包括自己的两亩,共打了一千七百斤麦子。交去一千斤公粮,余下七百斤。他的仓囤里有了足够的粮食,并且是细粮。更可喜的是,一毛二分钱一斤卖公粮,换得了一百二十元现金。这可不是个小数目,惹得不少人翻眼球呢!(未完待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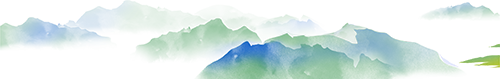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