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游丁家峪
宋文东
在济南,一提起丁家峪,喜欢亲近大自然的人可能无人不知。丁家峪是位于历城区西营街道办西北几公里远的一个小村庄,以其村后青龙山上的秋天红叶而闻名遐迩。但近年来,济南周边秋末看红叶的地方多了不少,因此丁家峪不再像前些年那么红火了。我和驴友们也有几个年头未到丁家峪了。也说不清楚什么原因,在这数九寒天里,我忽然有了去丁家峪看看的想法。
2024年1月28日,7点半,我与君哥、豌豆花、书亭、高哥等几位驴友在燕山立交桥南拼车,直奔丁家峪。半个小时后,我们抵达港西路进丁家峪的村口。高哥停下车,说,到了。见村口竖块牌子,上面写了“石岭村……”几个字,我便有点怀疑前面的村子究竟是不是丁家峪了。而村口那座架在水沟上的小石桥尚在,还有桥北沟西菜地里那眼沉默的老井,已经准确无误地告诉了我答案。但令人不解的是那块牌子上为什么不写丁家峪这个村名,而是写的石岭村呢?难道是丁家峪改村名了,还是被石岭村合并了呢?查看地图,石岭村在丁家峪之北,两者距离得有几公里远,根本就不是一个村子。见我仍是疑虑未消,高哥不明就里,说,错不了,就这儿。
有驴友说,夏天的南部山区气温比市里能低几度,对此我有亲身体验,深信不疑。但冬天的南山,气温比市里同样能低几度也是不争的事实。这不,早晨起来,我在市里还没觉得有多冷,但到了南山,不戴手套、棉帽,手和耳朵就被冻得有点受不了。不过,今日天气还是不错的,天色湛蓝,空气清新,太阳已经离山顶有三杆子高了。
8点半,驴友们集合齐了,然后出发进村、上山。山道是水泥路,比较陡峭,路上的积雪尚未融化,湿滑难行。山色萧索,景色荒凉,连那些松柏也被冻得萎靡不振,灰暗了几分,唯有路边那几片青郁郁的竹林显得绿意盎然,生机无限。有的竹竿子都长得有锨柄一般粗了,让人恍若到了江南一般。

爬上半山,远远地望见北面崖壁上刻有一个大大的红“壽”字,格外惹眼。“壽”字约有六米高,三米宽,但比起青州云门山上的那个“壽”字则要小得多。落款有点模糊不清,也不知道是哪位书法家的作品。记得青岛崂山上有数十个不同写法的“寿”字,占了一大面石壁,令人叹为观止。山上刻“寿”字,大概也是出自“寿比南山”之寓意吧?

离开“壽”字,我们沿着崖壁下面的小路往东北方向的山林之中蜿蜒而去。在一座楼宇后面,靠山崖处有一个石砌的近似椭圆形的小水池,显然是一眼泉。水池子旁边竖立一块比较正规的牌子,上面写有“白云泉”三个大字。我愣了下,记得这个泉不是白云泉,而是雪花泉,在雪花泉畔竟然插个白云泉的牌子是啥意思呢?令人不解的是下面介绍的内容里明白无误地说白云泉在白云洞内。另外还介绍了包括白云观、古树群、天然洞穴等多处景观,显然这块牌子插的地方不对,说它在误导游人一点也不为过。白云洞在此泉的上方,接近山顶处,距此直线距离约有百米远,绕道就更远了。也还记得这眼雪花泉畔曾有块小牌子写了泉名,现在那块牌子却不见了,这种做法简直是荒唐!现在泉池内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石壁上还结有几根粗大的冰柱,洁白如玉,晶莹剔透,赛过鹅脂。泉水像是冬眠了一般,寂然无声。原来雪花泉那泠泠的水声也听不见了,这可能是由于冬季枯水期泉水减少的缘故吧。


过了泉,见楼宇北门口有一群猫,不知道是冻的,还是饿的,都在喵喵乱叫,在这寒冷的冬日里,令人顿起恻隐之心。大家都在为猫咪们忧虑,房门忽然被推开了,一位穿着藏蓝道士服的中年男子走出来,把猫咪们引走了。好梦问道,这些猫咪是你养的吗?道士说,是的。看猫咪们的样子,像是几天没得到饭吃了。景区里除了我们10位驴友,再也没遇到一位游客,到处冷冷清清的。书亭有点好奇地说,这里还有道士?以为没人了呢。
告别了道士,我们继续前行。转过一座不知名的两层大殿,也就是白云观的前殿,沿着殿后的石阶爬上了白云观。白云观是一座仿古双层建筑,红柱黑瓦,歇山飞檐,雕梁画栋,也倒壮观。门前左侧有一块较大的太湖石,上面刻了三个字:白云洞。白云洞是一个天然的石灰岩洞穴,已经被建在白云观内了,还用一把铁锁将游人拒之门外。据我所知,白云洞至少有几个年头不对外开放了。
白云出岫是白云洞的一大奇观,也是洞名的来源。但这种奇观唯有阴雨天气方有可能出现,虽然不大常见,却早已名声在外了。游人们慕名而来,即使见不到白云出岫,但连洞也不让看,的确令人扫兴。现在的白云洞四周围得严严实实,到了汛期,不知道洞内还能再飘出白云来吗?我没有亲临过,因此就不清楚了。进不了洞,我们只好从门玻璃上窥几眼看个大概罢了。

白云观后墙借助的是白云洞岩壁,洞呈一个巨大的弧形,高3米左右,宽10几米,深浅不知,洞口砌一堵半米高的墙,可能是拦蓄泉水之用吧?据知情驴友说,白云洞里面还有几个支洞,直通后山,与锦绣川相连,不知真假。洞口前放置一块不大的石头,上面刻有“甘露”二字,我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也不清楚这眼泉究竟是白云泉,还是甘露泉呢?
白云观最早是一个叫徐立仙的元代道士所创建,曾兴盛一时。后来屡建屡毁,至今观内外尚有明清残碑遗迹散落各处。残碑虽然破损,但碑上字迹有的还较为清楚,其中有《……白云洞记》,落款为光绪十三年重阳;还有一块是《重修白云洞记》,落款是大清康熙四年;最为久远的一块当属大明嘉靖三十一年的《白云洞众祖先派记》。现在的大殿是近年新建的仿古建筑,虽然也是古色古香,但与真正的古建筑相比,似乎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上次来白云洞,驴友们也是跟这块刻有洞名的石头拍张合照,这次也不例外。大家拍完合影便离去。

白云洞北面崖壁上刻有“天然古树群”几个大红字,字下方有条小路蜿蜒东去。

不远处有一棵古柏,生在崖壁上,树干粗大,尤其根部突起,像是往石缝生长时遇到阻碍似的,估计两个成年人也不一定能搂抱得过来。据园林部门测算,这棵古柏已经有千年树龄了。古柏常见,但生在石缝之中的千年古柏就不多见了。

在那棵千年古柏的旁边,有一座甚不起眼的小庙——王灵官庙。小庙接近2米高,2米多宽,石头砌成,裸门朝东洞开着。庙里面黑洞洞的,门口摆有水果等贡品,还有个小香炉,可知尚有前来祭拜之人。关于王灵官,本名王恶,后因萨祖师改名王善,为道教第一护法镇山神将,与佛教的韦陀相似,在民间威望甚高。许多道观镇守山门的神将都是这位王灵官。传说王灵官火眼金睛,能辨真伪,洞识善恶,因此道教徒进道观都是先拜王灵官。民间一直有“上山不上山,先拜王灵官”之说,以表示对王灵官的崇敬。
在千年古柏往东10几米远处,还有一棵生长在石壁之上的古柏,古柏躺着生长了有半米左右,忽然拐弯直立起来,其不屈不挠,顽强向上的品格值得钦佩。

现在这些古柏都挂上了重点保户植物的牌牌,令人欣慰。附近山崖上还有几十棵类似的古柏,其共同特征都是生长于石壁之上或石缝之中,但形状各异,姿态万千,年岁不一,估计树龄至少也都在几百年以上了吧。它们被保护得如此之好,可能也有白云观里道士们的一份功劳吧。
沿着山崖小路继续东行。沿路两侧多黄栌,许多黄栌树龄已经有数十年了,有的甚至达到百年。红叶们早已凋零殆尽,地上就躺着很多,厚厚的一层,像铺了斑斓的锦毯一般。她们又像在冬眠,也算是落叶归根了。我真的不忍心打扰她们。红叶们生的时候神采飞扬,活力四射,装点的山野万紫千红,分外妖娆;死后毅然回归故土,然后零落成泥化作养分再回报大地母亲。红叶们这种知恩图报的品格是多么地可贵和高尚!

跻身山脊,回望白云观等几座仿古建筑,均隐在山林里,颇有几分深山古寺的味道。可惜现在不是秋天,倘在红叶满山的时候,站在这山脊上,透过树隙,正是观赏红叶的最佳之处,那种铺天盖地的红尤其醉人。

登上西面最高的山顶,大家在松林里休息会儿,喝点水,补充点能量。立身山顶,俯瞰西南,蓝天似洗,重山如阙,山川像画。那锦绣川水库的一泓碧水,宛如一大块玉坠卧在锦绣之川里。
再望眼前的南山之北坡,数十层梯田从山根一直叠到山顶,那淡墨色的墙堰,白皑皑的梯田,黑白分明,线条粗拙,轮廓清晰,犹如一幅水墨画似的。
驴友们欣赏了美景,继续沿着山脊往下一座山峰——鸡冠子山方向而去。
2024年1月31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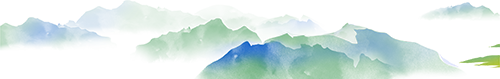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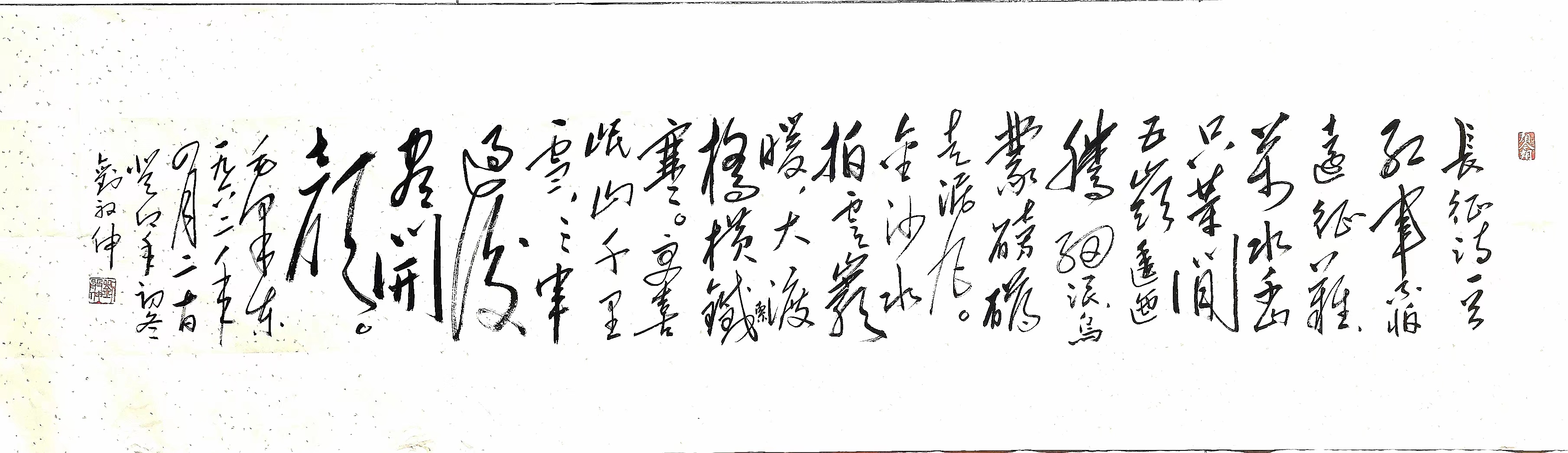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