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老家的核桃树
马延明
晚间,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妻子对我说:“吃核桃吗?”,我说:“拿两个!”妻子递给我两个,我用手一捏,皮立即就碎了,我取出带褐色的果仁,放到嘴里一嚼,香中带苦。我对妻子说:“这核桃比着我们老家的核桃差远了,那才叫一个”香”!”,妻子说:“老家有核桃树吗?”我说:“有啊,你忘了在老院子里北屋门口的香台子前面?”妻子说:“我怎么不记得了......”这一番对话,引起了我对老家核桃树的回忆。
小时候在老家能吃上核桃,那叫一个“奢侈”。在我的记忆中,我们老家的街坊邻居中,核桃树是很少的,记得赵元杰家的院子里有一棵,大概一抱粗;再就是第六生产队赵洪宪家的院子里有一棵,树径大约50厘米,枝繁叶茂。再一棵就是我们家的这棵了,说起这棵树,我的印象是很深的。

1972年秋天,老家的房子建成,院墙还没建好,我们全家就从老院子里搬了进去。一天中午,我们村老书记赵兴铭的孙子赵立新给我们家扛来一颗核桃树,说是他奶奶让送来的。这颗核桃树大概一米五、六高,和掀把一样粗,有点弯曲,顶端有一小枝,树根很少也很细,约有三、四厘米长。母亲说:“这个能活吗?”父亲说:“人家好心给送来了,栽上吧!”于是,父亲就在北屋门口香台子(在我们村几乎都在北屋门口的右边放一个上香的台子,我们家的香台是用水泥和石子浇筑成的,表面还刷了些红油漆)前面挖了坑,大概三十厘米见方,深也差不多三十厘米,把树放进去,浇上水,漫过树根,等水渗完,埋上土,父亲还特别的在树的周围用土围了一个圈,从此,我们时不常地浇上点水。
第二年的春天,核桃树枝上竟然冒出了嫩绿的小芽,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核桃树活了!”,全家人都欣喜的跑过来观看!慢慢地核桃树越长越粗,树枝也越来越多。可是,两年过去了,树上也没见长核桃。我听人说,核桃树杆必须用刀子上下划一划,核桃树才能长核桃,于是,在一个下午放学后,我偷偷地用镰刀在树干上从上到下划了好几道。心想,明年一定能长核桃了。

1981年9月,我考入济南师范学校,离开家乡。核桃树已经长成碗口一样粗,枝叶也像一把大绿伞,把阳光遮的严严实实,树上结的果子也已经很难数清楚。每年在核桃成熟的时候父亲和母亲总是给我悄悄地留出二、三十个。我回家时,父亲或母亲拿出来,我边吃边和他们聊家常,父亲总是问我的学习工作情况,母亲老是给我“唠叨”东家长李家短.....。

1997年,核桃树已是枝繁叶茂,树径大概三十五至四十厘米,树冠已经覆盖了院子的四分之一,当年我在树干上划下的刀痕,已经裂的手指一样宽,像是老农脸上深深地皱纹。然而,家里大哥翻盖院落,由于碍事,将核桃树伐掉了。我们真是舍不得啊!
在我的印记中,每年夏秋之交时,树上经常吊着一些小虫,大概一厘米长,绿色的,如纳鞋底的麻绳(过去人们都是穿布鞋,鞋底是用布一层层粘好后,再用麻绳纳成的)一样粗,我们叫它吊死“鬼”,我经常的拽下来,拿在手心里用手指逗着它玩,吊死“鬼”一会儿伸开身子,一会儿蜷起身子,直到把它玩够了为止。另外,树上还经常长一种像一分钱硬币大小的虫子,我们当地人把它叫作“扫蝎子”,和树叶的颜色一样,很难被发现,一旦被“扫蝎子”蜇到,疼痛难忍,说不上来的一种滋味,皮肤立即红肿成一片,所以,只要一旦发现,我们立即将它弄死。我曾经被蜇过,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毛骨悚然。

离开家乡已经四十多年了,核桃树也已经被伐掉二十六年了。现在想起来,我们家的核桃树,长得核桃特别大,她的外壳很硬,所呈现的纹理,宛如自然雕刻的精美艺术品。核桃的果肉很香,放到嘴里一嚼,那真的是韵味无穷.......
老家的核桃树啊!您留给我的不仅仅是一段回忆,留给我的更是对家乡的眷恋,对家乡人的思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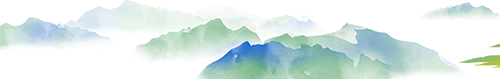

刘般伸,特型演员,著名书法家。
有需要刘般伸先生书法作品或者莅临现场演出鼓劲加油的请联系《都市头条·济南头条》。
刘般伸先生毛体书法作品欣赏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