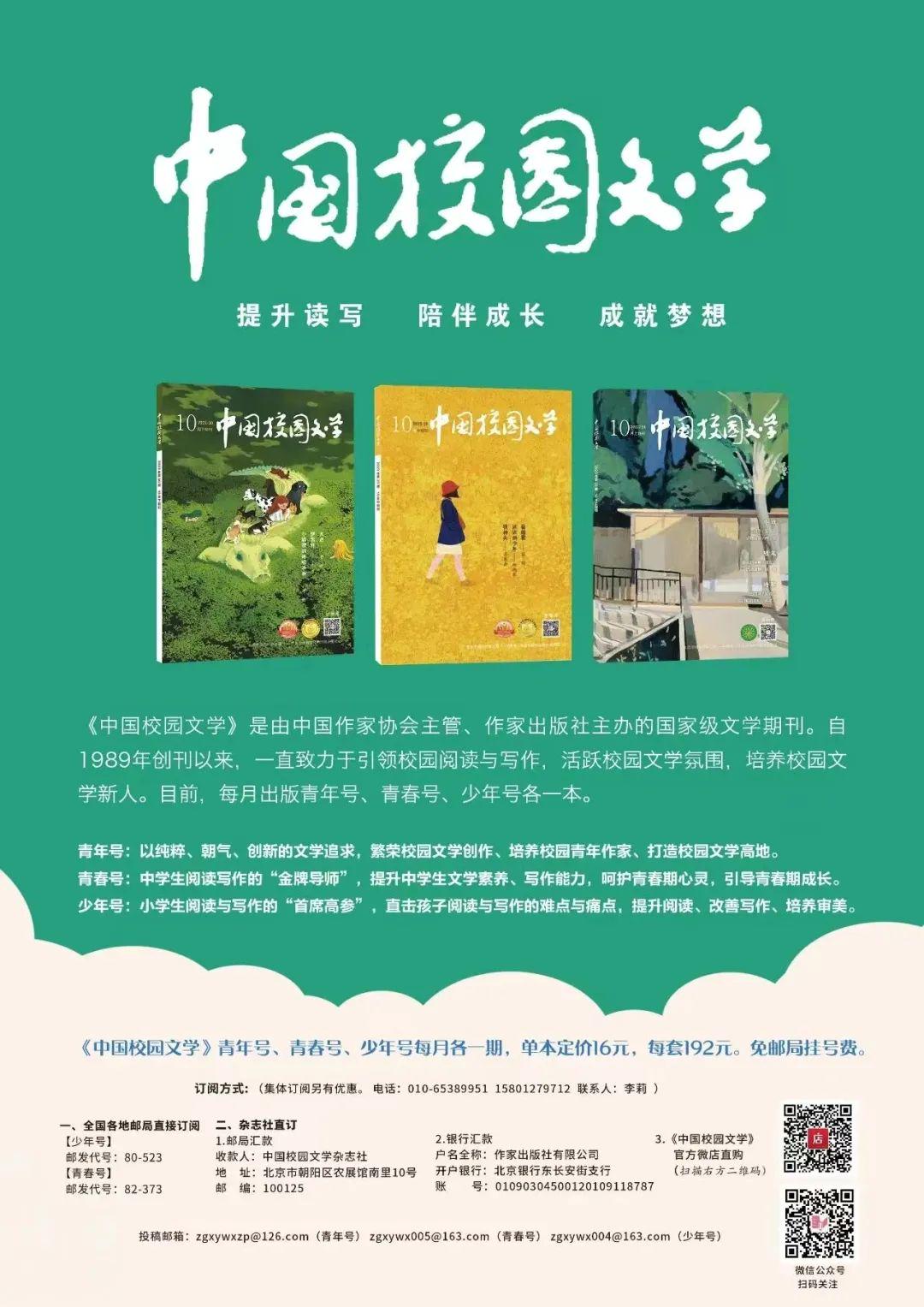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快讯!近日,顾一灯《等雨停的一小时》被选入北京三帆中学的期中考试题目。
出题老师说,语文老师们“读一次哭一次,太感人了。孩子们这次考场作文也有被这篇文章影响。”
对了,这篇文章刊于《中国校园文学》2020年11期青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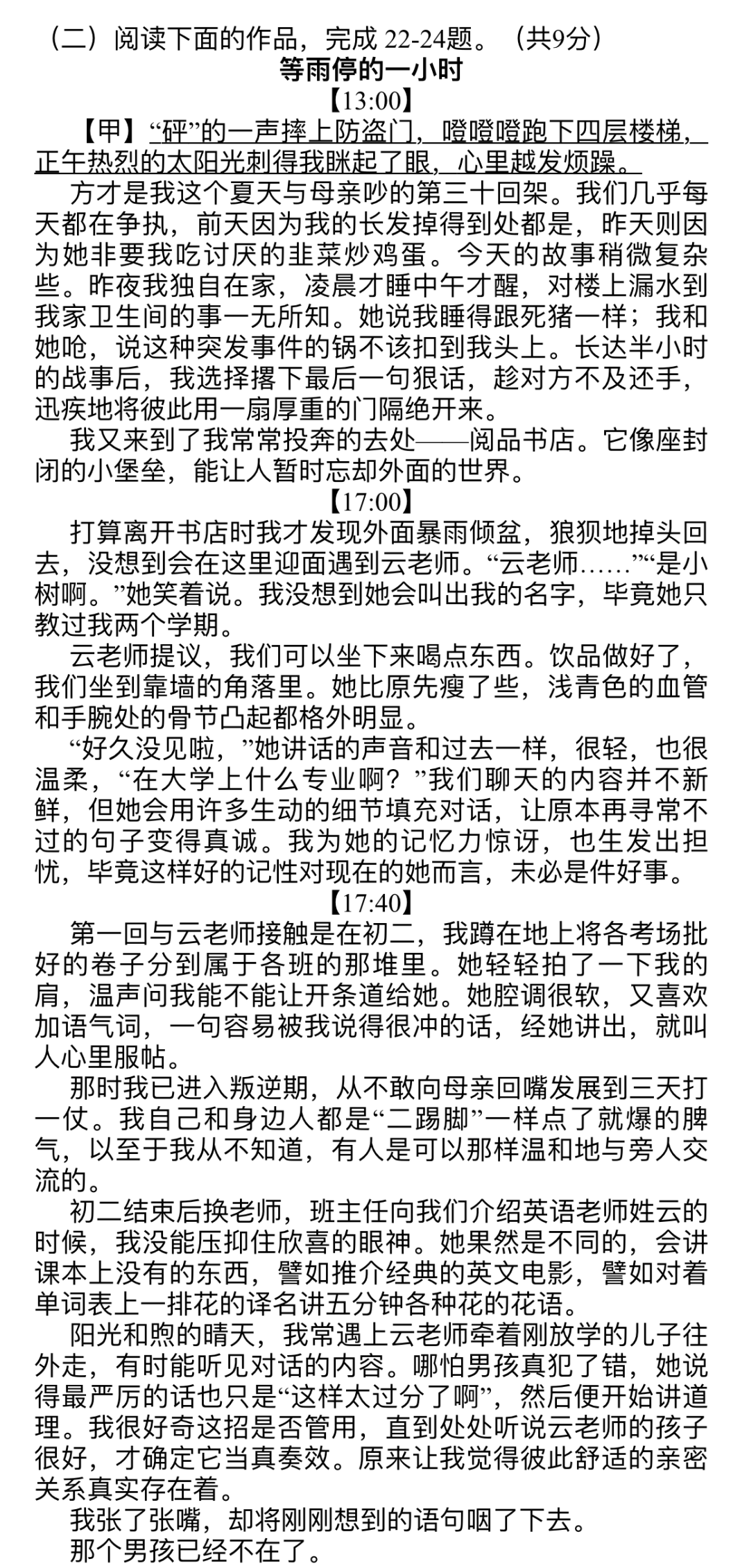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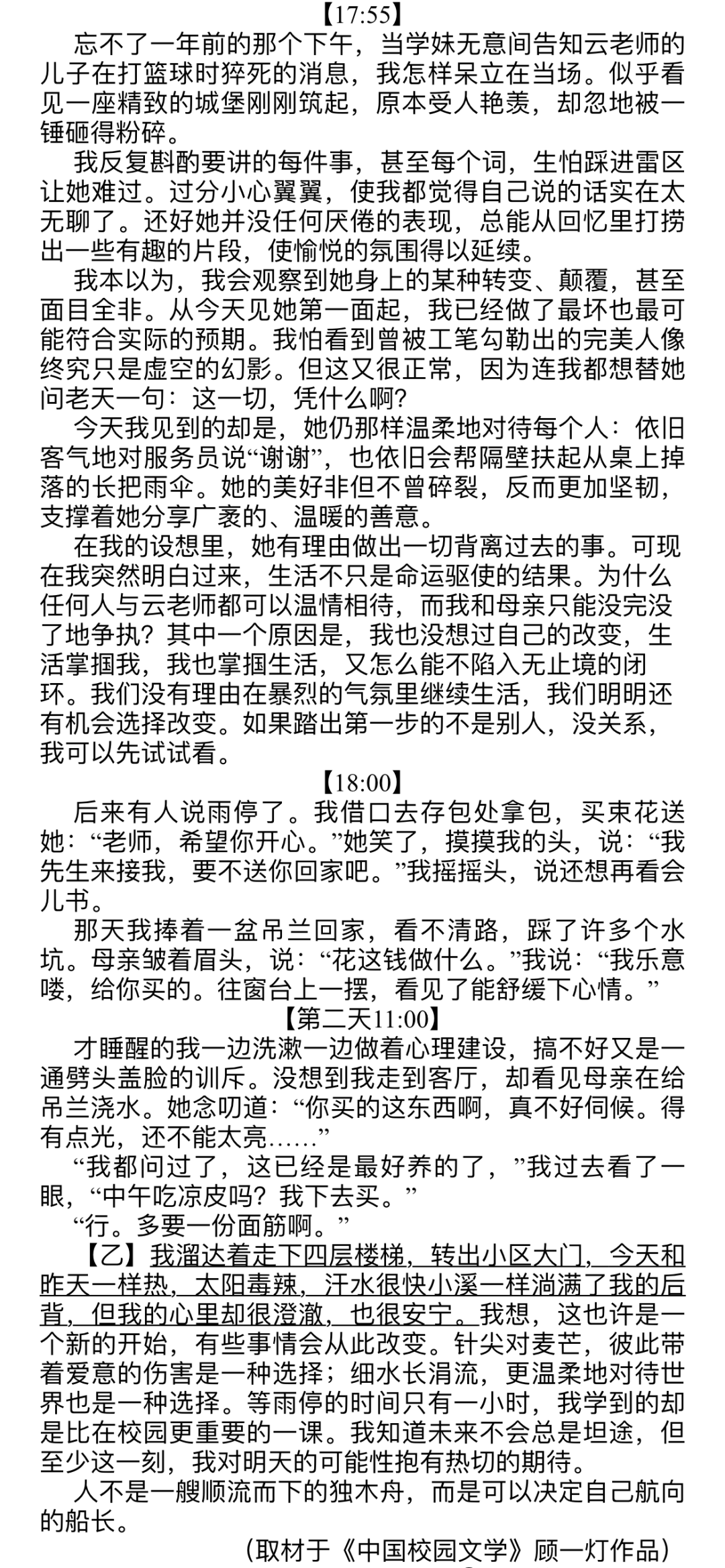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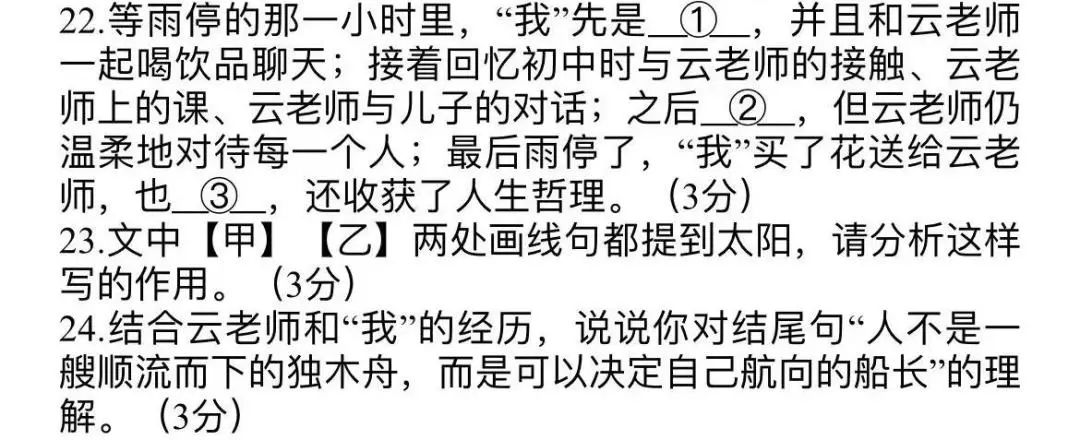
(有删节)
佳作欣赏

(图/周心悦)
等雨停的一小时
文/顾一灯
【13:00】
砰的一声摔上防盗门,噔噔噔跑下四层楼梯,正午热烈的太阳光刺得我眯起了眼。艰涩地流动的空气裹挟着火焰一样的热浪,拖曳着我的脚步。想起刚刚身处的空调房,念头短暂地动摇了一下。但一直以来固守的面子告诉我,现在没有选择。只能远走,不能回头。
方才是我这个夏天与母亲吵的第三十回架。这个数字如此精确,并非因为我小心眼地一天天掰着手指头计数,而是六月底各门科目结课后,我在家正好待满了一个月。我们几乎每天都在争执,前天因为我的长发掉得到处都是,昨天则因为她非要我吃讨厌的韭菜炒鸡蛋。
今天的故事稍微复杂些。昨夜我独自在家,凌晨才睡,对楼上漏水到我家卫生间的事一无所知。中午我揉着眼睛拉开房门,模糊的视线里第一个映入的便是母亲阴沉的脸。她正要将垃圾送到门外,显然刚刚收拾完一团狼藉。大战就此爆发。她说我睡得跟死猪一样;我和她呛,说咱们作息不同,四点睡自然要十二点起,这种突发事件的锅不该扣到我头上。原先与邻居的外部冲突很快演化成了内部矛盾。长达半小时的战事后,我选择撂下最后一句狠话,趁对方不及还手,迅疾地将彼此用一扇厚重的门隔绝开来。
【13:25】
我钻进冒着飕飕冷气的地铁车厢,从西门站的地下通道直接上行至阅品书店。空调开得很足,皮肤始终维持着冰凉的感觉,这让我很舒服。灯光却是暖色调的,浅淡的黄色均匀地投落在每个人身上,营造出一种仿佛被柔软的布匹包裹的美好。
和许多新潮些的书店一样,阅品的模式也是复合经营。一楼北侧设了咖啡厅,南边开了家花铺。咖啡豆研磨发出的苦涩的香味,和月季、玫瑰、百合的甜蜜相互碰撞,融合成一种特别的气息。
我走到二楼东南角的现当代文学书架前,抽了本黄国峻的《度外》读。序言里骆以军说,国峻小学时被老师罚写一百八十行错字,他的父亲春明去学校理论,却被老师冷语讽刺。春明便果断地帮国峻办理转学手续。余下的小半个学期,春明用机车载着国峻环岛旅行。敏感而羞涩的国峻紧紧抱住父亲的腰。风从生满绿叶的树梢吹过去,也从他们温热的耳边吹过去,一片呼啦啦的声响。
这个段落让我几乎落泪。我多想体会类似的温情,可事实上每天的生活里充斥的都是语言暴力。我们的住处分明宽敞明亮,但每当战争发动,它就变成吓人的逼仄,天花板垂得低了又低,下一秒就要将我压垮。
于是我夺门而逃。
阅品书店是我常常投奔的去处。它没有玻璃窗,像座封闭的小堡垒,能让人暂时忘却外面的世界。我坐在老位置——纹理分明的实木地板上,将书在盘起的腿上摊开,一页又一页翻过去,浸入横竖撇捺积蓄的海洋里。陆地上困扰我的喧哗声,渐渐遥不可闻。
【17:10】
这是一部不太好懂的短篇集。我时常回溯、反复,读得很慢。读完六篇后,肚子开始叫。下楼时,长时间的阅读让我视线模糊,台阶上蒙着一层轻薄的白雾。
踩下最后一级,雾气终于消失。我向大门走去,路过笑容甜美的羊角辫小女孩、认真举起习题集比较的家长,还有扶着花镜读《道德经》的老爷爷。
正值暑假,书店里人不少,每个书架前都有顾客驻足。可我的余光还是从他们当中瞥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眼神仿佛手持的跟拍镜头,摇晃着,一路随她挪移。
长及锁骨的亚麻色中发,尾端是内扣的卷。覆住脚踝的真丝印花长裙,绘的是灰色的大航海场面。她走在英文原版的区域里,攥着两本厚重的书,坚硬的漆皮上是烫金的英文字母,花体难以辨认。
由远及近,镜头变成特写。她往收银台的方向张望。我清楚地看见她的侧脸。
眼看她要转过头时,我缩回脑袋,藏到了畅销书架的后面。
我低着头,右手装作整理头发,挡住半边脸,仓皇地绕了个大圈往正门去。踩上门前的地毯时,我觉察出凉意,没多想,仍拨开棉被一样厚重的门帘往外走。恰好有人往里冲,蹭我一手水。
我这才发现外面暴雨倾盆。站在狭窄的玻璃隔板下,半边T恤很快被雨水打湿。许多只落汤鸡以好笑的姿态奔走在街道上纵生的河流里。同样没带伞,我狼狈地掉头回去,后面簇拥着把这里当作避难所的人们。
她正将书塞进托特包,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夹着一卷发票。
我们迎面相遇。
湿漉漉的水汽不断涌进原本干燥明亮的书店。我站在原地,呼吸迟滞,一时间大脑空白,像台机器开进突兀的场面,将平日那些机灵的念头全部抽干。耳边全是它轰隆隆的运转声。
“程老师……外面下雨了,很大的雨。”
这个傻乎乎的开场白,让我话音刚落就恨不得给自己一巴掌。
“是锦树啊。”她笑着说。
我没想到她会叫出我的名字。
毕竟她只教过我两个学期。
毕竟已经过去了四年。
【17:20】
近几年全球气候异常,北城也不例外。冬天格外冷,夏天格外热。大寒不再落雪,大暑却疯狂地降雨。常常没半点预兆地,长空便阴云滚滚,闪电似金色的镰刀劈砍整座城市,锋芒过后,雷声轰鸣。
这场雨应该下不久。但即便停了,也没法即刻上路。北城的排水设施不好,大雨后街道都会长成地上河。我低头看看皮质的新鞋,确定决不能让它泡了水。不只因为肯定要挨的骂,还因为我想到了母亲工作时的样子。我只见过一次,在北城附近的乡下,做工程师的她爬上梯子检查电线杆的问题。我用全身力气按住梯子,它仍摇摇欲坠。每分钱来得都不容易,我没理由糟践任何不便宜的东西。
明明不久前还在对她抗拒,还在逃离家庭,现在又主动寻求连接。我们之间的错综纠葛,像好几堆毛线缠成一团。红色的线是相爱,我们为彼此考虑,他们记着我爱吃的豆浆油条,我记着他们的鞋子尺码;黑色的线是伤害,我们倒持短剑刺向对方的软肋,剑把碰到皮肤便收手,不见血,却足以让对方觉得痛苦。
“我的母亲”一类的命题作文,从不允许我书写这样的情感。它只让我们抒发绝对的爱意。或者欲扬先抑,一个误解被揭开后,终于发现亲情那样坚不可摧。所以大多数同学都在编故事,闹出许多不合逻辑的笑话来。
没人帮我们解答,该如何接纳不完美的彼此,以及并不纯粹的感情。
程老师提议,我们可以坐下来喝点东西。这缓解了我手足无措的状态。至少当我不知该如何措辞时,可以拿过菜单,假装考虑要点哪道三明治;我也可以紧握住杯子,一点点往上吸冰水,这样即使沉默也不会过分尴尬。
其实我们的相遇并不奇怪。念初三时书店新开业,我在这里见过她几次。但此刻我并没做好足够的准备。我右手在身后握拳,大拇指没及时修剪的指甲深切进肉里,痛感尖锐。我得让自己足够清醒,才能应付接下来发生的事。
她讲话的声音和过去一样,很轻,也很温柔,似乎怕声音大点便会吓到别人。我安静地听着,复杂的情绪难以言表。她说每个句子前,我的心都会提起来,直至尾音吐出才回到原位。可当新一句话出口,心便再度悬在半空,仿佛站在因年头久远而脆裂的地板下,等第二只鞋子掉落的瞬间。
非要用一个词形容,应该是害怕。从今天见她第一面起,我已经做了最坏也最可能符合实际的预期。曾被工笔勾勒出的完美人像,终究只是虚空的幻影。相对而坐时,打光的灯束渐渐黯淡,我将眼看着它消失不见。
但我不愿面对。
【17:25】
程老师点了黑咖啡,我点了芒果汁。饮品很快做好了,我们坐到靠墙的角落里。她比原先瘦了些,浅青色的血管和手腕处的骨节凸起都格外明显。
“好久没见啦,”笑起来时,她眼角的细纹记录着时间长河冲刷过的痕迹,“你考入吉林大学了是吧?念什么专业呀?”
“对,”我赶紧说,“读中文系。”
她有些讶异,说记得我学的是理科。我向她解释,现在许多文科专业都文理兼收。她恍然,然后说,这个专业很适合我,她还记得初三那年,语文组统一布置了命题作文“我的老师”,作文课上各班都请了任课教师去听学生读范文。我那篇写的是班主任老周,每念一句,台下便发出爆笑声,老师们起初还绷着,后来也没忍住。一直到今天,还常有人拿其中的句子调侃,“每当我看见老周灵活地用身体模拟直角坐标系,都会暗暗感叹,这样一位骨骼清奇的高人没被体操队挑中,真的是中国体坛的一大损失……”
我们聊天的内容并不新鲜,走向与其他长辈别无二致。但她会用许多生动的细节填充对话,让原本再寻常不过的句子变得真诚。在我平庸的学生时代,站上讲台读《老周》的那五分钟或许是最高光的时刻。我又花了点时间,才回忆起她如何得知我学理科的消息。高二前我们回一中看过一次老师,我不曾与她单独交流,只在每人简述近况的轮转里说,自己留在了理科班。她竟一直记着。我为她的记忆力惊讶,也生发出担忧,毕竟这样好的记性对现在的她而言,未必是件好事。
【17:40】
我们从没这样近地坐着,又坐了这么久。四年前,甚至更早的细节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为什么程老师让我印象深刻,我也说不清楚,可能是她来自江南,说话的腔调和我们北城人全然不同。她腔调很软,又喜欢加语气词,一句容易被我说得很冲的话,经她讲述,就叫人心里服帖。
第一回与程老师接触是在初二,她肯定没印象了。期末后我被派去初三英语组,蹲在地上将各考场批好的卷子分到属于各班的那堆里。她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温声问我能不能让开条道给她。那时我已经过早地进入叛逆期,从不敢向母亲回嘴,发展到三天打一仗。我习惯了情绪最激烈的表达方式,自己的,别人的。送我去作文比赛的路上,母亲也要与路边的出租车司机因该打谁的车大吵特吵。街边大爷和任课老师,也大都有二踢脚一样点了就爆的脾气。以至于我从不知道,有人是可以那样与旁人交流的。
我看着她拎起桌上的水壶,细心地浇阳台上的几盆花。
自此我对她多了一分留意。在套着永不合身的校服的日子里,一个会打扮又声音好听的女老师足以吸引我的眼球。我知道她只教毕业班。初二结束后老师大换血,只有班主任老周坚守在了原先的岗位上。当他向我们介绍英语老师姓程的时候,我没能压抑住欣喜的眼神。她果然是不同的,会讲课本上没有的东西,譬如推介经典的英文电影,譬如对着单词表上一排花的译名讲五分钟各种花的花语。
在一中,办公室紧挨着教室,只隔了一处观景走道。我是语文课代表,常在它们之间来回。下午最后一个课间,我会去搬批改好的作业。
我喜欢在走道上穿梭的感觉。北城的晴天多,透过玻璃窗映射下的阳光总是很和煦。我常遇上程老师牵着刚放学的儿子往外走,有时能听见对话的内容。哪怕男孩真犯了错,她说得最严厉的话也只是“这样太过分了啊”,然后便开始讲道理。我很好奇这招是否管用,直到一天老周说程老师的孩子成绩很好,才确定它当真奏效。国峻和春明的故事终究太远,程老师的家庭却很近,让我觉得彼此舒适的亲密关系真实存在着,它也属于现实世界,不只在动画片、小说和梦境。
一次体育课后碰见他们,我将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找到的四叶草相送。我遥望着他们的背影,看见她将四叶草递给儿子,小男孩紧紧攥着它的柄。他们消失在操场前方的雪松后边。没像某些人一样,在我视线范围内就甩手丢掉。
我张了张嘴,却将刚刚想到的语句咽了下去。
那个男孩已经不在了。
【17:55】
母亲曾在争吵中对我说:“没有什么事,是本应该如何的。”
这是无意义的彼此攻击外,为数不多的被我记住的话。我眼看着它一次次应验,在我身上,也在程老师身上。世界的运转总会脱离我们预想的模式,我越发无奈地发现对于正在发生的许多事,我并没有决定权。
比如我继承了母亲的坏脾气。我喜欢用这个词,为自己身上讨人厌的特质找到某种根源。从小在相爱相杀的环境里成长,又怎么可能脱落出别的形状。觉得这还不足够,我将视野扩大到整个北城。你相信吗?如果城市也有自己的气质,那么北城一定是不甘的、幽怨的。二十年前它拒绝某家新起步的电器公司入驻,如今却眼看着它上市,带动着隔壁的蓝市风生水起、房价猛蹿,我们仍收入甚微。街头巷尾的内耗,也是落差之下某种形式的发泄。
我没法左右的,是一些空气一样环绕着我、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的东西。而程老师面临的是突然的变故。我忘不了一年前的那个下午,当学妹无意间告知程老师的儿子在打篮球时猝死的消息,我怎样呆立在当场。似乎看见一座精致的城堡刚刚筑起,原本受人艳羡,却忽地被一锤砸得粉碎。
我反复斟酌要讲的每件事,甚至每个词,生怕踩进雷区让她难过。过分小心翼翼,使我都觉得自己说的话实在太无聊了。还好她并没任何厌倦的表现,总能从回忆里打捞出一些有趣的片段,使愉悦的氛围得以延续。
我本以为,我会观察到她身上的某种转变、颠覆,甚至面目全非。这很正常,连我都想问老天一句:这一切,凭什么啊?
今天我见到的却是,她仍那样温柔地对待每个人。
【18:00】
她没有改变待人接物的态度,依旧客气地对服务员说“谢谢”,也依旧会帮隔壁扶起从桌上掉落的长把雨伞。这些细节是装不出来的。她的美好非但不曾碎裂,反而更加坚韧,支撑着她分享广袤的、温暖的善意。这让我又记起许多细节,比如后来去了职高的同桌告诉我,这是唯一一个会和他谈心听他倾诉的老师,唯一一个。“我这种坏学生”,他说这话的时候,什么都不在乎似的挑起嘴角。
在我的设想里,她有理由做出一切背离过去的事。可现在我突然明白过来,生活不只是命运驱使的结果。为什么任何人与程老师都可以温情相待,而我和母亲只能没完没了地争执?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也没想过自己的改变,误以为你骂我一句、我还你两句才是需要勾画的选项。生活掌掴我,我也掌掴生活,又怎么能不陷入无止境的闭环。我们没有理由在暴烈的气氛里继续生活,我们明明还好好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明明有机会改变。如果踏出第一步的不是你,没关系,我可以先试试看。
后来有人说雨停了。陆续有人走出去。程老师付了饮料的钱,我借口去存包处拿包,买了一束花送她。我记得以前英语组的办公室里,她养许多盆花,每逢春夏开得格外茂盛。跑圈时我将它当作一个地标来看,见了满目的绚烂便精神一振。我对她说:“老师,希望你开心。”她笑了,摸摸我的头。虽然我已经读大学了,但她待我仍像面对一个小孩子。她说:“我先生来接我,要不送你回家吧。”我摇摇头,说还想再看会儿书。
那天我捧着一盆吊兰回家,看不清路,踩了许多个水坑。纤细的绿叶低垂着,上面开了几朵零星的白花,进家门时基本掉光了。母亲皱着眉头,说:“花这个钱做什么。”我说:“我乐意喽,给你买的。往窗台上一摆,看见了搞不好能舒缓下心情。”我收拾了一块空地,将花盆归置好。再一转头,发现母亲已经回房间了。
选 择
第二天我醒来的时候,又已经是十一点。我一边洗漱一边做着心理建设,搞不好刚拉开房门,就要接受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没想到我走到客厅,却看见她在给吊兰浇水。吊兰被移动了位置,放在没被阳光直射的地方。叶子青翠,开成一朵花的形状。
她念叨道:“你买的这东西啊,真不好伺候。得有点光,还不能太亮……”
“我都问过了,这已经是最好养的东西了,随便照料下就能活,”我过去看了一眼,“今天中午吃凉皮吗?我现在下去买。”
“行。多要一份面筋啊。”
再一次,我溜达着走下四层楼梯,转出小区大门,融入菜市场喧哗的人流里。卖力的吆喝声中,穿插着讲价钱的你来我往。今天和昨天一样热,太阳毒辣,汗水很快小溪一样淌满了我的后背,但我的心里却很澄澈,也很安宁。我想,这个清静的早晨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有些事情会从此改变。针尖对麦芒,彼此带着爱意的伤害是一种选择;细水长涓流,更温柔地对待世界也是一种选择。我可以决定的,比生活给予我的多得多,也比我想象的多得多。等雨停的时间只有一小时,我学到的却是比在校园更重要的一课。我知道未来不会是顺利的坦途,但至少这一刻,我对明天的可能性抱有热切的期待。我不是一艘顺流而下的独木舟,而是可以决定自己航向的船长。

顾一灯,北京大学法学和经济学双学士,法学硕士,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获香港华文青年文学奖、周庄杯儿童文学短篇小说奖,作品见于《中国校园文学》《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已出版长篇小说《冰上飞驰》,同名有声书在“学习强国”平台上线。
END
(刊于《中国校园文学》2020年11期青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