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掩卷茫然对短檠
——忆刘泮溪教授
张杰
岛居犹记遇孙刘,校友联翩共一楼。
侪辈行中君独秀,温文端谨自风流。
岂止温良见性情,是非界限倍分明。
虛期再作京华会,掩卷茫然对短檠。
这是近代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孙思白教授在他的老同学、老朋友刘泮溪教授逝世以后所写的诗篇。
孙教授以深沉的感情回忆了抗战胜利后,他与孙昌熙先生、刘泮溪先生等从昆明回到青岛欢聚的情况。当时他们血气方刚,风华正茂,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以后很想干一番事业。他们共聚
这首诗形象地写出了泮溪先生的思想、品德、性格和才华,读来哀切动人,催人泪下。这是孙教授为他的老朋友写的挽诗,也是一曲感人肺腑的颂歌。
一
泮溪先生是山东昌邑县人,1914 年生于一个小康家庭。少年时代曾读过私塾,在家种过田,当过学徒,后到济南中学读书,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大中文系。抗战以后,他随校经长沙迁昆明。北大、清华、南开在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他随北大进入联大学习,1940年毕业。他毕业后先在银行做文书,同时兼任天南中学语文教师,后辞去银行职务,到联大附中教书,抗战胜利后,一直在山东大学任教。
他在旧中国十分憎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他曾投身于“一二•九”爱国运动,并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抗战胜利后,他又参加了昆明的学生运动,对国民党反动派残杀进步学生,制造“一二•—”惨案的罪行表示极大的愤慨。1947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反饥俄、反内战的民主运动。青岛市的学生于6月2日举行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他支持学生的正义斗争,率先到山大附属医院去看望慰问被军警打伤的学生。
他从青年时代起就追求光明。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就与地下党员毛承志同志有密切的联系。他在党员的帮助下,曾阅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他还在张天翼主编的《文艺新地》,钱俊瑞、千家驹主编的《中国农村》,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月刊》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抨击黑暗,讴歌光明。
新中国成立后,他热爱新中国,热爱共产党。他政治上要求进步,1951年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并积极靠拢党组织。山大和华大合并后,组建文学院,德高望重的吴富恒教授任文学院院长,他任该院的秘书兼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以后任中文系副主任、《文史哲》编委、《山东文艺》编委、山东省作协副主席等职。他在工作中以身作则,团结同志,不计名利,任劳任怨,踏踏实实,埋头苦干,竭尽全力完成任务,深得领导与同事们的好评。例如
他任山东省作协副主席时,曾多次调解同志间的矛盾,为促进团结做了很多工作。
二
泮溪先生自幼勤奋好学。他曾阅读了我国许多优秀古典文学作品,如屈原、李白、杜甫的诗歌,明清的小说,还阅读了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高尔基的名著。这些优秀作品培养了他的文学兴趣,陶冶了性情。
他也非常喜爱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他曾被郭沫若在《女神》中所表现的狂飙突进精神和爱国激情所感染所震撼,他决心像郭沫若那样诅咒黑暗,讴歌黎明。
抗战时期,他在云南曾大量收集整理过苗族瑶族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并发表过这方面的论文。他希望文艺作家从民间歌谣中吸取营养。
他十分崇敬鲁迅先生,崇敬他为人民所作的无私奉献,钦佩他对旧社会所作的入木三分的分析和批判。他要学习鲁迅鲜明的立场和韧性的战斗精神。他要以学习鲁迅、研究鲁迅作为自己终生之事业。
他曾对鲁迅的著作逐篇进行研读并作笔记。我们打开他读过的鲁迅的杂集就会发现,在书的扉页上及每篇文章的空隙都写满了笔记和各种记号,有毛笔记的,有钢笔记的,也有红蓝铅笔记的。旧的一套书记满了,他又买了一套新的再作笔记。
1951年,在华岗校长的倡导和支持下,山大中文系在全国率先开设了鲁迅研究课,华校长和泮溪先生、孙昌熙先生、韩长经先生合开这门课。他们的课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后来他和孙先生、韩先生将讲稿编成《鲁迅研究》一书正式出版。这是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鲁迅思想及其创作的专著。它的出版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在建国初期还写了不少研究鲁迅的论文,有的后来还收入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研究室编选的《鲁迅思想研究资料》一书。七十年代中期他又主持编写了《鲁迅杂文的时代背景》一书。
他在大学时代受教于闻一多、杨振声、朱自清、李广田等著名学者门下,受到名师多方的指导与熏陶。他大学时代的论文就是朱自清先生指导的。论文的题目是《清末诗歌与“五四”新诗之关系》。由于他深得恩师的奖掖与厚爱,兼之他学习刻苦,所以在学业上进步很快,功底很深。因而,他建国以后在山大曾开设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诗歌研究、文学概论等课程,与此同时还在校刊上发表了不少文艺论文,其中一部分编成《文论小集》一书。
1958年,他到东德汉堡大学讲学,讲授中国近代文学,为传播祖国文化,加强中德友谊做出了贡献。他曾和友人谈到,东德的学生善于思考,求知欲很强。他讲《官场现形记》时,学生对中国清代的官场情况问得很多,有许多官场情况他个人不甚了解,为此,他曾多次写信向在山大任教的黄公渚先生求教。由此也可以看出他的负责精神。
解放后不久,泮溪先生到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文艺理论研讨会。到会的还有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会上制定了新的文艺学提纲。回校后他深入研究文艺理论的许多新课题,他的课深受同学们的欢迎。从此以后文艺理论课,在山大一直受到学校的重视。
六十年代初,他到北京参加教育部组织领导的高校现代文学史的教材编写工作。这套教材由周扬同志负责,唐弢、严家炎任主编。先生为这套教材的编写花费了不少的心血。该书直到 1980 年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然而,先生却没有能够看到它,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遗憾的。我想,假若先生在世,看到这套教材正式出版并为全国高校普遍使用时,不知该怎样兴奋呢!
他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除培养青年教师外,主要工作是参加国家出版局负责组织领导的《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他和孙昌熙先生具体负责《故事新编》的注释。他带着重病,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投入这项工作,直到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
他历来以治学严谨为朋友们所称道。他将自己一生的全部心血倾注到教学和科学研究中去,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三
泮溪先生不仅品质高尚,作风正派,性情儒雅,和蔼可亲,待人诚恳,而且笃于友情。泮溪先生和孙昌熙先生是三十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的同学。抗战开始以后,他们一起从北京经长沙到昆明。抗战胜利后,他们又一起从昆明回到山东。他们朝夕相处,并肩而行,在人生的征途上共同跋涉了 40 多个春秋。他们情同手足,互相支持,互相帮助。他们都将对方看作是难得的知音。孙先生对老友的早逝感到无限的悲哀,十几年来他一直怀念这位难得的好友。
据孙先生说:泮溪先生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在银行任秘书并任中学语文老师,经济较为宽裕。同学和朋友生活上遇到困难向他求助,他有求必应,慷慨解囊,帮助朋友们解决了不少燃眉之急。
泮溪先生和他的老师杨振声先生、朱自清先生、李广田先生都有很深的感情。建国初期李广田先生在北京工作,他们过从甚密,李先生仍像过去那样经常给他以帮助。
我常常想,如果说我在学习研究的道路上多少做出了一点成绩的话,那么,这是与先生的帮助奖掖分不开的,我永远不能忘记我的恩师。
四
在旧中国,由于知识分子生活的不安定,工作的劳累,经济的窘困,医疗条件的限制等原因,不少人健康状况不佳,未老先衰。在这方面,建国初期我接触的山大中文系一些老师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的老师当时年仅40多岁,但看上去就像多病的老者。当时泮溪先生年仅30来岁,正是壮年,然而,他的身体状况也不佳。
他在青年时代曾患过风湿性关节炎,当时由于没钱治疗,发展成为风湿性心脏病。我在山大读书时就注意到:每当秋风一起,先生就早早地穿上了御寒的服装。心脏病人不仅怕感冒,而且最怕劳累和精神刺激。“文革”期间,他看到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悲愤难忍。后来山东大学又迁往曲阜,使他劳累不堪,这些情况都促使他的病情日趋严重。
1971年深秋的一天,我到当时迁到曲阜的山东大学参观学习。我顺便去看望先生。这是“文革”劫难后我们第一次见面,心情都十分激动。他围着被子坐在床上,他的爱人高重同志坐在他的身旁。我们进行了长谈,谈我们近几年彼此经历的惊涛骇浪,谈彼此所了解的师生们的近况,谈先生的疾病,我们互相劝慰,希望尽快地度过难关。我怕影响他休息,几次想告辞都被他留下,我们一起谈到深夜。
粉碎“四人帮”以后,山东大学又从曲阜搬回济南。我回母校向老师们表示祝贺。老师们在眉宇间流露出喜悦的神情,他们又在为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忙碌着。
泮溪先生的政治热情很高,在他的面前有许多工作要做,但他又为疾病困扰着。我除将所得到一知半解的医学知识告诉先生外,还建议他看点有关心脏病防治方面的书,并劝慰他保重身体,注意劳逸结合,延年益寿。
可是,不久就听说,他的病情有了发展,并且不断恶化。他仍然牵挂着教学,牵挂着《故事新编》的注释工作。我听后不胜凄然,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笼罩在我的心头。
我想,难道这位忠厚善良、和蔼可亲的长者真的会不久于人世吗?我不敢想下去。
然而,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978年2月16日先生由于心力衰竭而溘然仙逝,享年65岁!
我常常想,泮溪先生的晚年应感到欣慰,因为他终究看到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可耻下场!
然而,他却没有看到科学的春天,文艺的春天,知识分子的春天的真正到来!为此,我感到深深地遗憾!
1989年10月1日初稿
2023年8月30日北京定稿
张杰 教授
山东省新泰人,1931 年1月生,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泰山学院教授,离休干部,曾任泰安师专中文系主任、《泰安师专学报》主编、《泰山研究论丛》主编、泰山文化丛书执行主编、山东服装学院院长等职。著有《现代三作家论集》《高兰评传》等学术著作,散文集《春风桃李忆吾师》《翘首东海忆故人》,诗集《心中的歌》《筛月楼诗稿》《筛月楼诗稿续篇》等。

中国鹰王——王照华绘
独家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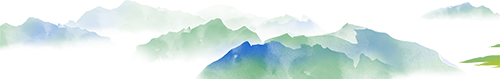

中国鹰王团扇大师王照华作品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