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旧时,济南泉上的端午景象
侯 林
小引:济南碧筒饮正值端午节焕然登场
农历五月初五日,是我国传统的民间节日端午节,亦以纪念相传于是日自沉于汨罗江的古代爱国诗人屈原,有裹粽子及赛龙舟等风俗。
具体到济南,旧时过端午节都有哪些讲究呢?
据清乾隆《乾隆历城县志·地域考·风俗》:
仲夏月,五日,书门符,悬艾虎,系彩丝,黍角相餽。士大夫携酒泛舟,作折筒饮,即小民亦携壶,剧饮树下。
书门符,即艾符,旧时在端午日为辟邪而悬在门户上的艾与(书写的)符箓。
悬艾虎,旧俗在端午节日以艾作成虎形或者剪彩为虎,粘艾叶,戴以辟邪。
系彩丝,端午节习俗,旧时人们、特别是妇女在端午日以五彩丝缠臂,名长命缕。
黍角,又名角黍,即粽子。
折筒饮,即碧筒饮;由此可知,济南之碧筒饮,盖自五月端午就已焕然登场。
那么,旧日在济南泉上,端午节的风情雅意又如何呢?
之一:趵突泉边,端阳时节敞琼筵
清代同治、光绪间宦居济南的邵承照有《午日约同人望鹤亭小集》:
晴旭烘开雨后天,端阳时节敞琼筵。
柳条斜亸飘如线,莲叶新浮小似钱。
隔院铎声摇屋角,当窗塔影落樽前。
诸公莫惜今朝醉,一日清闲一日仙。
(光绪七年刻本《云卧堂诗集》卷六)
邵承照(1832 ——?)字伯廌,号香听。浙江籍(直隶)大兴人。举人。同治五年官肥城知县。光绪二十二年官曹州知府。著有《云卧堂诗集》。
端午节乃是酒仙的节日。宋代诗人戴复古有句:“榴花角黍斗时新,今日谁家不酒樽?”(《扬州端午呈赵帅》)而在济南,一如上文所述:“即小民亦携壶,剧饮树下”,好是过瘾、好是肆意酣畅、放怀任诞的景象。

济南日报 吕传泉摄
而在趵突泉上,特别是临泉的雅舍如望鹤亭之类,早已被士大夫捷足先登,订好了端午酒宴。午日,端午之日,同人,邵承照在山东的同官。琼筵,盛宴、美宴之谓也。此时,雨后初晴,又逢端阳佳节,趵突泉上,清丽悦人,红花照眼,诗人抓取了仲夏趵突泉上最为典型的风物:柳条、莲叶。绿柳与泉水是最为美妙的搭配,微风之下,绿柳飘拂戏水,诗意尽显无遗;而在趵突泉上的青青莲叶,此时尚未长成大叶,如钱浮在泉池水面之上,更有欣欣之深意与精致婉约之美感。
“隔院铎声摇屋角,当窗塔影落樽前”,隔院,因有绿竹掩映,石欄人静,南山画屏,时人称之为竹院。山东巡抚崇恩有诗称其:“松篁幽翳處,丹室篆烟清。”(《初春小集趵突泉次嵇孝廉韵二首其二》,清同治刻本《香南居士集》拾得集)由此可知为一道院。“隔院铎声摇屋角”,其妙处在一“摇”字,它将铎之动感与音响诗意地传递出来,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形,而且,它与“当窗塔影落樽前”的“落”字,前呼后应,将名士们在趵突泉饮酒的雅趣与惬意,不露痕迹地表达出来。
结句“诸公莫惜今朝醉,一日清闲一日仙”,可谓曲终奏雅。诗人说,在如此的吉日佳节、良辰美景之下,你只管尽情地一醉方休吧,一切的忧愁、焦虑、苦恼,今天都已不复存在了。浮生难得是清欢,一日清闲一日仙,这其实是人生顿悟的智慧与超越,难得此语一出,便如此撩拨情性!
之二:珍珠泉上,荷叶为杯碧筒饮
济南端午,荷叶田田,红榴照眼,一场文化盛宴——碧筒饮在济南泉湖如时展开。
清代,作为山东最高官府衙门山东巡抚署的珍珠泉上,我们且看是一番何等的端午景象。
乾隆初年,山东巡抚朱定元有《午日东抚署中偶咏》诗,为我们展现了珍珠泉上端午节的真实情形:
榴火燃天景物移,海东又遇浴兰时。
珠泉照影清于水署西有珍珠泉,荷叶称觞香沁脾是日荷叶为卮。
採艾因思医宇宙,佩符恒欲净边陲。
何须䌽缕缠吾臂,自有胸中五色丝。
(清乾隆六年刻本《静宁堂诗集》莅东草)
朱定元(1687——1770),字象乾,号奎山。贵州黄平人。康熙五十二年(1713)举人,历仕康雍乾三朝。尤娴水利,累任河工厅道,多治绩。乾隆间官至河南布政使、山东巡抚、内阁学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十四年因足疾致仕。生平藏书数万卷,有《四书文稿》、《静宁堂诗集》。
在历任山东巡抚中,朱定元从政能力超强。
山东原本军事管理混乱,有总兵而无提督,影响地方秩序。朱定元上疏请加河南、山东巡抚提督衔,由巡抚统筹军地秩序,这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为树立良好社会秩序与风尚。朱定元令山东各府州县广行教化,有一事近于孝悌者,从而嘉奖之,大则给匾褒奖,小则语言鼓励。而不孝不悌者则反之:“先加化导,继严饬禁,大则以律问拟,小则杖笞示戒。”另外,朱定元还强化社会治安,大力捕盗,捕获山东老瓜贼犯十八名,又续获巨窝积盗。(参见道光《济南府志》卷三十七朱定元传)
朱定元的行政举措大见成效,受到山东百姓的赞同。其幕僚岳梦渊称:“其道路之讴思,建树之卓越,尤彰彰在人耳目。”(岳梦渊《静宁堂诗序》)
而时任山东学政的徐铎则称道朱定元:“处处劳心,美政无惭制锦;时时脱手,新诗有似弹丸。”(徐铎《静宁堂诗序》)
我们来看朱定元诗。午日,端午日。东抚署,山东巡抚署。
“榴火燃天景物移,海东又遇浴兰时”,“浴兰”节,即端午节。端午节的典型风物,是榴花,五月,有“榴月”之称,所谓“五月榴花照眼明”(韩愈《题榴花》)、“榴花角黍斗时新”是也,而“榴火燃天”一语,足见抚署内榴花盛开之灿烂、壮观美景。

“珠泉照影清于水署西有珍珠泉,荷叶称觞香沁脾是日荷叶为卮”,我们随着诗人的吟唱来到抚署西侧的珍珠泉上,佳节的珍珠泉犹如一面明镜,可以清晰地照见人与物的影像,卮,酒杯,荷叶为卮,正碧筒饮是也。清代诗人董芸有《使君林》诗:“使君林下起清风,荷叶为杯号碧筒”,正此意也。我们可以想见,正是在端阳这个美好的季节里,朱定元特意在珍珠泉上,以济南的“特产”碧筒饮来宴请他的属官与幕僚们,这是十分令人振奋且难忘的人生际遇呀!
“採艾因思医宇宙,佩符恒欲净边陲”,这是朱定元借端午风俗来抒发自己的心志与情怀。“艾符”,已见上解。朱氏说:我的“採艾”与“佩符”,不是为了个人的消除祸殃,而是为了“医宇宙”“净边陲”(当时边陲为多事之秋),作为一名封疆大吏,这是难能可贵的雄才大略。所以,他说自己无须像别人那样,将五彩丝缠在臂上以求长命,因为以国家、民众为本的“五色丝”,正时时存在于他的胸中呢!
壮怀激烈!
由此诗我们还可以看到, 清乾隆《历城县志》称济南碧筒饮自端午节开始(“士大夫携酒泛舟,作折筒饮”),委实不假,此诗即一证也。
之三:德王府内,笙歌乐舞度端阳
如果放在几百年前的珍珠泉大院,那是明代德王府时期,这端午节过得会更加排场、更加阔绰的。原来。每逢此时,德王都要大摆宴席,招待、犒劳山东的地方官员们的。
明代嘉靖初年山东巡抚陈凤梧《五日珠泉宴赏》:
隔年游赏此重来,更喜端阳管钥(疑“弦”之误)催。
泉面风微摇爽气,崖头日霁净浮埃。
金鱼尾戏晴波动,玉蕊花临碧岸开。
亭午席间无暑到,恍疑弱水护蓬莱。
(明刘敕编万历刻本《历下十六景诗·白云霁雪》)
陈凤梧(1475——1541),字文鸣,号静斋。明代江西泰和(今江西省泰和县)人。弘治九年(1496)进士,历任湖广提学佥事、河南按察使,官至右都御史。嘉靖元年(1522),以副都御史巡抚山东。
五日,有下面诗句中“端阳”可知,为五月五日端午节;珠泉,珍珠泉;宴赏,谓德王设宴犒赏。
“隔年游赏此重来,更喜端阳管钥(弦)催”,隔年重来,可知德王每年端午节都要举办这样的犒赏活动的,端阳时节,德王府管弦齐奏,笙歌乐舞,而在珍珠泉上摆开宴席,招待前来的有头有脸的地方官员。显然,一般人是无缘此会的。
“泉面风微摇爽气,崖头日霁净浮埃”,珍珠泉边的清爽之气,崖头丽日的明净之感,令人心旷神怡。珍珠泉内,锦鳞戏水,晴波涌动;岸边则玉蕊临镜,美艳无比(“金鱼尾戏晴波动,玉蕊花临碧岸开”),在这样的环境中,即便炎热的仲夏,席间依然清爽宜人,没有丝毫暑热的感觉,倒是感觉自己恍如到了弱水环绕的蓬莱仙境一般,舒适无比。
明人刘敕在《历下十六景》中这样形容德王府:
德藩内有濯缨泉、灰泉、珍珠泉、硃砂泉共汇为一泓,其广数亩,名花匝岸,澄澈见底,亭台错落,倒影入波,金鳞竞躍,以潜以泳,龙舟轻泛,箫鼓动天,世称人间福地、天上蓬莱,不是过矣。
之四:百脉泉畔,踽踽身影吊屈原
清康熙四年乙巳(1665年)端午节的下午,一位孤独的悲剧诗人来到章丘明水镇百脉泉上,感念身世,抚今追昔,不胜感伤,他由自己的身世联想到古代屈原沉江的故事,写下《五日宿明水镇游百脉泉六首》。
他是济南府淄川县著名诗人袁藩。
袁藩(1627——1685),字宣四,号松篱。康熙二年(1663)举人,拣选知县。诗文有名。著有《敦好堂集》行世。
这袁藩乃是富于个性之人。他是诗人,也是个痴迷的收藏家。乾隆《淄川县志·续文学》说他:
读书精于搜罗名山石室之藏,购求装潢,不遗余力。尝得苏长公(苏轼)所题孙莘老(孙觉)风字砚,尽出所有古玩易之。又于东海获一秦镜,自为题咏,一时文人皆属和焉。
袁藩老乡、清代嘉道间诗人、学者王培荀《乡园忆旧录》曾录这首袁藩自为题咏的诗,并称此诗问世后的盛况说:
一时和者累累。刻《古镜诗》行世。今惟念东、渔洋两先生题诗存本集中,余不可见。《古镜诗》刻本亡矣,镜亦不知落于谁手。故存其诗。
袁藩还喜欢旅游,且游屐所至,著述满箧。《乡园忆旧录》说他曾经:
南涉大江,过虎林,登采石,往返淞江、苕水之间。又溯三衢、过豫章,返棹鄱阳。所历皆有诗,名其集曰《远游草》,共一千五百余首。
然而,如同他的淄川老乡蒲松龄,袁藩心中最痛的伤疤也是科考的失利,虽说他的功名略高于蒲氏。
袁藩写过一首著名的闱中诗,其悲苦程度令人不忍卒读。王士禛在《池北偶谈卷十八》专门收录这首诗,并写下袁藩不无惨淡的生命轨迹。他说:
淄川袁孝廉松篱藩,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礼经,壬戌尚困公车。闱中赋诗云:“二十年前古战场,卧听谯鼓夜茫茫。三条画烛连心热,一径寒风透骨凉。苦向缁尘埋鬓发,凭谁青眼讬文章?明宵别后长安月,偏照河桥柳万行。”武康陈孝廉兴公之群吟之,至泣下。是科袁竟下第。乙丑病蛊卒。
《五日宿明水镇游百脉泉六首》有序,虽则偏长,但笔者不忍割爱,因为它是如此真切地写出了诗人的处境及感受,还有,二十年间百脉泉的沧桑变化:

百脉泉在阳邱城东南三十里。余往来济上,道必经此。记乙酉春同友人游寺中,时干戈甫静,景物萧条,旅况悽凉,田畴未垦。及入寺门,春波漾绿,新柳增妍,顾而乐之。再十年,同苏若佩重游,则佛宇倾圮,石甃陷泥淖中矣。时正季秋,霜净波明,一池如镜。读壁间李太常先生诗,步其韵得二首。及今不觉又复十年,端阳自祝阿还,日晡憩此。则庙貌重新者四年矣。宏厰虽复旧观而垂杨辄已老丑,石阑渐就剥落。凭吊畴昔,意惝怳不能自持,出凭石上卧听流泉,远望长白,诸峰湛湛,浮水面爽气逼人,因念客况无聊,佳节犹旅食也,听隔垣竹树中俦坐,浮白为欢,此日而余潦倒支离,正不减三闾大夫憔悴江潭,岂不悲哉。因随笔识之如左。
篇幅所限,我们只能六首选二以飨读者。
之五:
才过山雨麦初黄,波涨畦田露稻秧。
是处鹫峰留盛迹,何年龙窟驾飞梁?
深林五月云衣湿,远岫千层水面凉。
欲赋灵均人不见,离骚读罢咏沧浪。
之六:
胜地寻来兴渺茫,惊心客里又重阳。
池边艾叶窥丝鬓,野外熏风度薄裳。
静夜鲛人珠泪冷,晓天神女舞衣凉。
莓苔满迳无人到,明月空留薜荔房。
(清钞本《敦好堂诗集》卷二)
令人唏嘘!也许,正是屡困场屋的坎坷遭遇,使得袁藩体味到了社会与官场的黑暗、腐败与不公,使他拥有了更多的平民意识与平等思想。由诗中“欲赋灵均人不见,离骚读罢咏沧浪”“莓苔满迳无人到,明月空留薜荔房”等诗句里,所表述的袁藩对于屈原的崇敬与叹惋来看,任凭命途多舛,他作为正直文人的骨气与志节是不会改变的。
之五:郊坰汲泉瀹茗,士子羡煞农家乐
当年,济南东城外有柳行村,老百姓俗称柳行头。是一清泉淙淙的景致胜处。至今此村尚在,不过已经彻底城市化了。
距今350年前的清代康熙初年,一个端午节的前一天,一位士子冒着暑热,行色匆匆路过此村,然而,他却被村旁菜圃中的淙淙流泉吸引住了,他于是停下来,与灌园人有了一次幸福的相遇,并作诗于壁上,专记此事。
此人是明末清初济南府名士王樛。
王樛(1627——1665),字子下,号息喧。清初济南府淄川县人。明司农王鼇永子。九岁从父通州署中,读书过目不忘。入清,由銮仪卫指挥佥事,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以疾卒。著有《息轩草一卷》《云中杂咏》等。
诗的题目较长,概述了这件事情的全部过程:《重午前一日行次柳行村,渴甚,小憩村旁蔬圃中,茂树招凉,小亭来风,汲泉瀹茗,聊设枕簟,因题二绝句壁上》。
诗人说:他在端午节前一天路过柳行村时,盖因天热,他口渴至极,不承想,村旁菜圃中有淙淙流泉,他于是停下来,受到灌园人的热情款待,先是“汲泉瀹茗”,其后又帮他“聊设枕簟”,在“茂树招凉,小亭来风”的蔬圃凉亭下,他美美地睡了一觉,然后深有感触地说:还是当一个“画圃灌园”的普通老百姓好呀!
诗有两首,我们且来欣赏其一:
筍舆常扑庾公尘,触热还为褦襶身。
独酌寒泉寻午梦,总输画圃灌园人。
(民国七年顺和堂石印局石印本《王氏一家言》
卷十五《银台公集》)
筍舆,竹制的轿子,旧时为有身份、地位的人所乘坐。庾公尘,典出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轻诋》:
庾公权重,足倾王公。庾在石头,王在冶城坐,大风扬尘,王以扇拂尘曰:元规尘污人。
这段故事是说,庾公(庾亮,字元规)权势很大,足以压倒王公贵族。庾亮在南京,王导在冶城坐镇。一天,大风刮起了灰尘王导用扇子扇去灰尘,并说:元规用尘土污染我!
此典被后人喻为:权贵的气焰逼人!
“筍舆常扑庾公尘”,显然蕴含着诗人深深的命运感慨,济南是都会,诗人眼见得一个个富贵人家乘轿子扬尘而去,而自己却忍渴受暑,辛苦赶路,心下不平可知,既而诗人自我安慰:这又热又渴应该是衣服穿得厚了(“触热还为褦襶身”),是的,终年在外为功名奔波的士子,必得随身携带几个季节的衣服方可,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
“独酌寒泉寻午梦,总输画圃灌园人”,幸好,遇到这位热情好客的“灌园人”,不惟喝到清凉解渴的泉水泡茶,还能美美地睡个午觉,真的好生羡慕着如同图画的美丽菜圃,还有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平头百姓“灌园人”呀!


中国鹰王——王照华绘
独家代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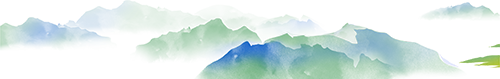

中国鹰王团扇大师王照华作品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