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难忘恩师情
——忆孙昌熙教授
张 杰(93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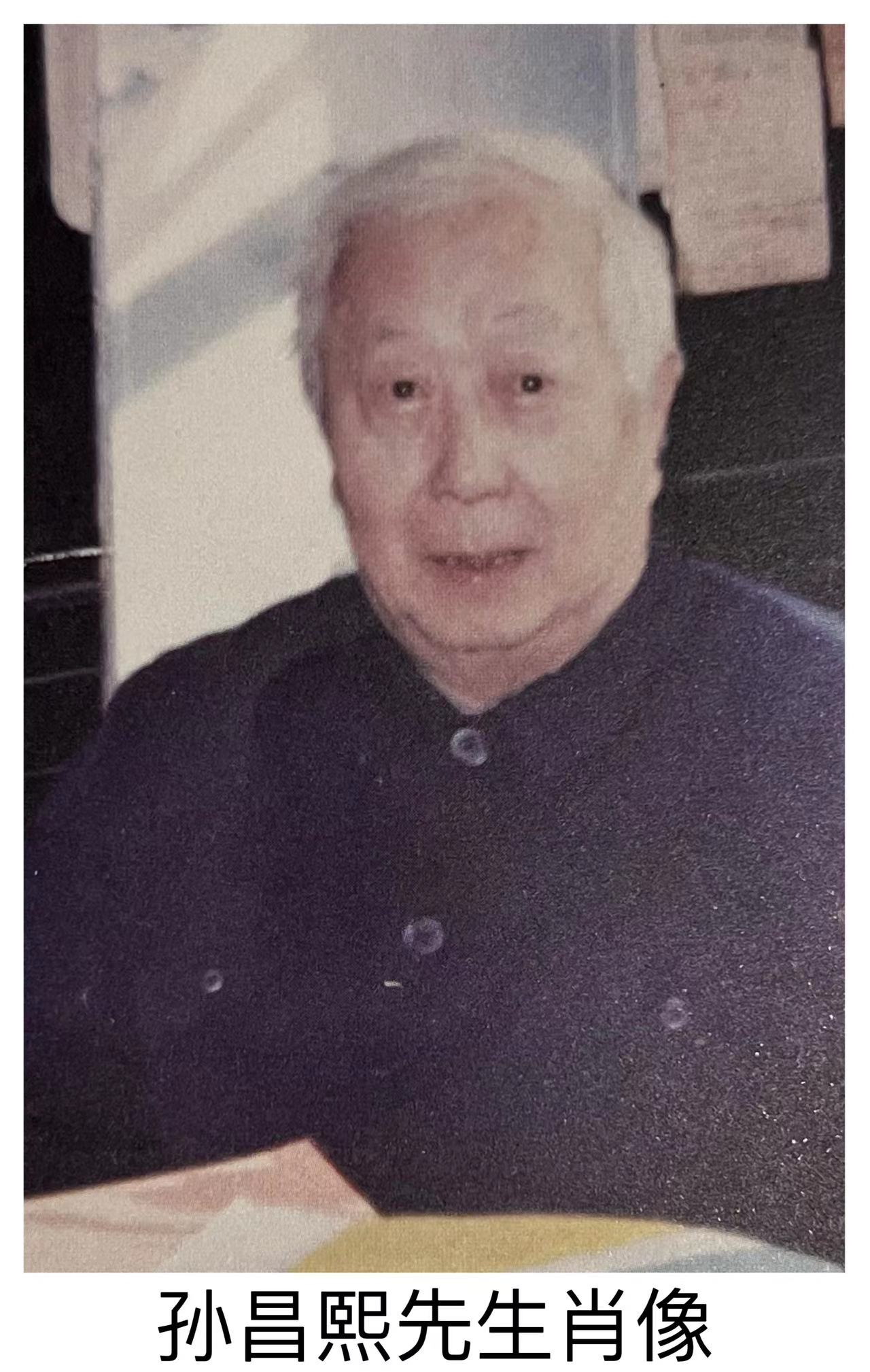
一
1951年3月,我进入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学习。那素有“东方瑞士”之称的美丽的海滨城市,那如花似锦的山大校园,使我心潮澎湃,激情难抑。还有那一位位闻名遐迩的教授们更使我敬佩不已,在给我们授课的诸多老师中有一位令人注目的年轻人,他就是孙昌熙先生。
先生给我们开设现代小说选讲课。上课铃一响,他就迈着矫健的步伐走上讲台。当时他 30多岁,中等身材,白白的脸庞,一头乌黑浓密的卷曲头发,在那和蔼可亲的脸上有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一走上讲台,闲言少叙,打开讲稿就开始讲课。他所选的文章大都是刚刚在报刊上发表的新作。他是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条件下,全凭着自己的理解将作品分析得头头是道。他那独到的见解,那风趣的语言,使课堂气氛十分活跃,不时发出阵阵笑声。他将我们这些求知欲很强的青年学子们征服了。
五十年代初期,在华岗校长的倡导下,山大中文系在我们班率先开设鲁迅研究课。华校长讲授鲁迅的思想,孙先生、刘泮溪先生、韩长经先生讲授鲁迅的作品。后来他们将讲稿整理出版了《鲁迅思想的逻辑发展》(华岗著)和《鲁迅研究》(刘泮溪、孙昌熙、韩长经著)两本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较早的研究鲁迅的专著,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1952 年,根据工作需要,我调到山大附设工农速中任教。不久,先生由现代文学教研室调到文艺理论教研室任主任,同时开设文艺理论课。而我却没有机会听这门课。然而我在教学之余常写些文艺通讯之类的文章,在先生主编的校刊上发表,我也常到校刊室坐坐,我们师生仍保持着联系。
1955年秋季,经领导批准我回到中文系继续学习。当时,先生刚开设选修课《文心雕龙》研究。他那认真负责的教学态度,那对问题鞭辟入里的透彻分析,那幽默、风趣的教学风格一如从前,使我惊讶的是,他的古典文学修养也十分深厚,真是博古通今!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文革”开始以后,听说先生吃了不少苦头,我十分挂念他。
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怀着无比喜悦之情到山大去看望先生。他当时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他已接受了国家委托的重点项目《鲁迅全集》中的《故事新编》的注释工作; 他除给本科生讲课外,正准备招收研究生的工作。我提出找个时间请他到我校作学术报告,他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1980 年秋天,我邀请先生和孟广来同志来我校讲学。他讲的题目是《<故事新编>新探》,盂广来讲的题目是《中国戏曲和中国话剧之比较》。他们的精采演讲受到同学们普遍的好评,获得很大的成功。我陪他们游览了泰山和岱庙,在泰安度过了他一生中难得的轻松愉快的几天。
二
建国初期,我曾先后听过先生讲授的三门课,这为我一生从事文学事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新时期以来,先生在工作上给我以多方面的支持:
我担任中文系主任之后,他曾两次亲临我系讲学,开扩了学生的视野,活跃了我系的学术气氛。
为了加快教师队伍建设,我系曾选派了几位优秀青年教师,请我省几位著名专家指导进修。当我去济南和先生协商,请他指导魏建同志进修时,他立即答应。在以后的日子里他对魏建精心培养,热情帮助,经过一年的时间,魏建的水平有了显著的提高,先生与魏建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当魏建进修即将结束时,我专程去济南对先生表示感谢。他说,魏建是个上进心强、思想活跃、品德很好的青年人,我非常喜欢他。我很想把他留下给我当助手,但是考虑到你们那里更需要他,为你们的事业着想,我还是希望他按时回去。我听了这些话,十分感动。
1985 年我担任学报主编。我向先生约稿。他先后给我们寄来了《〈世说新语〉给鲁迅以艺术启示》《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鲁海”无涯苦作舟》,还有他和研究生张华同志合写的《茅盾论鲁迅小说的艺术贡献》等文章。像先生这样著名学者的文章能在我们这小小的刊物上发表,不仅使刊物增加了光彩,也使广大读者耳目一新,从中受到不少教益和启迪。
我是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来捧读先生寄来的一篇又一篇佳作的。《把中国新文学抬上大学讲坛的人》一文,作者怀着无限深情回忆了恩师杨振声先生对他的培养帮助和提携,他如何在杨先生的指引下步入小说创作之门,发表了不少富有现实意义的小说创作。他还向人们介绍了杨先生不仅是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还是位有远见有才能的教育家。
30 年代初期,杨先生从清华大学教务长岗位上调至青岛任山东大学校长之职。他在不长的时间就兴建校舍,聘请全国著名学者如闻一多、丁西林、任之恭及著名小说作家沈从文诸先生任教,他“的的确确发动了一场课程內容革新,结构调整活动。他还带头开‘小说作法’课,把新文学课提到了与楚辞研究、诗经研究······同等的地位,而且是全中文系课程的中心和先导”。
在抗战时期,杨先生在筹建西南联大的工作中也有不少建树。为了适应时代潮流和抗日斗争的需要,他亲自开设中国新文学简史与创作实习课; 为了普及新文学教育,他又亲自主持全校一年级共同必修课“大一国文”的编写工作,那教材大部分是新文学。他请朱自清先生带着孙先生也讲授这门课。先生在文章中说:“杨振声先生在西南联大为中国新文学披荆斩棘地开辟道路,或者说‘打天下’,是胜利的,那标志,就是新作家群的不断涌现。先生培养我只是丰收事业中的一粟。”
 孙昌熙先生和作者亲切交谈
孙昌熙先生和作者亲切交谈
三
先生对我的支持、奖掖和帮助是多方面的:80年代中期,我和友人合写了《高兰评传》,脱稿以后想请先生为之作序。他欣然同意。
在《序言》中,他高度评价诗人高兰和他的诗作:
“伟大的抗战时代迫切需要战斗的文艺武器,高兰先生的朗诵诗便应运而生。人以诗立,于是高兰便名播海内外,成为朗诵诗的开创者,著名诗人和评论家,领袖诗坛一角亘60年。” “诗人的一生,与前进的时代同步,他的诗笔绘出了时代的主要面貌,他的诗篇吹奏出时代的节奏。”
先生对《高兰评传》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它深刻描绘出朗诵诗独创者的活生生的形象,传记文学真实的形象。” “像这样一部完整的评传,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个创举。” “它也弥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朗诵诗章久缺的空白。而且不仅如此,更由于《评传》沉甸甸的学术性与独创性的艺术结合,这就同时在传记文学领域,亮起了一颗新星!”
我和文采对这篇序言都曾反复诵读,对先生感激之情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
80 年代末,我将一部分回忆性散文结集出版,想请先生为之作序,他欣然同意。他看完书稿后建议将书名定为《春风桃李忆吾师》。不久我就收到了先生的序言《化短暂为永久一 序张杰著<春风桃李忆吾师>》。先生说:
“作者所怀念的是学府名流,而且是作者化雨春风的座师,因而不仅情感浓烈,而且书味生香,真如陆机所说:“石韬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文赋》)
“凭一己之努力,独铸先师诸像于巍峨学术殿堂,供读者礼拜,这恐怕是学术界难得之举”。
“总之,读本书,巡礼张杰同志用心血建起来的座师长廊中,使人感触万端,徘徊在座师像前,不能遽去。而座师虽风采各异,贡献有殊,却都是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而献身。其感人力量,正从这里喷薄而出。而作者张杰同志则祝愿其先师千古永恒!学统绵绵,不要出现‘断层’!”
《序言》对书的写作动机、特点和出版意义的分析非常深刻,使我在认识上得到了升华。还有那优美的辞章,那诗一般的语言,更使我击节叫好,敬佩不已。
先生为了进一步扩大该书的影响,后来又将“序言”发表在《文史哲》1990 年第3期上。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
1995年夏天,我又将一部分回忆师友的散文结集为《翘首东海忆故人》,准备在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我想请谁写“序”呢?当然是先生最好,他对我写的这些人最熟悉,对我也最了解,而且他在学术界又有很高的威望。但考虑到先生的视力已相当差,我实在不忍心麻烦他。我考虑许久,终于想了个妥善的办法:我将该书的内容向先生作个较全面的介绍,有重点地再读一部分,请他构思之后由他口述,让他的学生,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同志执笔整理。我将这个想法分别征求先生和魏建的意见,他们都很赞同。8月中旬就收到了这篇“序言”。题目是《让真情长留人间——序张杰著<翘首东海忆故人>》。先生说:
“······ 张杰是用眼泪甚至是用生命写成的这些文章。它们是友情的结晶,是心血的结晶,它凝聚了人间的真、善、美。它让美好的真情永驻人间。”
我手摩“序言”,沉思良久,80 岁高龄的先生是这么认真地构思这篇“序言”,真使我感激不尽!于是,我在该书“后记”中说:
“我的老师孙昌熙教授,过去曾多次为我的著作撰写序言,给予我不少的鼓励和支持。现在他已年过八旬,为奖掖后进,仍然不遗余力; 只是由于他的视力很差,已不能执笔为文,不得已,本书的序言,只能由他口述,由他的学生魏建教授笔录了。”
四
新时期以来,先生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到学术研究中去。他先后完成了《鲁迅文艺思想新探》《鲁迅“小说史学”新探》等学术专著。他主编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现代小说史》等教材。他发表了不少富有开拓性和创新精神的文艺论文,如《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研治古典文学的成就》一文,就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然而,由于在“文革”劫难中,他遭受毒打,致使他的眼睛因创伤造成了青光眼疾患。开始是眼压升高,视力逐步减退,阅读和写作不得不借助于放大镜,嗣后,连出门走路都十分困难,以至于最后的完全失明。
先生面对将要失明的眼睛,焦虑万分:他埋怨天气不好,其实天气很好; 听师母说,他常为点小事就发火。我经常去劝慰他。他让我问问眼科专家是否可以做手术,即使将视力恢复到0.1度也好啊!于是,我拿着他的病历先后到解放军 88 医院和泰山医学院等地向眼科专家请教。他们的答复几乎是共同的:不能做手术。对此,先生是非常失望的。
先生晚年经济也比较拮据。师母原在机关工作,“文革”前,她响应号召辞职回家。她身体多病,生活费医疗费全部自理。80 年代后期全家才“集资”买了台电冰箱,连部电话也安不起。我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时任山大副校长的老同学乔幼梅教授,她对先生深表同情,学校终于给先生安上了电话。
1994 年春天,听说先生患肺癌住院,但当时并未把真实病情告诉他。魏建告诉我,先生的家人和他的学生研究,因先生年事已高,难于承受手术之苦,以采取保守疗法为好。随即,我带着照相机,赶到医院,让魏建给我们照了一张合影,以作为永久的纪念。这是我和先生最后的一张合影,我一直珍藏着。此后,我每过一段时间就去济南看望先生或用电话问候。
1998 年9月20 日,我突然接到先生于9月18日逝世的讣告。我立即赶往济南,眼含热泪向我的恩师作最后的告别。归途中我思绪万千,不能自已,想了很多很多······
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研究鲁迅,他以学习鲁迅,发扬鲁迅的光荣传统作为终生之事业。他为人正派,爱憎分明。他曾担任山东省人大代表、济南市人大代表、山东省鲁迅研究学会会长、山东大学图书馆长等职。他曾被评为优秀教师和模范党员。
先生非常尊敬他的老师,直到晚年还怀着深情写了回忆杨振声、朱自清等恩师的文章。先生十分珍惜友情,他和刘泮溪先生是同学、同事和挚友。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情同手足,亲如家人。刘先生谢世后,他家中的事情都征求先生的意见。他和著名鲁迅研究专家单演义教授是老朋友,晚年,他用十倍的放大镜怀着无限深情写了回忆单先生的文章。
先生非常爱护学生对弟子是一片真诚,“和蔼若朋友然”。弟子每有所求,他总是慷慨相助,鼎力支持。
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踏上文艺的征途。他是位有成就的作家,是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学养深厚、视野开阔的著名学者。他在文艺界 、教育界、学术界享有盛誉,受到学生们的爱戴和广大知识分子的敬重。
我记得先生在谈到诗人高兰时曾说过:“纵观诗人的一生,在其生活中,尽管有过生活的花朵,也有过甜蜜的短暂,但崎岖或坎坷,则是其生活的主调。(《<高兰评传>序言》)。我想此话对于先生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先生从青年时代起就背井离乡,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人到中年又一次次遭受“运动”的劫难,受尽了人间的凌辱和摧残。新时期终于到来了,正当他大展宏图之时,眼疾却日渐加重以致于完全失明,其心中之痛苦可想而知。我每每想到这些,真是肝肠寸断,悲愤万分!
然而,他那丰富的著作与他那不朽的名字在现代文学学术殿堂里将永放光芒!弟子们也将永远铭记着这位敬爱的导师!这是足以慰藉先生在天之灵的!
2000年9月18日初稿
2023年5月15日泉城定稿
张杰 教授
山东省新泰人,1931 年1月生,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泰山学院教授,离休干部,曾任泰安师专中文系主任、《泰安师专学报》主编、《泰山研究论丛》主编、泰山文化丛书执行主编、山东服装学院院长等职。著有《现代三作家论集》《高兰评传》等学术著作,散文集《春风桃李忆吾师》《翘首东海忆故人》,诗集《心中的歌》《筛月楼诗稿》《筛月楼诗稿续篇》等。

中国鹰王——王照华绘
独家代理


中国鹰王团扇大师王照华作品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