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天问——寻找中国人的最高信仰
胡春雨
中篇望岳:唯天为大
典出《论语-泰伯》:“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风俗通义》:“尧者,高也,饶也。”

遥望泰山之巅,问的是天道,观的是天下,悟的是天人。一部《中庸》,塑造中国人的性格,开篇第一句,便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譬如天命、天性、天理、天良,中国人认为,人类生命来自天地化育,一切禀赋来自上天赐予,一切文化由此展开。是为“天人合一”,并非二元对立。我们的“上古圣神”,无非“继天立极”,留下“道统之传”,奠定文明丕基。这种思想,与源自古希腊的“自然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礼记-礼器》云:“礼者,反其所自生;乐者,乐其所自成”。华夏祖先以虔诚之心、祭祀之礼致敬上苍,让生命原本复始,实现价值;顺应天地大化,代代繁昌,为构建中华文明奠定终极依据。其中最庄重、最神圣的形式,便是封禅泰山。

据《管子-封禅》追述,“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其中能够回忆的有十二家。从上古时代天真未凿的无怀氏开始,中经三皇五帝,下至三代明王,对上天的礼敬伴随整个中国文化史。我们与其怀疑古史的恍惚,不如仰望祖先的虔诚,不能因科学文明的刺目看不见天道之大。《五经通义》揭示封禅的崇高意义:“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何?天命以为王,使理群生,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寥寥数言,揭示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基本理念:自古“继道统而新治统”,政权更替在所不免,文化精神万古常新。仰体天心,临深履薄,建国立政的意义在于代天理物,兴致太平,民生才是历史进化的重心。
关于封禅的仪节,《史记正义》云:“此泰山上筑土以祭天,报天之功,故曰封;此泰山下小山除地,报地之功,故曰禅”。所以如此安排,《白虎通-封禅》解释,“天以高为尊,地以厚为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报天,附梁父之基以报地。明天之命,功成事就,有益于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核心是一个“报”字,既是对上天的报答,更是对上天的报告。其中隐藏的深意,用《墨子-天志》的话说,“天子未得次己而为政,有天政之”,有国者必须畏天之威,不容肆意妄为。“然则率天下之百姓以从事于义,则我乃为天之所欲也,”政权最终的合法性,在于顺应天意,践行天道,服务天民,方为“有益于天地”。

这种政治伦理,始终与中国人的天道信仰相表里。《诗经-玄鸟》赞颂殷人的光荣:“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从生命的赐予到天命的眷顾,追本溯源,莫非天赐。然而天心所在,无非民生利病,《诗经-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国家的主要职能,在于顺应天然伦理,推行道德教化,实现社会建构,《诗经-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心并非玄远不测,《尚书-皋陶谟》云:“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威。”《尚书-泰誓》又云:“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人民代表天心所向,决定天命所归。《左传-文公十二年》总结中国人的世界观:“其在《周颂》曰:‘畏天之威,于时保之’。不畏于天,其何能保?”这种政治传统,被梁启超先生概括为“其形质则神权也,其精神则民权也”,乃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要义。
中国人信仰上天,就像西方人信仰上帝,穆斯林皈依真主,关乎各自文明根性。祭祀以独特方式承载核心价值,祭天,明的是天道。《孔子家语-郊问》云:“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也,”来自中国人深沉的生命意识。与西方人不同,中国人的上帝乃天道的化身,代表着宇宙大化与运动规律。程子说:“天者,理也;神者,妙万物而言者也;帝者,以主宰事而名”。在中国人看来,上天的伟大只是一个“至诚无息”,《孟子-离娄上》云:“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人对天的信仰在于诚挚之心,复归本然之善。《孟子-尽心上》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程子解释其中原理,“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谓之天,自秉受而言谓之性,自存诸人而言谓之心。”是为“天人一也”,乃一口“浩然之气。”
可见,祭祀与迷信无关,贵在以神圣的形式、艺术的表达、心灵的慰藉,寄托文化理想,树立民族信仰。《礼记-礼运》云:“故先王患礼之不达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所谓“五祀”,迄今遗风犹存,《论衡-祭义》解释,包括“门、户,人所出入;井、灶人所欲食;中溜,人所托处。五者功钧,故俱祀之。”立足根本,扎根生活,形成完整的礼乐体系,塑造诚实笃厚的国风民俗。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靠文化陶冶不靠口头说教。

董仲舒总结中华文明的特质,“道之大源出于天”。在生命本体上,《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以为,生命来自上天赋予,故人之所以为人本于天,譬如“人之血气,化天志而仁;人之德行,化天地而义。”总之天与人的关系,“天之副在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包括了天性、天良这些中国人至今深信不疑的基本观念。在社会政治领域,主张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阐扬王道理想,其解释政治原理:“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主张效法天道,顺应天时,譬如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庆赏刑罚,“异事而同功,皆王者所以成德也”,天人道理相通,故“圣人副天人之所行以为政。”与同时代罗马帝国的塞涅卡等西方先哲相比,两者同样主张自然是天地与宇宙的代表,调节人类世界。只是中西文明一个天人合一,循着天道前行;一个天堂地狱,走向上帝信仰。
从泰山的历史看,天道信仰不仅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特质,而且塑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尚书》阐扬中国政治文明从《尧典》开始,大舜受禅后首先举行大典,“肆类于上帝”,向上天报告担负起天子之任,随后踏上巡狩四方的征程。王者的足迹不可能遍布天下万国,雄镇四方的岳山,遂成为各方诸侯朝会的坐标。大舜的第一站当然是泰山,“东巡狩,至于泰山,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后,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以上天的名义,在泰山大会东方诸侯,在意识形态上、基本制度上、用人行政上,推动早期中国的深度融合与国家治理。可见,泰山是文化山,信仰山,也就包含了政治山,为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的成长作出了重大贡献。“泰山安则天下安”,其中深意,耐人寻味。

至于封禅作为祭天的最高形式,其隆重远超登基大典,一个时代只有地平天成、天降祥瑞,才有资格考虑,往往数百年不遇。功高德厚如唐太宗者,尚迟疑再三,最终没有封禅。秦始皇扫平六合,自以为“功高三皇,德过五帝”,东封泰山却留下了千古之讥。《史记-封禅书》记载,“始皇之上泰山,中坂遇暴风雨,休于大树下。诸儒既绌,不得与用于封事之礼,闻始皇遇风雨,辄讥之”。一个政权,比得罪精英阶层更可怕的,是得罪天下百姓。《老子》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个道理化作民间传说,把历史写照的更加生动。大树上有神人讥之曰:“无道德、无仁义、无礼而得天下,妄受帝命,何以封?”始皇三十六年,泰山天降陨石,百姓刻书“始皇帝死而地分”,获罪于天的大秦帝国,在人民的诅咒中灰飞烟灭。
在封禅这样重大的问题上,还是唐太宗具有大政治家的气度。《资治通鉴-贞观六年》载太宗上谕:“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数百年后,当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亲自策划了封禅大剧。历史是最公正的评价者,宋室之举获讥后世,此后千百年间再无封禅。乾隆皇帝六登泰山,三叩九拜,哪怕自诩“十全老人”,也没有决策封禅。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国泰民安,天下泰安,乃封禅大典的文化理想,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报告上天,在于内心的虔诚,不懈的追求,原在不言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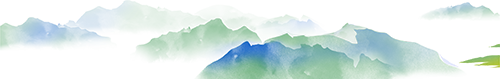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