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精华热点
精华热点 清初孝妇河畔淄川文化圈
赵玉霞
清朝顺治、康熙年间,淄川孝妇河两岸出现了一个文化鼎盛时期,其标志是文人众多、文化活动频繁、文学作品丰富、文化影响深远。其影响,从范围上说,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地域上说,波及到当时整个孝妇河流域乃至全国文坛;从时间上说,甚至一直影响到几百年后的今天。
一、 众星璀璨耀般阳
自明朝中后期的嘉靖年间,淄川文化兴起,中举人进士者多。自嘉靖至崇祯127年间,考中进士29人;在京及外地为官者多,其中不乏高官,如王崇义做过刑部主事,高举做过浙江巡抚,张至发做过明末首辅,毕自严做过户部尚书,仇维祯做过南京户部、礼部、刑部、兵部四部尚书,毕道远做过礼部兼兵部尚书。并逐渐形成了“西毕、东王、南孙、北韩”以及城里高家、张家等几大望族,他们重视教育,又互相联姻,联系密切,互相提携影响,使人才辈出,资绂绵长。
明清交替之际,淄川没受大的屠戮,保护了已然茁壮的文化根脉,因此,清初顺治、康熙时期78年间,淄川竟有37人中进士。整个明、清543年间,淄川考中进士者81人,从明嘉靖至清康熙这约200年时间里,中进士比例竟占了81.5%,所以,尽管朝代更替,淄川却文士多、文化兴盛。他们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其主要成员是高珩、唐梦赉、王樛、孙蕙、毕际有、张绂、袁藩、赵金人、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还有孙琰龄、王敏入、王观正、邱希潜等等。
他们生活于同时代,论年龄,前后相差仅十几岁(除高珩外),如果以蒲松龄出生年1640年为轴,高珩大他28岁,唐梦赉、王樛、袁藩大他13岁、孙蕙大他8岁、毕际有大他17岁、赵金人大他16岁、张笃庆(历友)小他两岁、李尧臣(希梅)小他3岁。年龄相近,没有代沟。
论科举仕进,高珩、王樛、唐梦赉、毕际有孙蕙都做过官,其余的虽未为官,却最低也有秀才的功名,大家都有学问,因而能谈到一起。
若讲彼此间的关系,王樛是毕际有的妹夫;毕际有的夫人是高珩的从姨母;蒲松龄是高珩侄女的舅父,高珩称蒲松龄亲家;张绂和张笃庆是父子,张笃庆是高珩的女婿;唐梦赉和赵金人是好友,两人订“生死交”;赵金人是蒲松龄的从外甥,又是孙蕙、李尧臣的老师;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曾结“郢中诗社”,人称“郢中三友”,是一辈子的好友;袁藩和蒲松龄又是好友,与唐梦赉、张绂等关系非同一般;蒲家与王家也有联姻,蒲松龄称王樛表兄。那时候讲究门当户对,所以淄川望族之间几乎都有联姻。因此这些人就很容易走到一起,并能保持长久的良好关系。
在这个文化圈里,论年龄、资格、学问、威信,首推高珩。
高珩(1612——1697),字葱佩,号念东,晚号紫霞道人,曾任刑部左侍郎。为官清正,为人宽和,诗文皆出色。他是曾做过明朝兵部尚书的王象乾的外孙,其表弟王渔洋赞他“为文千言立就”,写诗“如麻姑掷米,粒粒皆成丹砂”,“诗有元白之风”。《山左诗抄》收录其诗150余首。其著作有《劝孝汇编》《劝善等说》《畏天等歌》《醒梦戏曲》《四勉堂说略》《栖云阁诗文集》34卷等。时人赞誉高珩才如大海、山东文章宗伯、海内通儒、国史笔、骚坛领袖。指导编著康熙《淄川县志》和《山东通志》。
再一个重要人物是唐梦赉。唐梦赉(1627——1698),字济武,号豹岩,别号岚亭,顺治六年(1649)23岁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26岁因谏阻翻译《文昌化书》和《玉匣记》被罢官。他是地方著名文人。人赞他“为文左右逢源,如同悬河决堤,一泻千里,有不可阻挡之势”。其“诗雄浑流畅”,《山左诗抄》收录其诗达73首之多。他领衔编著了康熙《淄川县志》8卷和《济南府志》54卷。他自己著有《志壑堂文集》32卷。他与高珩是淄川这个文化圈的核心人物。
王樛也是淄川文学圈重要成员。王樛(1627——1665),字子下,号息轩,14岁中秀才,清初入朝为官时才17岁,人称"王小官"。官至通政使司右通政。王樛擅长声律之学,著有《息轩草》诗集。其同朝为官的好友高珩评价其诗,说有唐朝著名诗人元稹、柳宗元的风格,称赞他为淄川树起了唐朝贞观、开元、大历诗歌的大旗。
毕际有(1623——1693),字载积,号存吾。曾为江南通州知州,是毕自严的仲子,其夫人是王渔洋的从姑母,也是后来蒲松龄西铺坐馆的东家。他参与编著清康熙《淄川县志》,并特别写了《淄乘征》一书,对淄川历史人物、事件、物产等33条进行了辨析厘正,有根有据,极具说服力。
孙蕙(1632——1686),字树百,号笠山,淄川西笠山村人。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中进士。34岁做江南宝应县知县,为官务实,锐意革除陋俗,去除杂税,减轻人民负担,百姓爱戴,上级也很赏识他。曾聘淄川文化名人蒲松龄做幕宾。曾任江南考试官,后做户科给事中。
孙蕙晚年因丁忧(因父或母去世在家守丧)住在家里,持正义,存仁心,慷慨好施。爱好诗书,曾藏书万卷。自己也写了不少书,有《心谷制艺》《安宜治略》《笠山奏议》《笠山诗选》《历代循良录》《感立篇笺注》等。
张绂,庠生(即秀才),是曾为明末首辅的张至发之孙。参与编著清康熙《淄川县志》和康熙《济南府志》。《淄川县志·艺文志》中选载他不少诗文。
袁藩(1627——1685)字松篱,号宣四。康熙二年(1663)中举,并是经魁(明清科举考试分五经取士,每科乡试及会试的前五名即分别为五经中各取其第一名,即为经魁)。喜作词曲和收藏。有《敦好堂诗》若干卷。参与编著清·康熙《淄川县志》和康熙《济南府志》。《济南府志》载“般阳邑乘之役,删定独多。”
赵金人(1624——?)字晋石,庠生,清初名儒。曾在青云寺设馆授徒,学子慕名云集,其中邱希潜、韩允义都考取功名,走上仕途。喜“推奖士类”,知孙蕙遭“后母之变”,准他免费食宿,精心教导,使孙蕙终于考取进士。
赵金人经常与唐梦赉、蒲松龄、李希梅、张笃庆、孙蕙等“酬唱为乐”。其著作有《借山楼诗文集》《四六骈言》等。
张笃庆(1642——1715),字历友,号厚斋。拔贡(贡生:被推荐到国子监读书的秀才;拔贡:经地方和京城选拔的操行、成绩双优的贡生)。才高学富,14岁作《梦游西湖赋》,20岁已作有乐府诗200首。常与唐梦赉、孙蕙、赵金人及其二弟履庆唱酬为乐。王渔洋赞他“真冠古之才”,又赞他“七言歌行尤为擅场(技艺高超出众)”;《淄川县志·文学》评价他“生平撰述等身,浩如烟海,不可涯涘”;《四库全书总目》评他“才藻富有”,“动辄千言”,“不可节制”。其著作有《八代诗选》《班范肪截》《五代史肪截》《两汉高士赞》《昆仑山房集》《古文集》。
李尧臣(1643——?),字希梅,号约庵。诸生。“居家孝友,笃嗜诗书,号称博洽(《淄川县志》语)。”康熙年间分攥《府志》,极为当事所称赏。著作有《百四斋文集》10卷,《诗集》1卷,《笔势》1卷,《书谱》2卷。《山左诗抄》也收有他的作品。
蒲松龄(1640——1715),字留仙,号柳泉,岁贡生(按年龄、资格等推荐的贡生)。著有《聊斋志异》12卷、《文集》4卷、《诗集》6卷等等。
以上11人,加上其他诸人,共十几人,都极富才学,能诗能文,他们共同组成了淄川当时这个热闹的文化圈。
二、 吟山咏水寄豪情
他们还曾经结伴出游,1673年夏,高珩、唐梦赉、张绂、蒲松龄等8人游了崂山。他们路过诸城超然台,蒲松龄还写了《登超然台》的诗,《聊斋志异》有两篇与崂山有关的故事:《香玉》和《崂山道士》,不知是否为蒲松龄等崂山听来的。
1674年夏,在唐梦赉倡议下,又游览了泰山。这次出游,除了原有人马,还增添了毕际有、张笃庆等。乘车骑马几日夜,夜宿泰山顶,第二天看到了日出,欢呼雀跃。于是或诗歌、或文赋,抒发豪情。高珩写了数首诗,唐梦赉写了观日出的游记散文,还结识了道行高深的僧人元玉;蒲松龄除写了《登泰山》三首诗,还写了一篇《秦松赋》,同时,还搜集了大量素材,为创作有关泰山的部分小说打下基础,这26篇小说,如《云翠仙》《胡四姐》等。
总之,这些文人才俊,有时寄情于风景,放歌于山水之间,有时家中聚会,斗酒百篇。高珩、唐梦赉、毕际有等人家中,经常高朋满座,文士盈门。高、唐在世时期,这个文学圈子活动最频繁,也最兴旺。他们结社(如蒲松龄等人曾结“郢中诗社”),互相切磋,提高诗文水平;他们奖掖后进,互相鼓励,使得后来居上,如高珩、唐梦赉先后给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作序,评价赞誉,高珩还把书带到京城,为他传播,使《聊斋志异》迅速得到世人瞩目。因此,使蒲松龄、张笃庆、李尧臣等文人迅速成长起来。
三 、繁荣文化利民生
这支文人队伍不只留下了大量诗作,还有文章著作。并且,他们的好多文章是为淄川的政治经济生活而撰写,从而改变了当时淄川的面貌。在这个文化圈中,高珩曾在京为高官,清正廉洁,德高望重;唐梦赉曾为翰林院编修,文名扬天下,所以百姓敬服,县令也仰重。他们回乡后,作为乡绅,有威望,有热情,有水平,为家乡办了不少好事。他们撰文募化,帮助本县振兴教育,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繁荣文化,移风易俗,在重修淄川学宫、般水官坝、孝妇河六龙桥、郑公书院、建义仓、县府立旌善瘅恶亭等善事中都起了首倡或推动作用,助力重修兴教、宝塔、青云、禹王等寺庙,引导人们行善积德,使家乡风气为之一新。淄川当时诸多方面的改变,都为临县所钦仰。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高珩、唐梦赉领衔纂修了清·康熙《淄川县志》,而毕际有、张绂、袁藩、李尧臣等都是参与者。比起明·嘉靖、万历两部《淄川县志》,康熙《淄川县志》体例更完备,内容更详实,厘正了过去县志上的不少讹误,说明比起前代,纂修者更认真,更有文化底气和自信。而在唐梦赉的带领下,张绂、李尧臣等人随后又完成了康熙《济南府志》54卷,这是济南府历史上的第一部府志。《济南府志》委托淄川这班文人来完成,更足以说明当时淄川文化人在整个济南府的地位和影响。
高珩极为重视自身修养与家教。创修族谱,制定祖训、庭训教导子孙。他制定的《十宜十戒家训》是:
宜畏天命、宜奉王章、宜敦孝友、宜济人物、宜勉谦和、宜安懦拙、宜守耕读世业、宜遵淳朴家风、宜待人人大度、宜持事事小心;
戒杀生、戒邪淫、戒傲、戒贪、戒赌、戒斗、戒懒、戒奢、戒无信无礼、戒不孝不仁。
同时,他提倡移风易俗,丧事从简,从而使一方土地改掉陋习,向文明靠拢。蒲松龄写《督丈词》,讽刺和揭露淄川管丈量土地的督察官擅自缩小尺寸,使淄川百姓蒙受损失的罪恶行径,高珩、王樛等知道了,出面揭出弊端,使执行者改正过来,保护了百姓利益。
唐梦赉做官三年即被罢官,虽身处林泉民间,心里却还惦记着经济、国防大事,他不仅文学才华名满天下,更具有卓越的济世才华,归田后仍心系家国天下,他的《铜钞疏》《禁籴说》《备边策》等作品,主张货币改革,建议招商引资,加强物资流通,以缓解政府财政的压力,为官增俸,为民减税等等,又针对时弊写了许多利世文章,据王士禛《敕授徵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载:“尤加意桑梓,如《议革签报柜书》、《筹省漕粮折解》、《免西郭义集起税》,皆请于县令,力举行之。县人食其利者二十余年。”高珩赞其有“救时宰相之才”, 山东巡抚张鹏亦有同感。
对于唐梦赉的济世之才,康熙皇帝也十分认可。康熙皇帝南巡时,曾两次召见唐梦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康熙皇帝正月第二次南巡,正值灾荒年景,62岁的唐梦赉在济南第二次被召见。康熙帝问唐梦赉减免税租一事,唐梦赉以百姓与国家的关系,据实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康熙帝于是诏示山东巡抚钱钰“蠲免山东二十九年通省钱粮”,也就是免除了康熙二十九年(1690)整个济南府的钱粮税。
唐梦赉尤其爱好推奖士类,一些文人学子经过他的指导传授,都成为名士,并且科举考试一跃成功,例如苏元行、谭再生、杨万春等等。
王樛关心家乡百姓,在本乡办义学,供同族子弟学习;拆掉房子五间,约值银几百两,帮助县里重修学宫;出资建韩仓桥,方便淄川至青州的交通;淄川官票盐税被坏人操纵,课税压得百姓十分痛苦,王樛出面协调,将官票归商人,让商人办课税,使商人、百姓都深为受益;淄川无狐狸,却要向朝廷供奉狐皮,百姓深受其害,几乎逼人致死。王樛帮助交涉,转为免供。
康熙三十六年(1697)高珩以86岁高龄无疾而终,第二年,72岁的唐梦赉又突然去世,两年间痛失两位文化界核心人物,从哪方面说,也是淄川的重大损失。所以蒲松龄在高珩去世后,曾以七律三首沉痛悼念,而在唐梦赉去世后,蒲松龄在《为众乡绅祭唐太史》文中,有“一木折而大厦倾,一人死而气运衰”、“衣冠遂无领袖,里社竟无典型”之句,表现了淄川文化界深重的惋惜之情和切肤之痛。从中也可看出他们在本地区文化界的重要地位。
四、 无分南北同一体
淄川高氏、毕氏与新城王家联系密切。提到新城王家,最负盛名的当属王士禛(渔洋)。
王士禛(1634—1711),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世称王渔洋,清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康熙四十三年(1704)官至刑部尚书。清初杰出诗人、文学家,诗论创“神韵”说,于后世影响深远。好为笔记,有《池北偶谈》《古夫于亭杂录》《香祖笔记》等。
王渔洋和高珩是表兄弟,比高珩小22岁,毕际有分别是高珩和王渔洋的姨夫和姑父,王樛因为是毕际有的妹夫也就和二人有了亲戚关系,同时,高珩的高祖母高王氏也就是王樛的太老姑,都是亲戚。这样,他们就有了经常联系的可能。因此诗文常常互相交流,由此,在毕家坐馆的蒲松龄的作品便也同时得到他们的青睐和推举。高珩去世二年后,其仲子高之騱请王士祯写了《诰授通奉大夫刑部左侍郎念东高公神道碑铭》,详述高珩一生,十分推崇其道德学问,并在文中有“相契合最深且久”之句,表明两人交往时间长且关系密切的情况。
而唐梦赉去世后,王士祯也为他写了《敕授徵仕郎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志铭》。
王渔洋还为高珩、唐梦赉、孙蕙、张笃庆的诗和蒲松龄的聊斋故事作点评,为唐梦赉和孙蕙的诗集写序言。
这些,都说明淄川与新城的文化名人联系是密切的。
那么,淄川文化圈与博山文人们交往如何呢?
孙廷铨(1613——1674),字枚先,博山人,崇祯十三年(1640)进士,曾为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内秘书院大学士。他与淄川高氏十世高玮、高珩、高玶兄弟是表兄弟,崇祯十二年(1639)乡试,高玮夺冠,冯溥第二,孙廷铨、高珩随后。高珩曾撰《孙文定公文集》序,从序中, 可以看出二人在参加乡试及后来至京城做官时交流很多,来往频繁。
高珩与博山赵执信叔祖赵进美同朝为官,并关系密切。而赵执信作为博山清朝著名文人,与高珩的关系更是非同一般。
唐梦赉的孙女是赵执信的儿媳,唐梦赉去世后,赵执信也为他写了《内翰林秘书院检讨豹岩唐公墓表》。
所以清朝初年,从南到北,孝妇河畔著名文化人联系密切,他们打破了地域界限,共同创造了孝妇河畔文化的辉煌。今天孝妇河畔丰厚的文化底蕴,是他们和先人铸就的,他们的精神、境界及留下的文化遗产,还在启迪和影响着今人,值得我们好好挖掘和研究。目前,这个工作正在进行着,如点校整理毕自严的《石隐园藏稿》、高珩的《栖云阁诗文集》,已经做了;唐梦赉的《志壑堂文集》及窎桥王家的《王氏一家言》正在点校整理即将完成;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及其他著作的研究一直做着;孙锡嘏先生的《般阳诗钞》正在整理之中,还有王樛、张笃庆的诗集以及好多文学遗产亟待整理。努力挖掘、整理典籍、弘扬地方传统文化,是我们后辈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都说孝妇河畔有王渔洋、蒲松龄、赵执信“三大”历史文化名人,其实高珩、唐梦赉也毫不逊色,按我的看法,应该是“五大”历史文化名人。
撰于 2018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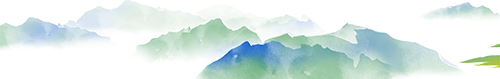


史志年鉴、族谱家史、
各种画册、国内单书号、丛书号、
电子音像号、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
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

军旅大校书法家书法宋忠厚独家销售
艺术热线:
13325115197




